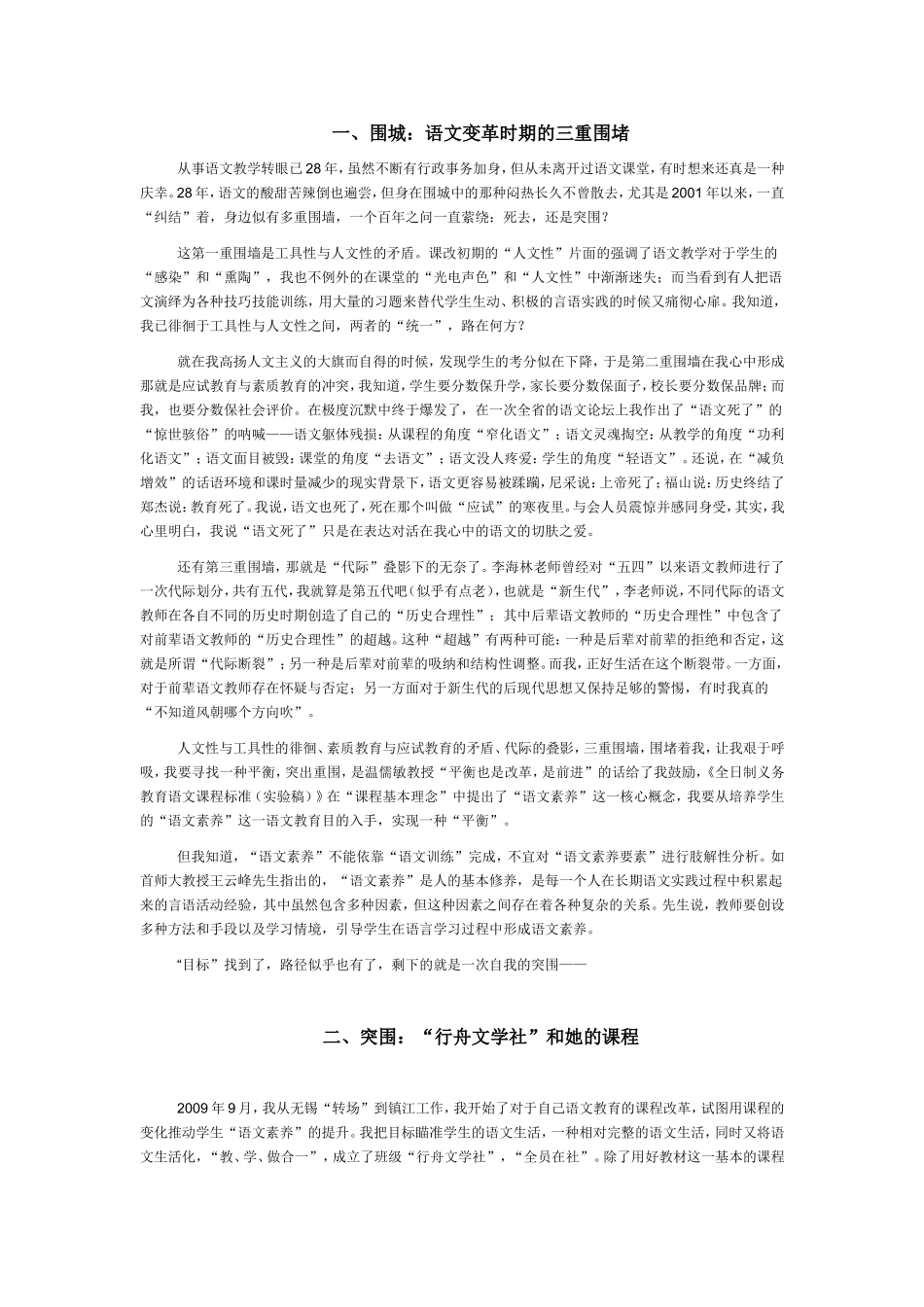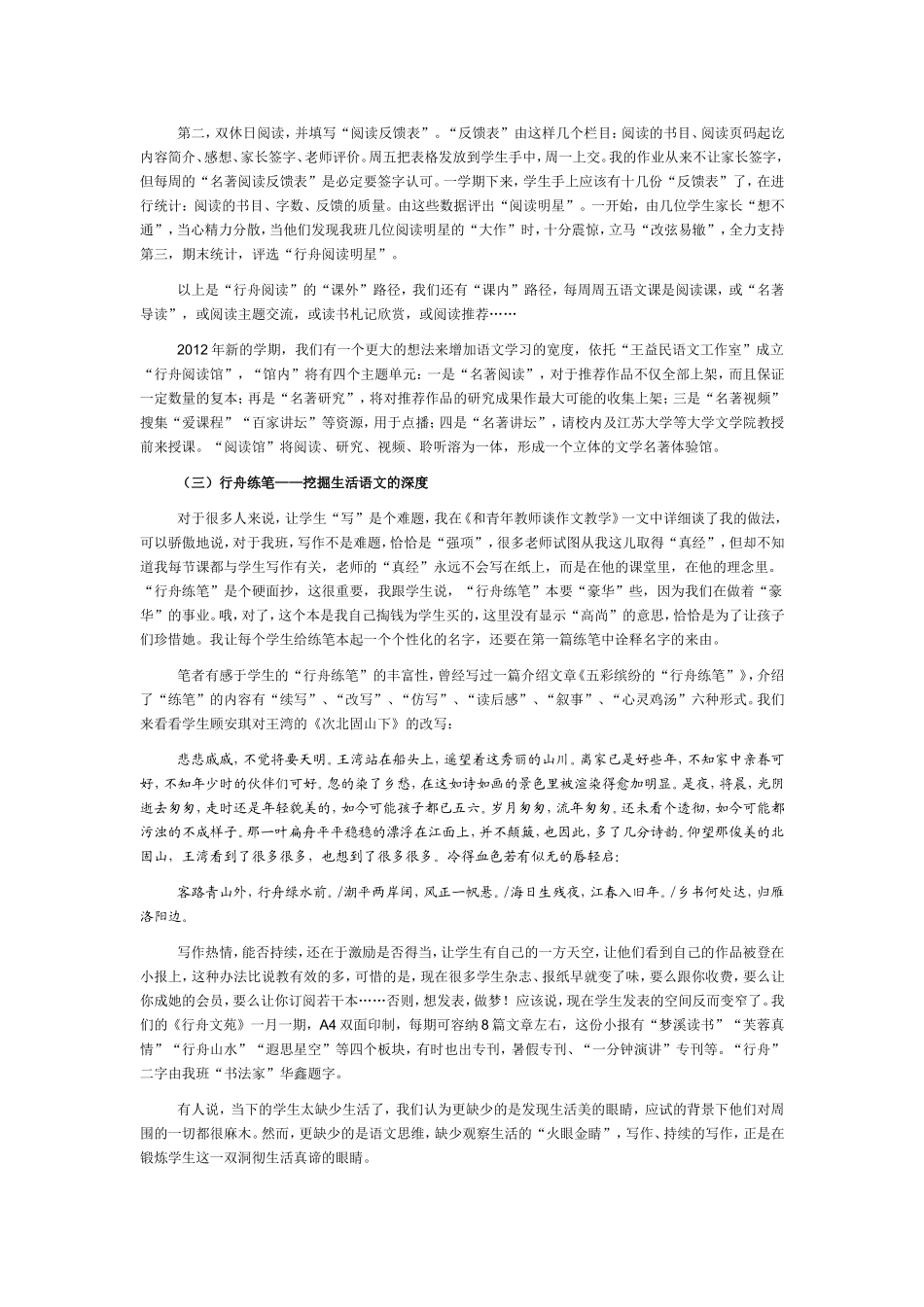一、围城:语文变革时期的三重围堵从事语文教学转眼已 28 年,虽然不断有行政事务加身,但从未离开过语文课堂,有时想来还真是一种庆幸。28 年,语文的酸甜苦辣倒也遍尝,但身在围城中的那种闷热长久不曾散去,尤其是 2001 年以来,一直“纠结”着,身边似有多重围墙,一个百年之问一直萦绕:死去,还是突围?这第一重围墙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矛盾。课改初期的“人文性”片面的强调了语文教学对于学生的“感染”和“熏陶”,我也不例外的在课堂的“光电声色”和“人文性”中渐渐迷失;而当看到有人把语文演绎为各种技巧技能训练,用大量的习题来替代学生生动、积极的言语实践的时候又痛彻心扉。我知道,我已徘徊于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两者的“统一”,路在何方?就在我高扬人文主义的大旗而自得的时候,发现学生的考分似在下降,于是第二重围墙在我心中形成那就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冲突,我知道,学生要分数保升学,家长要分数保面子,校长要分数保品牌;而我,也要分数保社会评价。在极度沉默中终于爆发了,在一次全省的语文论坛上我作出了“语文死了”的“惊世骇俗”的呐喊——语文躯体残损:从课程的角度“窄化语文”;语文灵魂掏空:从教学的角度“功利化语文”;语文面目被毁:课堂的角度“去语文”;语文没人疼爱:学生的角度“轻语文”。还说,在“减负增效”的话语环境和课时量减少的现实背景下,语文更容易被蹂躏,尼采说:上帝死了;福山说:历史终结了郑杰说:教育死了。我说,语文也死了,死在那个叫做“应试”的寒夜里。与会人员震惊并感同身受,其实,我心里明白,我说“语文死了”只是在表达对活在我心中的语文的切肤之爱。还有第三重围墙,那就是“代际”叠影下的无奈了。李海林老师曾经对“五四”以来语文教师进行了一次代际划分,共有五代,我就算是第五代吧(似乎有点老),也就是“新生代”,李老师说,不同代际的语文教师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其中后辈语文教师的“历史合理性”中包含了对前辈语文教师的“历史合理性”的超越。这种“超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后辈对前辈的拒绝和否定,这就是所谓“代际断裂”;另一种是后辈对前辈的吸纳和结构性调整。而我,正好生活在这个断裂带。一方面,对于前辈语文教师存在怀疑与否定;另一方面对于新生代的后现代思想又保持足够的警惕,有时我真的“不知道风朝哪个方向吹”。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徘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代际的叠影,三重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