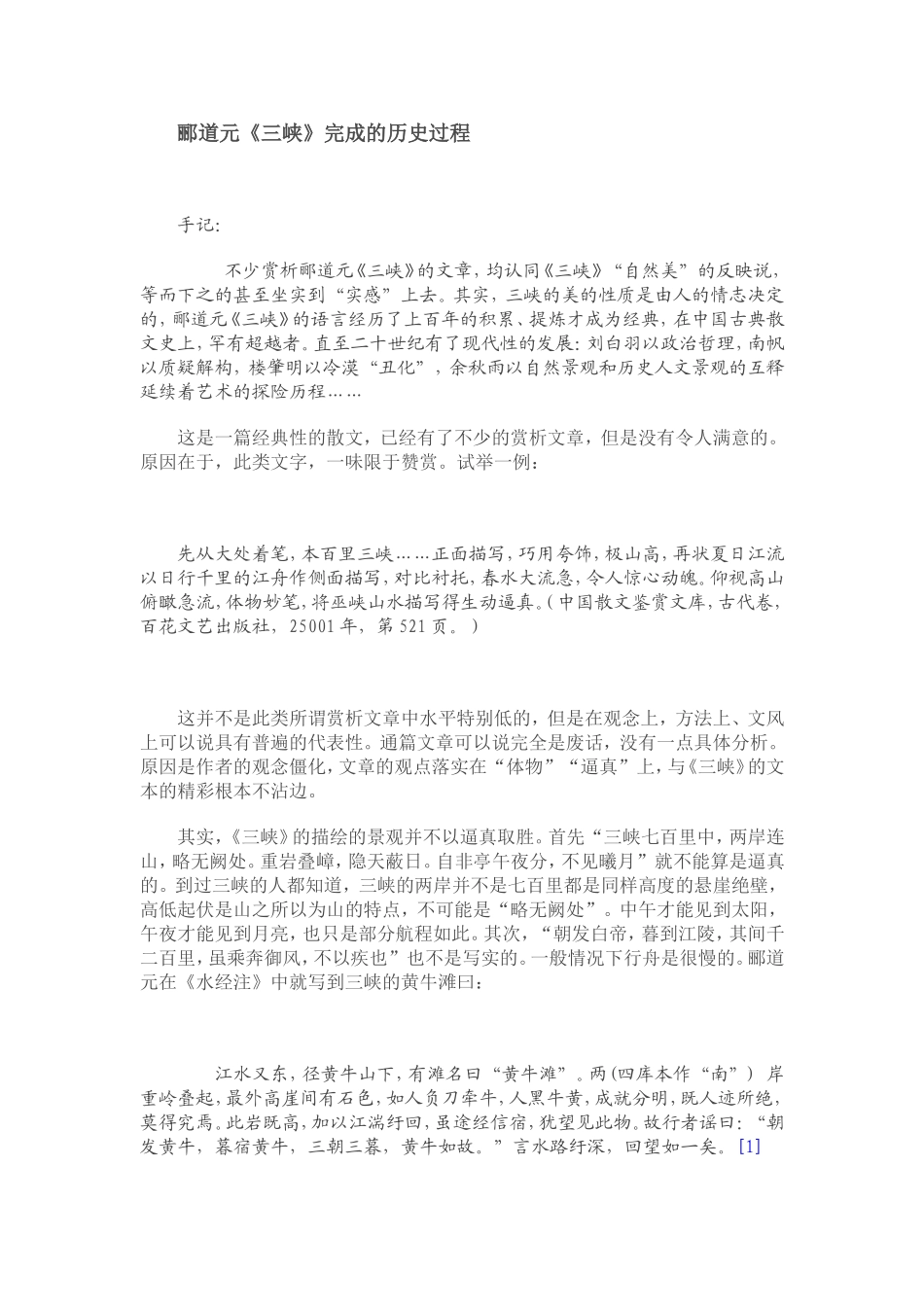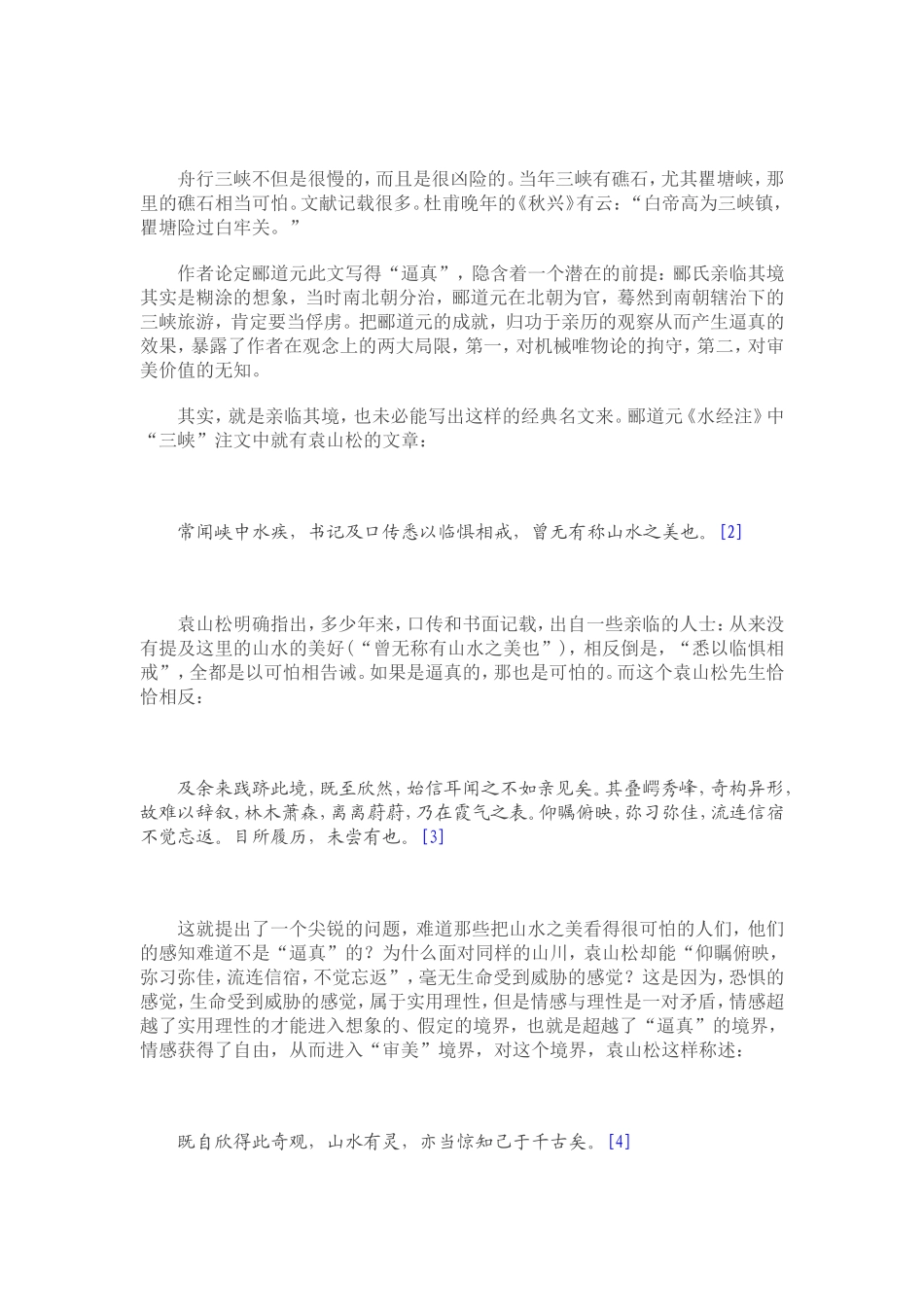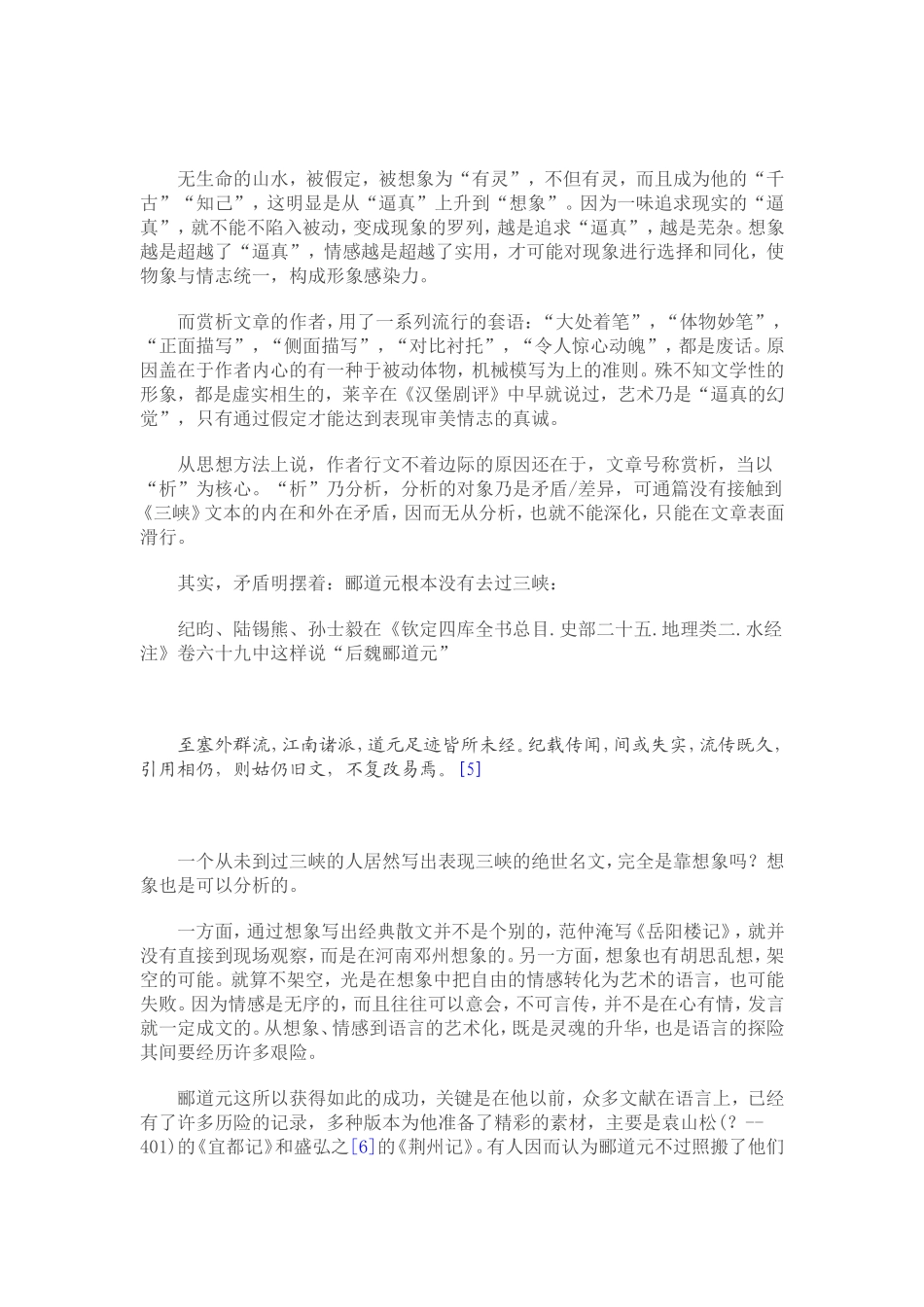郦道元《三峡》完成的历史过程 手记: 不少赏析郦道元《三峡》的文章,均认同《三峡》“自然美”的反映说,等而下之的甚至坐实到“实感”上去。其实,三峡的美的性质是由人的情志决定的,郦道元《三峡》的语言经历了上百年的积累、提炼才成为经典,在中国古典散文史上,罕有超越者。直至二十世纪有了现代性的发展:刘白羽以政治哲理,南帆以质疑解构,楼肇明以冷漠“丑化”,余秋雨以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的互释延续着艺术的探险历程……这是一篇经典性的散文,已经有了不少的赏析文章,但是没有令人满意的。原因在于,此类文字,一味限于赞赏。试举一例: 先从大处着笔,本百里三峡……正面描写,巧用夸饰,极山高,再状夏日江流以日行千里的江舟作侧面描写,对比衬托,春水大流急,令人惊心动魄。仰视高山俯瞰急流,体物妙笔,将巫峡山水描写得生动逼真。(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5001 年,第 521 页。) 这并不是此类所谓赏析文章中水平特别低的,但是在观念上,方法上、文风上可以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通篇文章可以说完全是废话,没有一点具体分析。原因是作者的观念僵化,文章的观点落实在“体物”“逼真”上,与《三峡》的文本的精彩根本不沾边。其实,《三峡》的描绘的景观并不以逼真取胜。首先“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就不能算是逼真的。到过三峡的人都知道,三峡的两岸并不是七百里都是同样高度的悬崖绝壁,高低起伏是山之所以为山的特点,不可能是“略无阙处”。中午才能见到太阳,午夜才能见到月亮,也只是部分航程如此。其次,“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也不是写实的。一般情况下行舟是很慢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写到三峡的黄牛滩曰: 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两(四库本作“南”) 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1] 舟行三峡不但是很慢的,而且是很凶险的。当年三峡有礁石,尤其瞿塘峡,那里的礁石相当可怕。文献记载很多。杜甫晚年的《秋兴》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白牢关。”作者论定郦道元此文写得“逼真”,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前提:郦氏亲临其境其实是糊涂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