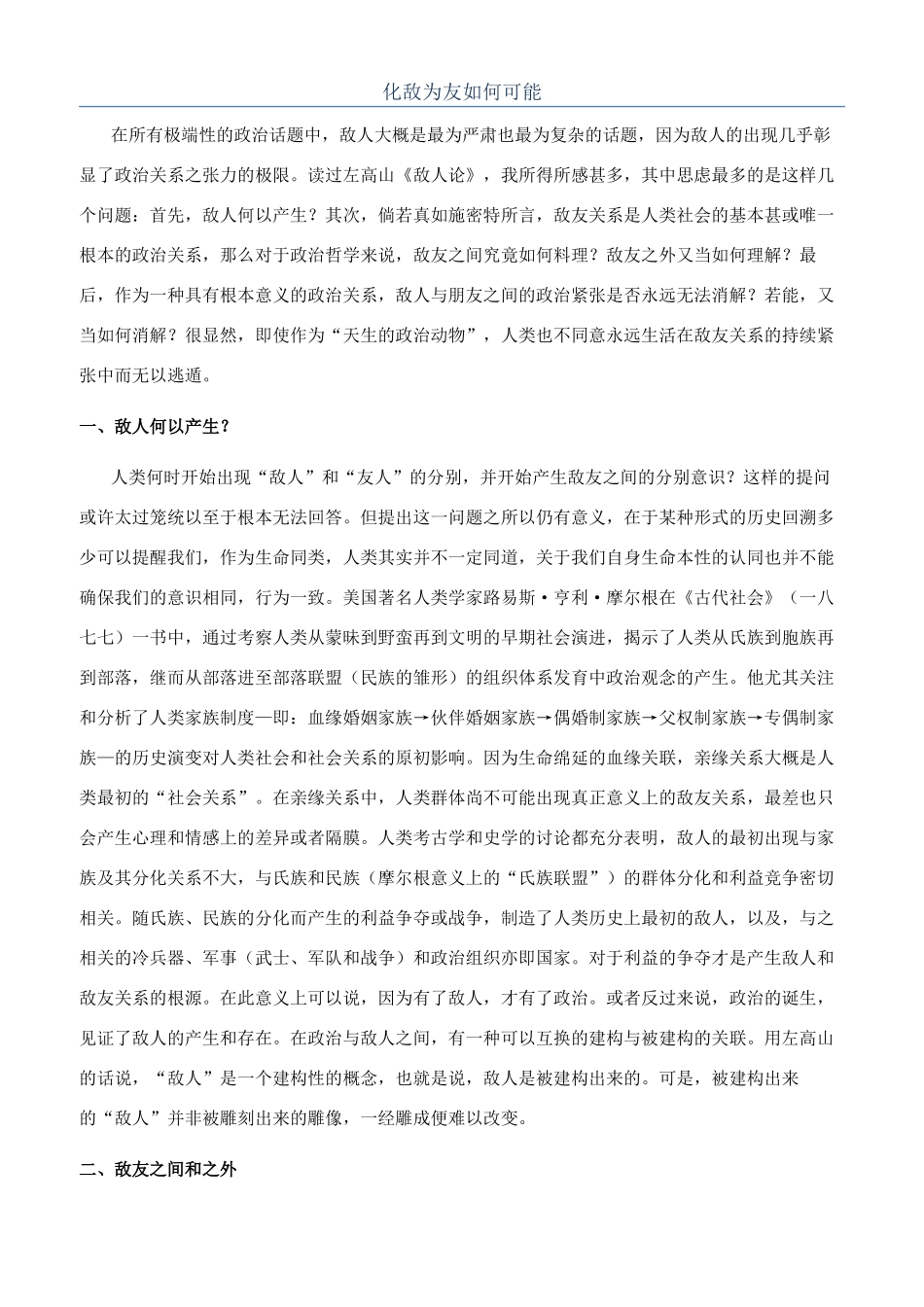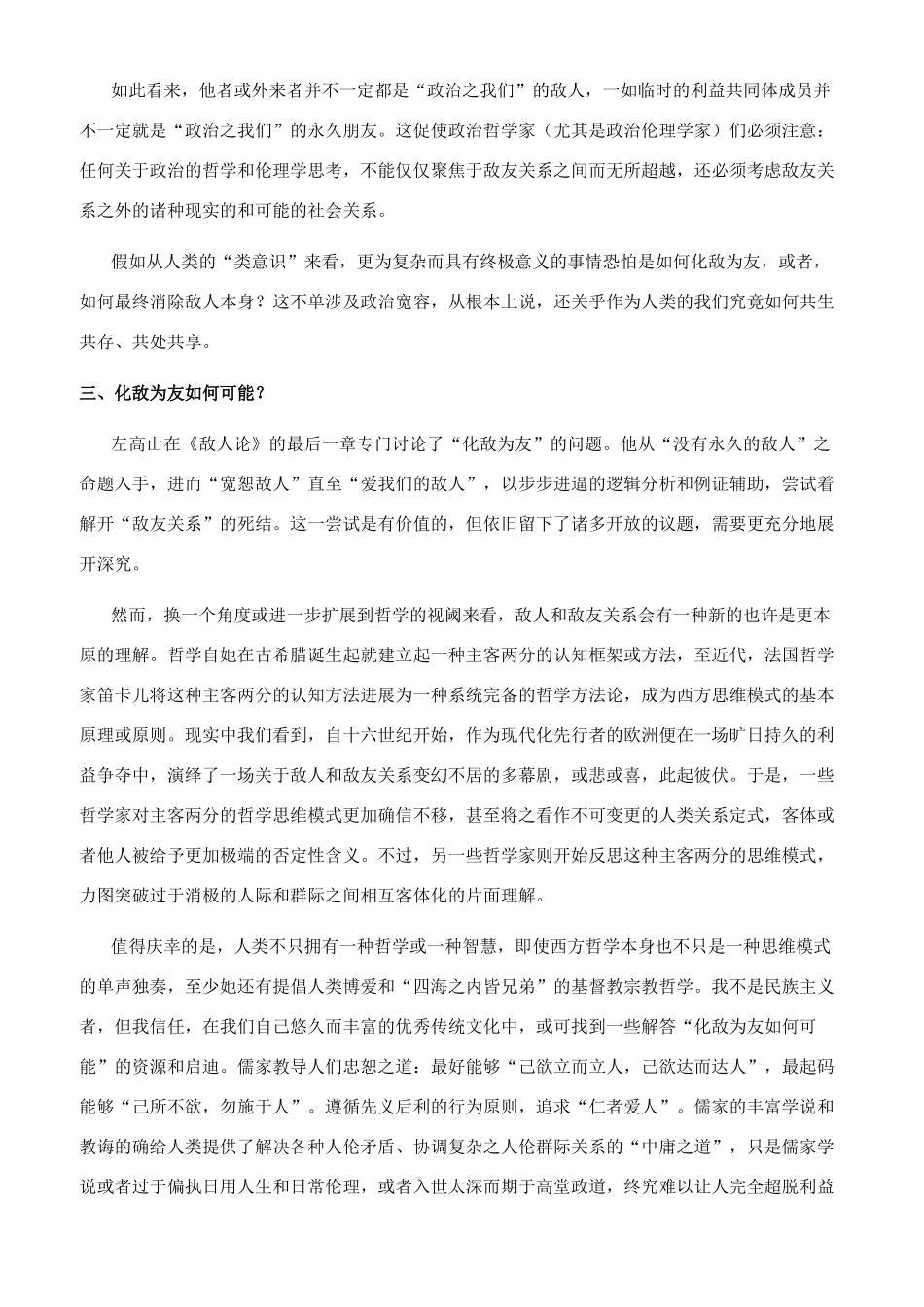化敌为友如何可能在所有极端性的政治话题中,敌人大概是最为严肃也最为复杂的话题,因为敌人的出现几乎彰显了政治关系之张力的极限。读过左高山《敌人论》,我所得所感甚多,其中思虑最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敌人何以产生?其次,倘若真如施密特所言,敌友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甚或唯一根本的政治关系,那么对于政治哲学来说,敌友之间究竟如何料理?敌友之外又当如何理解?最后,作为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政治关系,敌人与朋友之间的政治紧张是否永远无法消解?若能,又当如何消解?很显然,即使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也不同意永远生活在敌友关系的持续紧张中而无以逃遁。一、敌人何以产生?人类何时开始出现“敌人”和“友人”的分别,并开始产生敌友之间的分别意识?这样的提问或许太过笼统以至于根本无法回答。但提出这一问题之所以仍有意义,在于某种形式的历史回溯多少可以提醒我们,作为生命同类,人类其实并不一定同道,关于我们自身生命本性的认同也并不能确保我们的意识相同,行为一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八七七)一书中,通过考察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早期社会演进,揭示了人类从氏族到胞族再到部落,继而从部落进至部落联盟(民族的雏形)的组织体系发育中政治观念的产生。他尤其关注和分析了人类家族制度—即:血缘婚姻家族→伙伴婚姻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权制家族→专偶制家族—的历史演变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原初影响。因为生命绵延的血缘关联,亲缘关系大概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在亲缘关系中,人类群体尚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敌友关系,最差也只会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差异或者隔膜。人类考古学和史学的讨论都充分表明,敌人的最初出现与家族及其分化关系不大,与氏族和民族(摩尔根意义上的“氏族联盟”)的群体分化和利益竞争密切相关。随氏族、民族的分化而产生的利益争夺或战争,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敌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冷兵器、军事(武士、军队和战争)和政治组织亦即国家。对于利益的争夺才是产生敌人和敌友关系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有了敌人,才有了政治。或者反过来说,政治的诞生,见证了敌人的产生和存在。在政治与敌人之间,有一种可以互换的建构与被建构的关联。用左高山的话说,“敌人”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敌人是被建构出来的。可是,被建构出来的“敌人”并非被雕刻出来的雕像,一经雕成便难以改变。二、敌友之间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