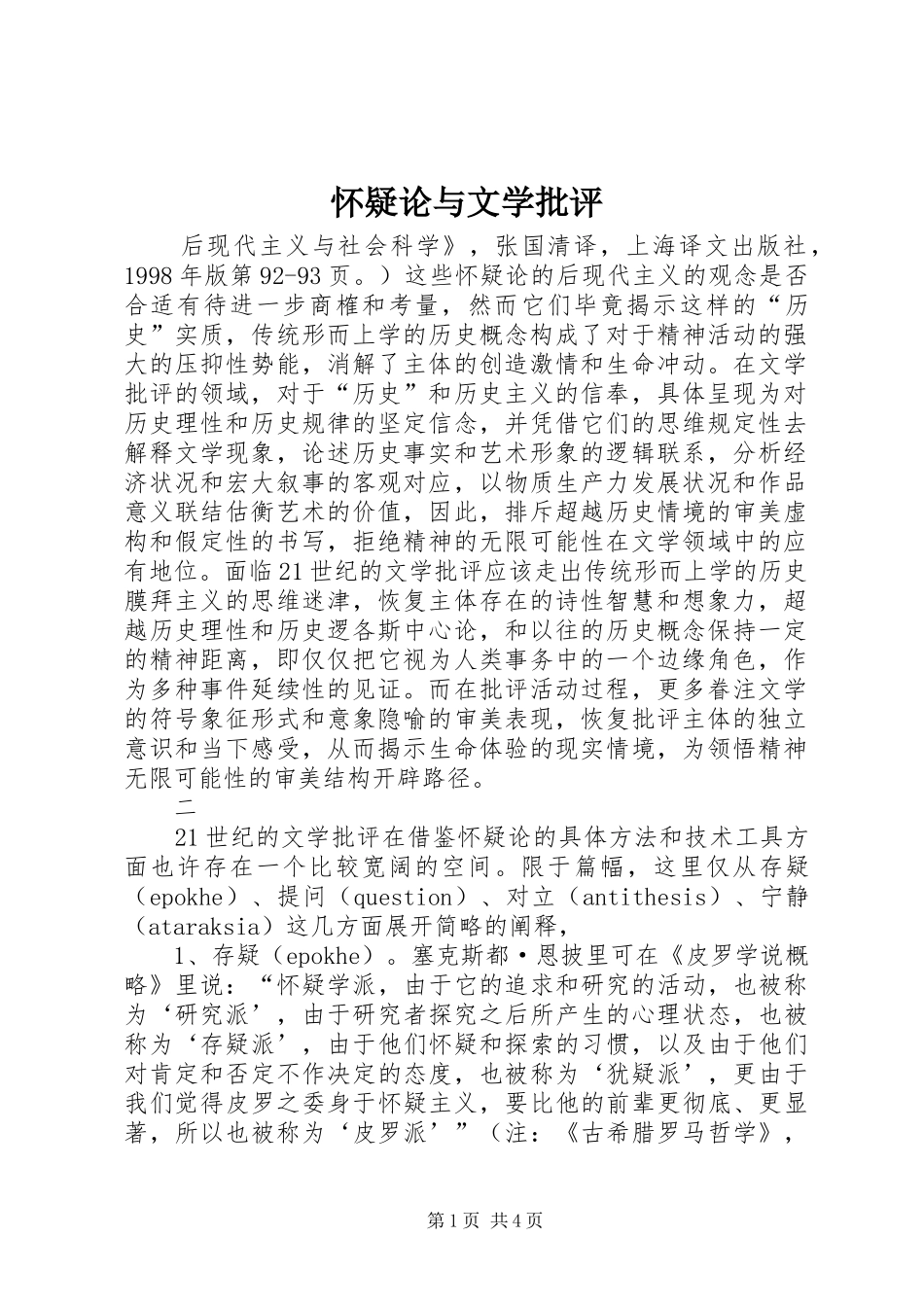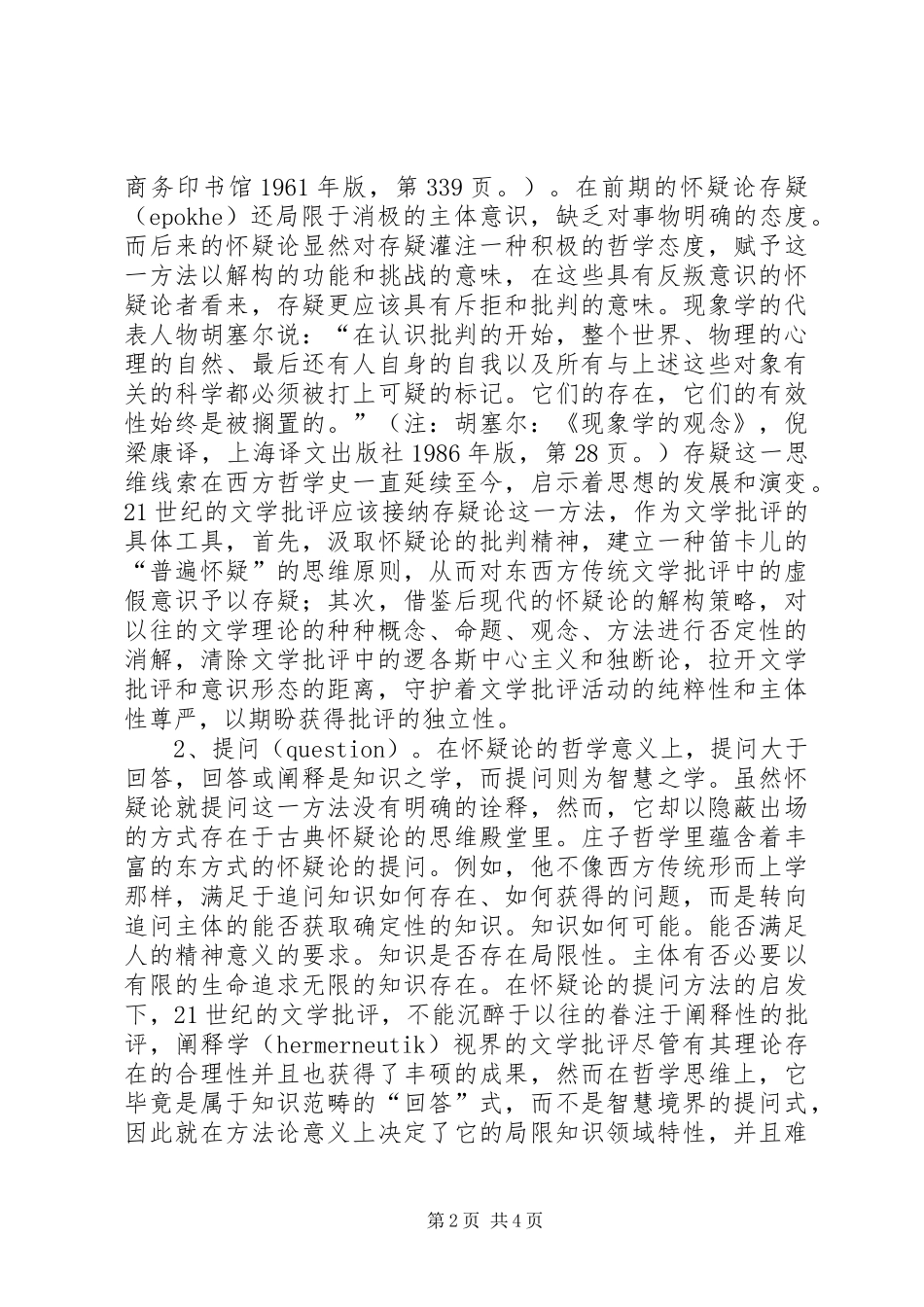怀疑论与文学批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2-93页。)这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考量,然而它们毕竟揭示这样的“历史”实质,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构成了对于精神活动的强大的压抑性势能,消解了主体的创造激情和生命冲动。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对于“历史”和历史主义的信奉,具体呈现为对历史理性和历史规律的坚定信念,并凭借它们的思维规定性去解释文学现象,论述历史事实和艺术形象的逻辑联系,分析经济状况和宏大叙事的客观对应,以物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作品意义联结估衡艺术的价值,因此,排斥超越历史情境的审美虚构和假定性的书写,拒绝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在文学领域中的应有地位。面临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膜拜主义的思维迷津,恢复主体存在的诗性智慧和想象力,超越历史理性和历史逻各斯中心论,和以往的历史概念保持一定的精神距离,即仅仅把它视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边缘角色,作为多种事件延续性的见证。而在批评活动过程,更多眷注文学的符号象征形式和意象隐喻的审美表现,恢复批评主体的独立意识和当下感受,从而揭示生命体验的现实情境,为领悟精神无限可能性的审美结构开辟路径。二21世纪的文学批评在借鉴怀疑论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工具方面也许存在一个比较宽阔的空间。限于篇幅,这里仅从存疑(epokhe)、提问(question)、对立(antithesis)、宁静(ataraksia)这几方面展开简略的阐释,1、存疑(epokhe)。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在《皮罗学说概略》里说:“怀疑学派,由于它的追求和研究的活动,也被称为‘研究派’,由于研究者探究之后所产生的心理状态,也被称为‘存疑派’,由于他们怀疑和探索的习惯,以及由于他们对肯定和否定不作决定的态度,也被称为‘犹疑派’,更由于我们觉得皮罗之委身于怀疑主义,要比他的前辈更彻底、更显著,所以也被称为‘皮罗派’”(注:《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页共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9页。)。在前期的怀疑论存疑(epokhe)还局限于消极的主体意识,缺乏对事物明确的态度。而后来的怀疑论显然对存疑灌注一种积极的哲学态度,赋予这一方法以解构的功能和挑战的意味,在这些具有反叛意识的怀疑论者看来,存疑更应该具有斥拒和批判的意味。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说:“在认识批判的开始,整个世界、物理的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存疑这一思维线索在西方哲学史一直延续至今,启示着思想的发展和演变。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接纳存疑论这一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具体工具,首先,汲取怀疑论的批判精神,建立一种笛卡儿的“普遍怀疑”的思维原则,从而对东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虚假意识予以存疑;其次,借鉴后现代的怀疑论的解构策略,对以往的文学理论的种种概念、命题、观念、方法进行否定性的消解,清除文学批评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独断论,拉开文学批评和意识形态的距离,守护着文学批评活动的纯粹性和主体性尊严,以期盼获得批评的独立性。2、提问(question)。在怀疑论的哲学意义上,提问大于回答,回答或阐释是知识之学,而提问则为智慧之学。虽然怀疑论就提问这一方法没有明确的诠释,然而,它却以隐蔽出场的方式存在于古典怀疑论的思维殿堂里。庄子哲学里蕴含着丰富的东方式的怀疑论的提问。例如,他不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样,满足于追问知识如何存在、如何获得的问题,而是转向追问主体的能否获取确定性的知识。知识如何可能。能否满足人的精神意义的要求。知识是否存在局限性。主体有否必要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存在。在怀疑论的提问方法的启发下,21世纪的文学批评,不能沉醉于以往的眷注于阐释性的批评,阐释学(hermerneutik)视界的文学批评尽管有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哲学思维上,它毕竟是属于知识范畴的“回答”式,而不是智慧境界的提问式,因此就在方法论意义上决定了它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