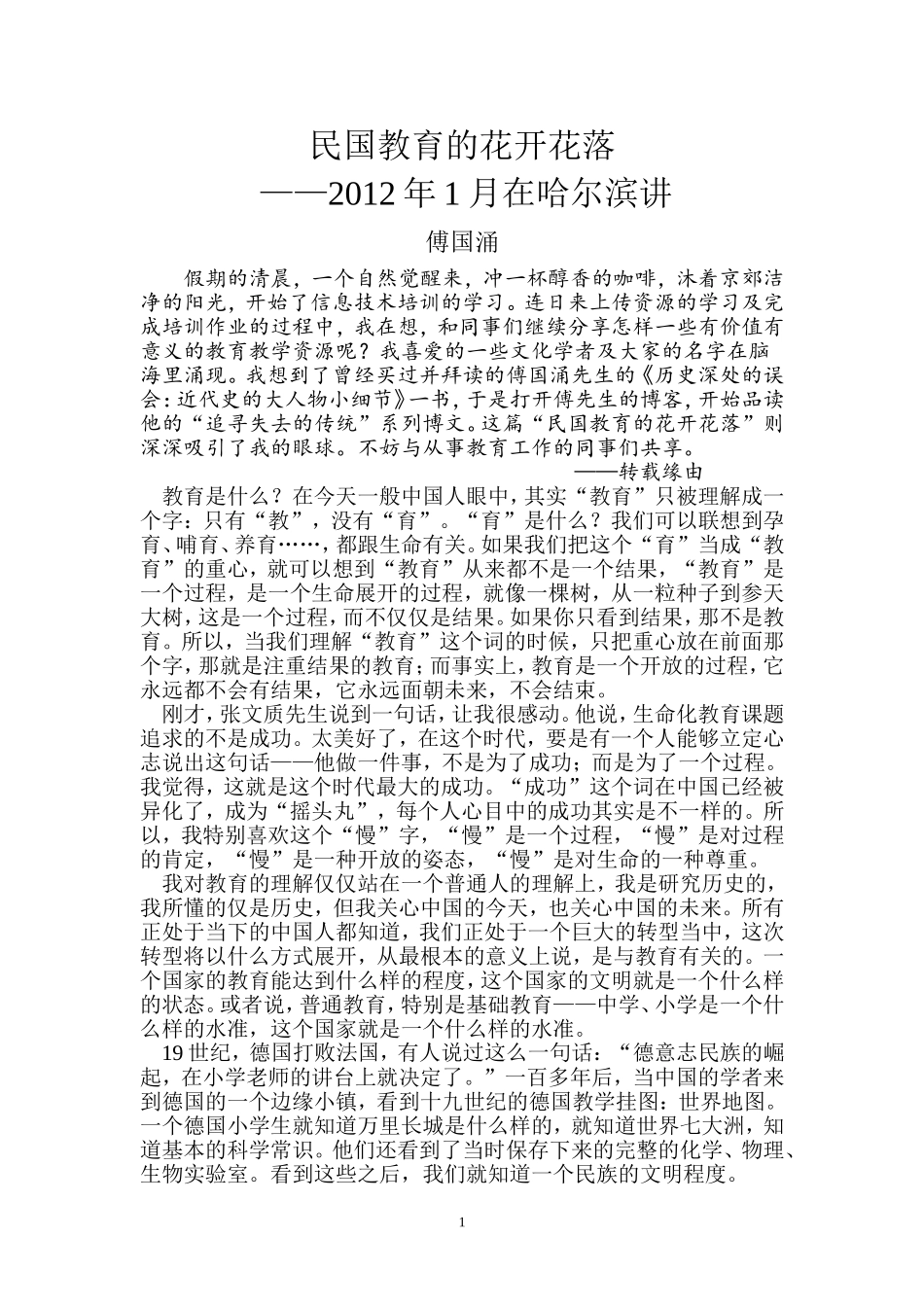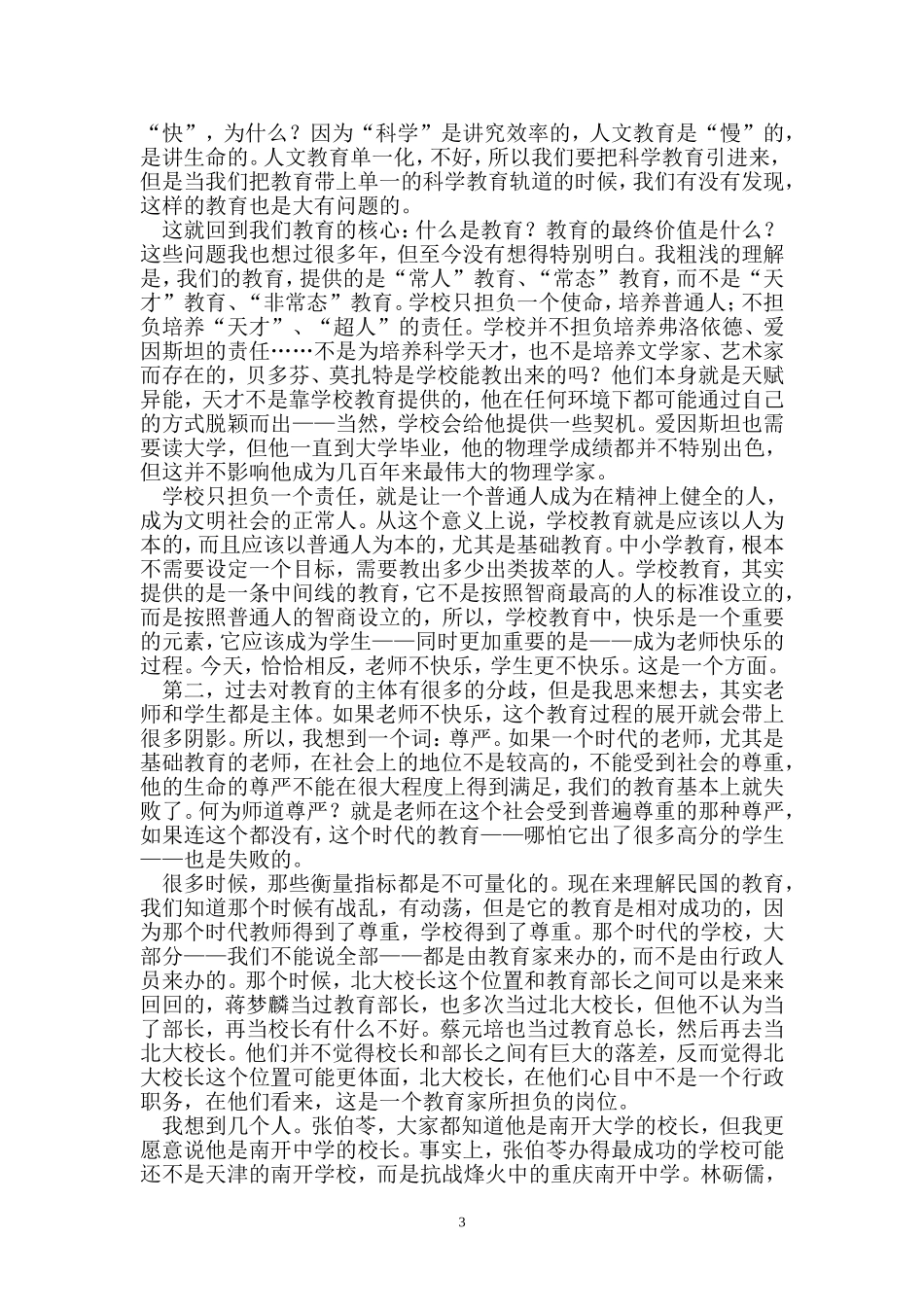1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2012年1月在哈尔滨讲傅国涌假期的清晨,一个自然觉醒来,冲一杯醇香的咖啡,沐着京郊洁净的阳光,开始了信息技术培训的学习。连日来上传资源的学习及完成培训作业的过程中,我在想,和同事们继续分享怎样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教学资源呢?我喜爱的一些文化学者及大家的名字在脑海里涌现。我想到了曾经买过并拜读的傅国涌先生的《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一书,于是打开傅先生的博客,开始品读他的“追寻失去的传统”系列博文。这篇“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则深深吸引了我的眼球。不妨与从事教育工作的同事们共享。——转载缘由教育是什么?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眼中,其实“教育”只被理解成一个字: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结果,“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这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如果你只看到结果,那不是教育。所以,当我们理解“教育”这个词的时候,只把重心放在前面那个字,那就是注重结果的教育;而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它永远面朝未来,不会结束。刚才,张文质先生说到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生命化教育课题追求的不是成功。太美好了,在这个时代,要是有一个人能够立定心志说出这句话——他做一件事,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成功”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异化了,成为“摇头丸”,每个人心目中的成功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慢”字,“慢”是一个过程,“慢”是对过程的肯定,“慢”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慢”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我对教育的理解仅仅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理解上,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所懂的仅是历史,但我关心中国的今天,也关心中国的未来。所有正处于当下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当中,这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与教育有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学、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19世纪,德国打败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一百多年后,当中国的学者来到德国的一个边缘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2我在关注民国历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们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顶尖的大学,我们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空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越会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而蔡元培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而所有的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所以,我说了一句话: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这句话曾经被媒体广泛引用。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我记得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