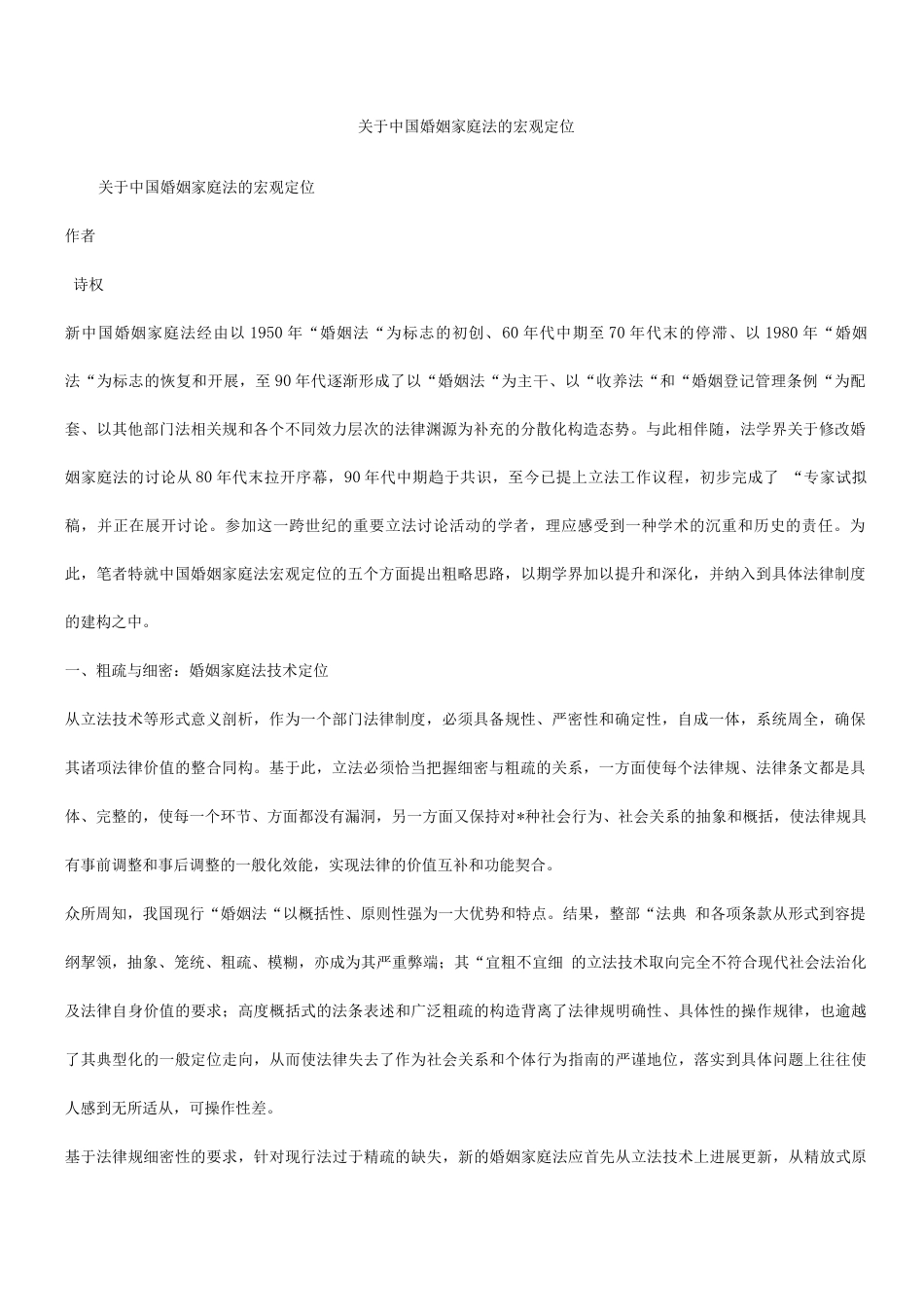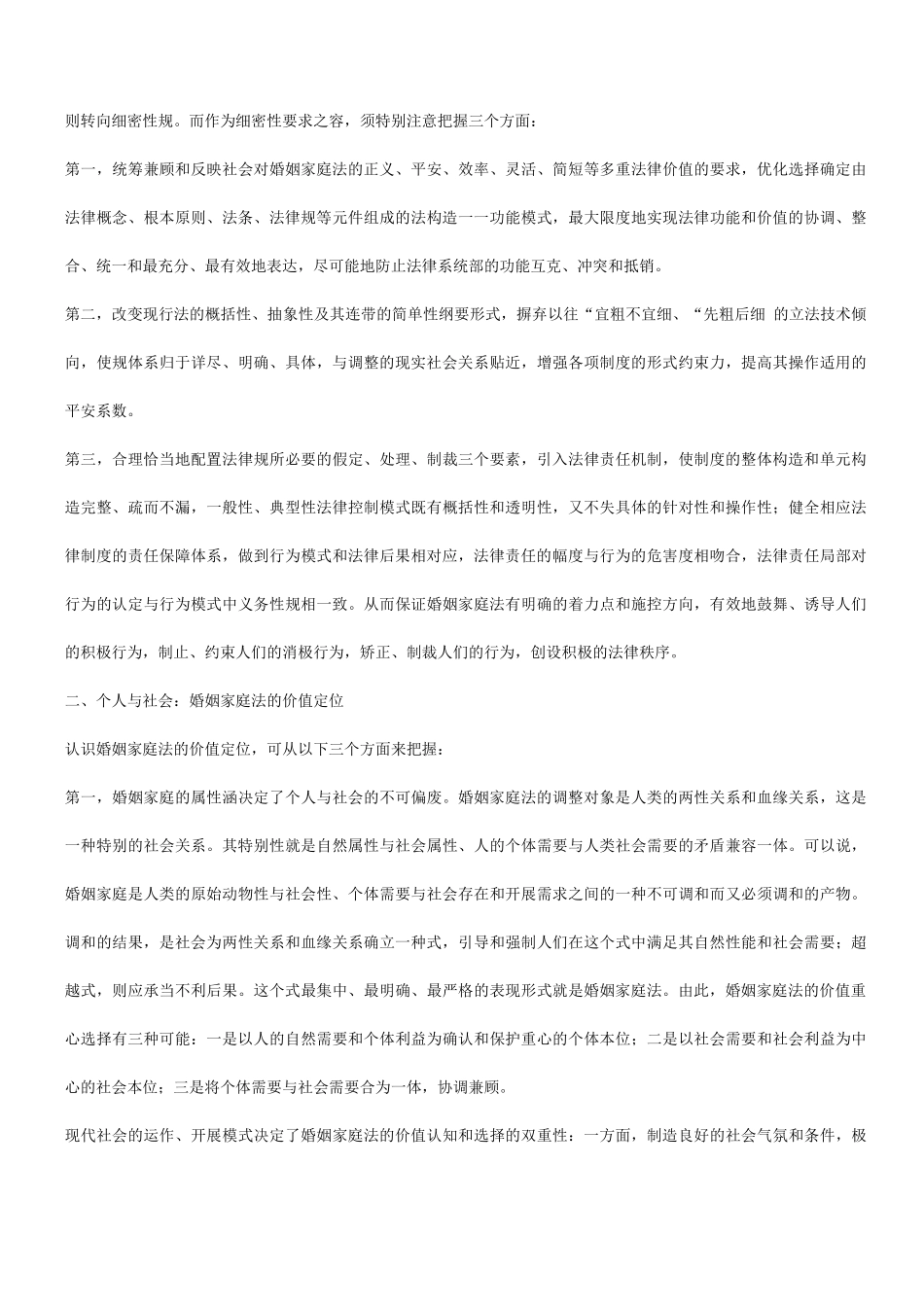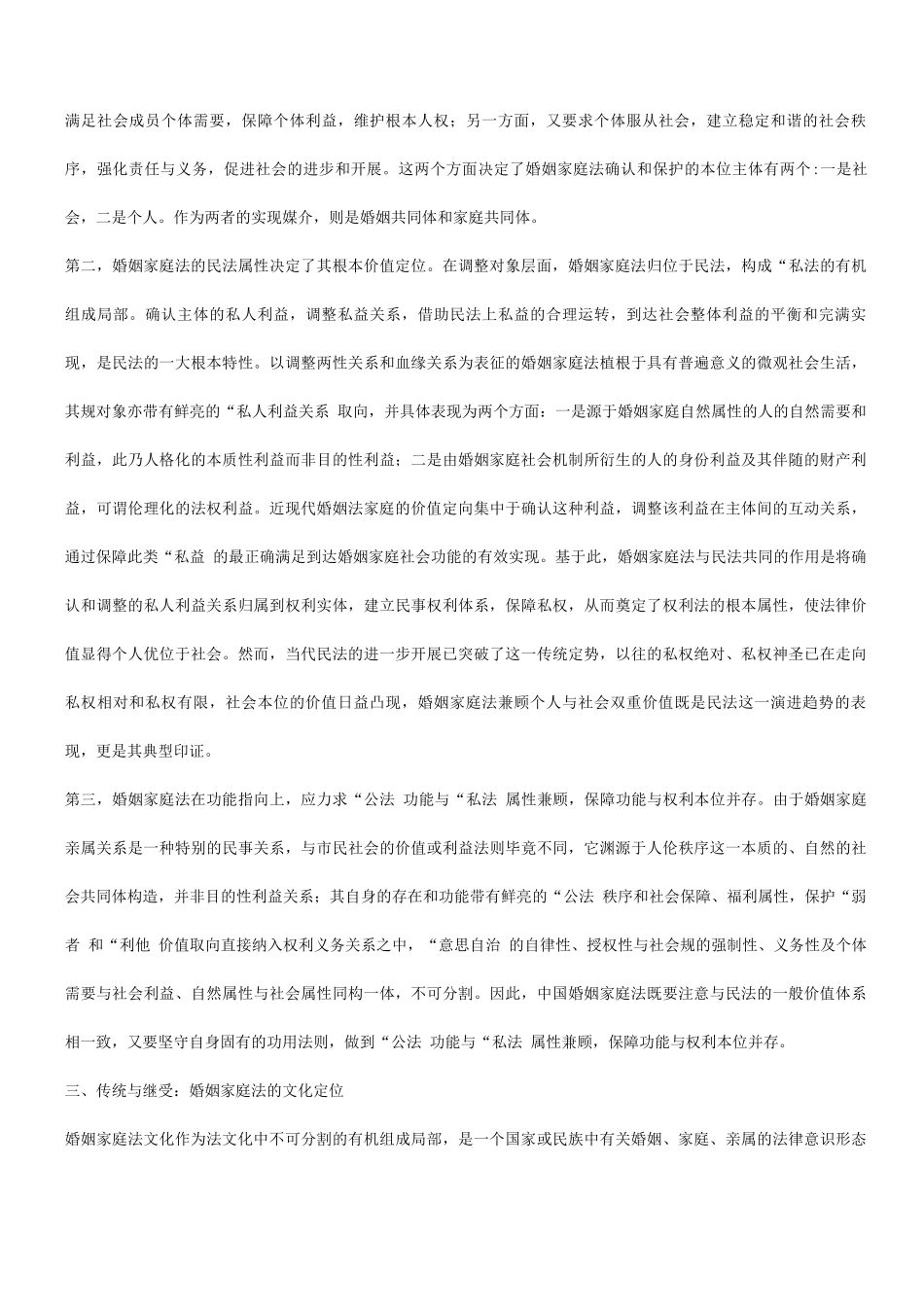关于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宏观定位关于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宏观定位作者诗权新中国婚姻家庭法经由以 1950 年“婚姻法“为标志的初创、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的停滞、以 1980 年“婚姻法“为标志的恢复和开展,至 90 年代逐渐形成了以“婚姻法“为主干、以“收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为配套、以其他部门法相关规和各个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渊源为补充的分散化构造态势。与此相伴随,法学界关于修改婚姻家庭法的讨论从 80 年代末拉开序幕,90 年代中期趋于共识,至今已提上立法工作议程,初步完成了 “专家试拟稿,并正在展开讨论。参加这一跨世纪的重要立法讨论活动的学者,理应感受到一种学术的沉重和历史的责任。为此,笔者特就中国婚姻家庭法宏观定位的五个方面提出粗略思路,以期学界加以提升和深化,并纳入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建构之中。一、粗疏与细密:婚姻家庭法技术定位从立法技术等形式意义剖析,作为一个部门法律制度,必须具备规性、严密性和确定性,自成一体,系统周全,确保其诸项法律价值的整合同构。基于此,立法必须恰当把握细密与粗疏的关系,一方面使每个法律规、法律条文都是具体、完整的,使每一个环节、方面都没有漏洞,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的抽象和概括,使法律规具有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的一般化效能,实现法律的价值互补和功能契合。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婚姻法“以概括性、原则性强为一大优势和特点。结果,整部“法典 和各项条款从形式到容提纲挈领,抽象、笼统、粗疏、模糊,亦成为其严重弊端;其“宜粗不宜细 的立法技术取向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法治化及法律自身价值的要求;高度概括式的法条表述和广泛粗疏的构造背离了法律规明确性、具体性的操作规律,也逾越了其典型化的一般定位走向,从而使法律失去了作为社会关系和个体行为指南的严谨地位,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往往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可操作性差。基于法律规细密性的要求,针对现行法过于精疏的缺失,新的婚姻家庭法应首先从立法技术上进展更新,从精放式原则转向细密性规。而作为细密性要求之容,须特别注意把握三个方面:第一,统筹兼顾和反映社会对婚姻家庭法的正义、平安、效率、灵活、简短等多重法律价值的要求,优化选择确定由法律概念、根本原则、法条、法律规等元件组成的法构造一一功能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功能和价值的协调、整合、统一和最充分、最有效地表达,尽可能地防止法律系统部的功能互克、冲突和抵销。第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