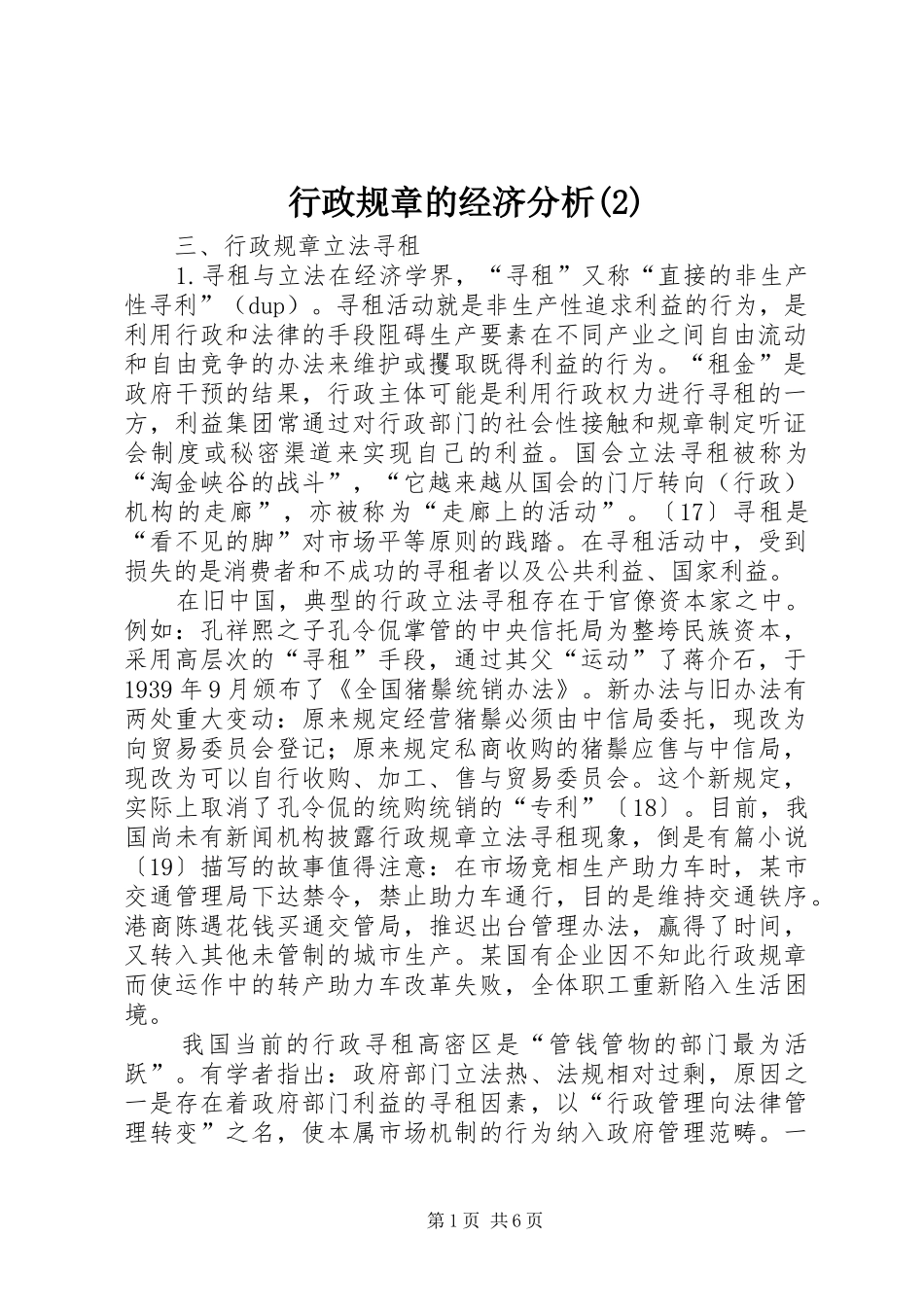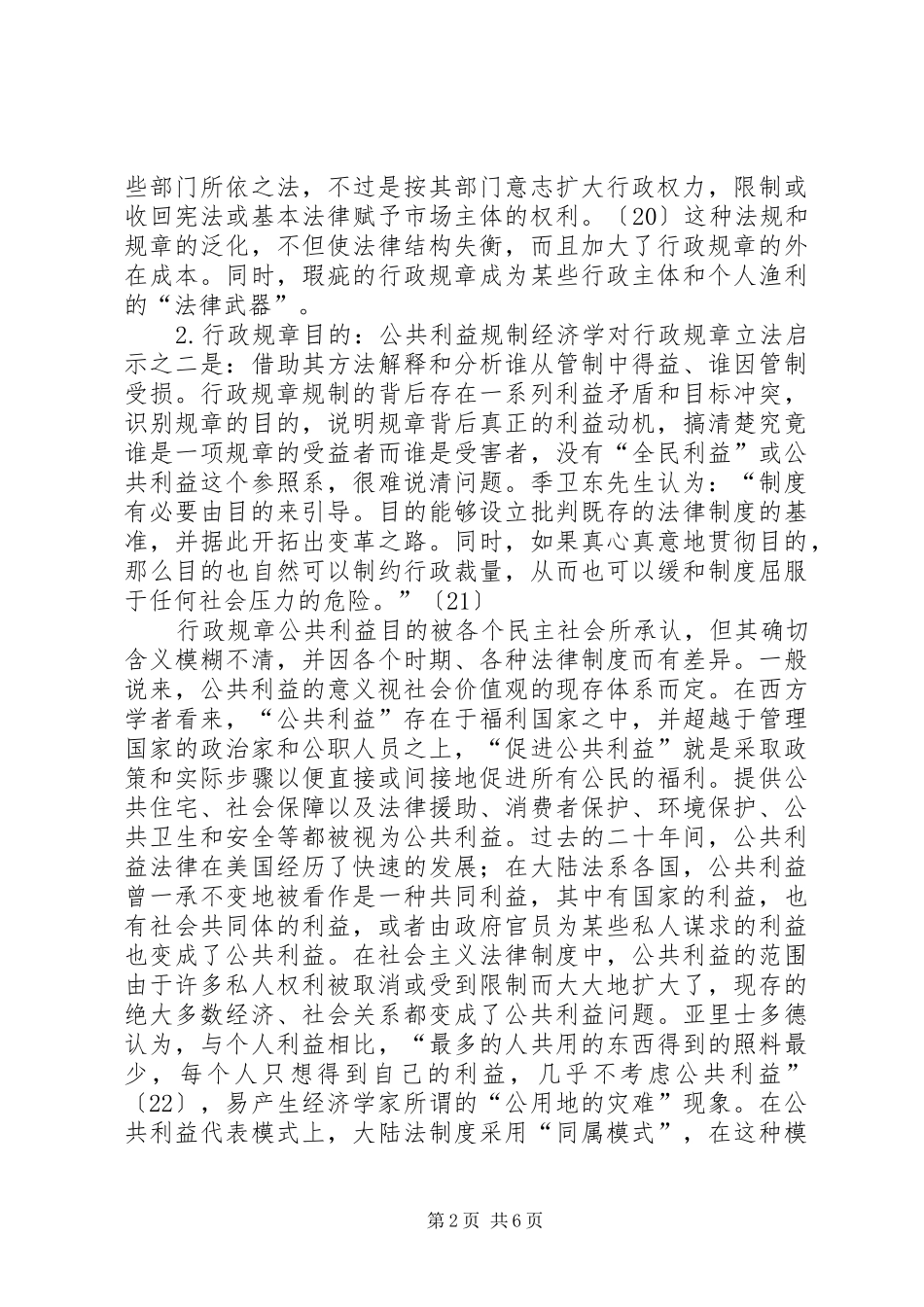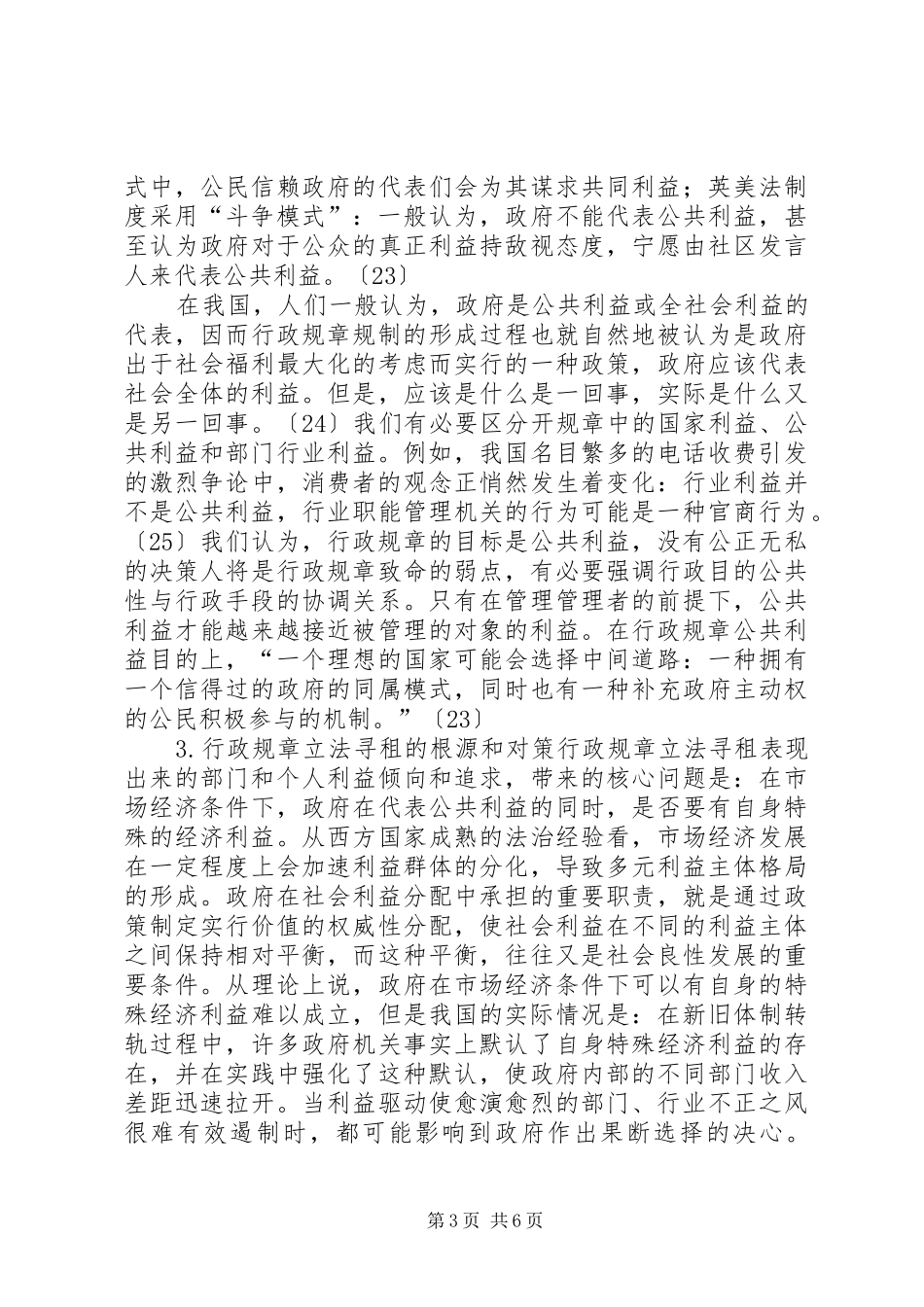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2)三、行政规章立法寻租1.寻租与立法在经济学界,“寻租”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租金”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行政主体可能是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寻租的一方,利益集团常通过对行政部门的社会性接触和规章制定听证会制度或秘密渠道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国会立法寻租被称为“淘金峡谷的战斗”,“它越来越从国会的门厅转向(行政)机构的走廊”,亦被称为“走廊上的活动”。〔17〕寻租是“看不见的脚”对市场平等原则的践踏。在寻租活动中,受到损失的是消费者和不成功的寻租者以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在旧中国,典型的行政立法寻租存在于官僚资本家之中。例如: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掌管的中央信托局为整垮民族资本,采用高层次的“寻租”手段,通过其父“运动”了蒋介石,于1939年9月颁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新办法与旧办法有两处重大变动:原来规定经营猪鬃必须由中信局委托,现改为向贸易委员会登记;原来规定私商收购的猪鬃应售与中信局,现改为可以自行收购、加工、售与贸易委员会。这个新规定,实际上取消了孔令侃的统购统销的“专利”〔18〕。目前,我国尚未有新闻机构披露行政规章立法寻租现象,倒是有篇小说〔19〕描写的故事值得注意:在市场竞相生产助力车时,某市交通管理局下达禁令,禁止助力车通行,目的是维持交通铁序。港商陈遇花钱买通交管局,推迟出台管理办法,赢得了时间,又转入其他未管制的城市生产。某国有企业因不知此行政规章而使运作中的转产助力车改革失败,全体职工重新陷入生活困境。我国当前的行政寻租高密区是“管钱管物的部门最为活跃”。有学者指出:政府部门立法热、法规相对过剩,原因之一是存在着政府部门利益的寻租因素,以“行政管理向法律管理转变”之名,使本属市场机制的行为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一第1页共6页些部门所依之法,不过是按其部门意志扩大行政权力,限制或收回宪法或基本法律赋予市场主体的权利。〔20〕这种法规和规章的泛化,不但使法律结构失衡,而且加大了行政规章的外在成本。同时,瑕疵的行政规章成为某些行政主体和个人渔利的“法律武器”。2.行政规章目的:公共利益规制经济学对行政规章立法启示之二是:借助其方法解释和分析谁从管制中得益、谁因管制受损。行政规章规制的背后存在一系列利益矛盾和目标冲突,识别规章的目的,说明规章背后真正的利益动机,搞清楚究竟谁是一项规章的受益者而谁是受害者,没有“全民利益”或公共利益这个参照系,很难说清问题。季卫东先生认为:“制度有必要由目的来引导。目的能够设立批判既存的法律制度的基准,并据此开拓出变革之路。同时,如果真心真意地贯彻目的,那么目的也自然可以制约行政裁量,从而也可以缓和制度屈服于任何社会压力的危险。”〔21〕行政规章公共利益目的被各个民主社会所承认,但其确切含义模糊不清,并因各个时期、各种法律制度而有差异。一般说来,公共利益的意义视社会价值观的现存体系而定。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共利益”存在于福利国家之中,并超越于管理国家的政治家和公职人员之上,“促进公共利益”就是采取政策和实际步骤以便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所有公民的福利。提供公共住宅、社会保障以及法律援助、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等都被视为公共利益。过去的二十年间,公共利益法律在美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在大陆法系各国,公共利益曾一承不变地被看作是一种共同利益,其中有国家的利益,也有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或者由政府官员为某些私人谋求的利益也变成了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的范围由于许多私人权利被取消或受到限制而大大地扩大了,现存的绝大多数经济、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公共利益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与个人利益相比,“最多的人共用的东西得到的照料最少,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几乎不考虑公共利益”〔22〕,易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公用地的灾难”现象。在公共利益代表模式上,大陆法制度采用“同属模式”,在这种模第2页共6页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