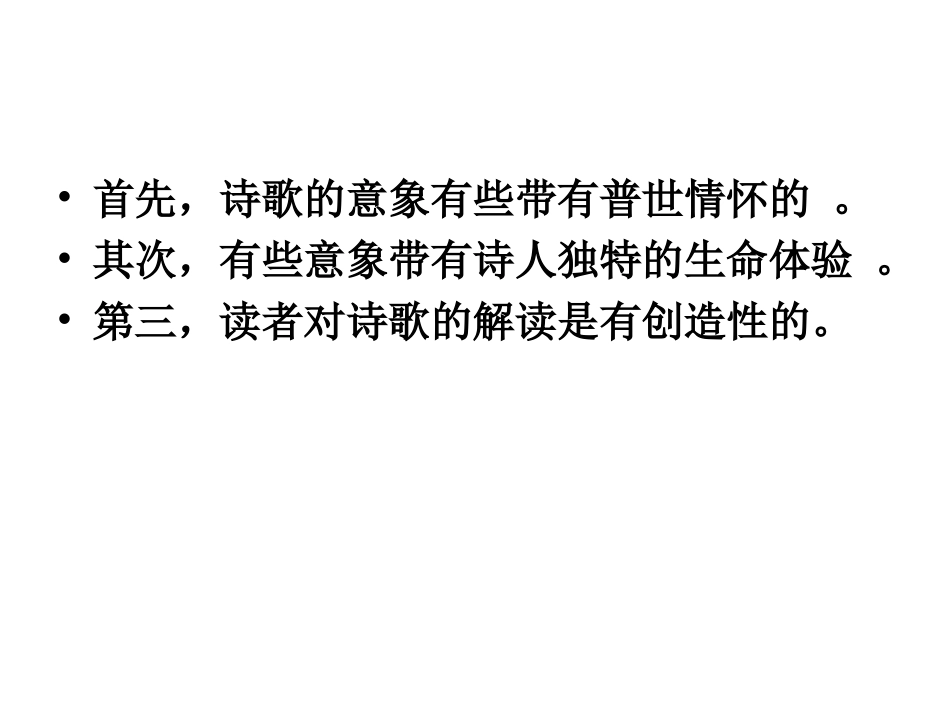相信未来•“蜘蛛网”“炉台”“灰烬”“贫困的悲哀”•“美丽的雪花”•“紫葡萄”“深秋的露水”•“我的鲜花”“别人的情怀”•“凝露的枯藤”•“孩子的笔体”•首先,诗歌的意象有些带有普世情怀的。•其次,有些意象带有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第三,读者对诗歌的解读是有创造性的。•“红卫兵”运动的兴衰,是“文化大革命”这场非理性运动的缩写。那种冲动与盲目的激情受挫之后,很快地,反思与觉醒替代了幻灭之后的沮丧,成了那个时期青年思想的主流。食指以生来与共的悲剧意识,面对这场民族的动乱,以清醒的艺术洞察力,准确无误地表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心灵与声音。•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这种复苏与觉醒是初步的,肤浅的。虽然幻灭的痛苦已经击倒他们,但还固守着旧日的精神家园,编织着已破碎的梦,大有“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气概。这种矛盾或者这种张力,使这种觉醒的感觉更加敏感。正因为如此,它们受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的热烈的欢迎。•新诗潮的重要成员们都曾宣称,食指是开辟—代诗风的先驱者。那是比1978年要早十个年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这位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天才诗人,已写出了数十首具有历史价值的光辉诗篇。他以独特的风格填补了那个特殊年代诗歌的空白,以人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再现了艺术的尊严与光荣。而他的后继者们正是在这种人格力量的启示下,开创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新篇章。•有关红卫兵•“文革”是一个多视角的旋转舞台。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毫无粉饰地争扮着自己的角色。红卫兵的主体成员——“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演显露了那个时代的阴暗与荒唐。•“文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文革”都曾利用“干部子弟”打前阵,企图控制局面。•红卫兵的肆虐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城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傲慢跋扈、冷漠清高,愚昧无知、凶横无常,就其民众性而言,红卫兵比后来得“造反派”要少得多。红卫兵运动是以与人民为敌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有关“红八月”•1966年的夏天,在北京城出现过被诗人食指喻为“波涛汹涌的海洋”的狂潮。那是一片红色的海洋。那扑天盖地的浪头出现在八月十八日的清晨的地平线上。东方红,太阳升,出升的烈日把万物染红,旗帜是红色的,袖标是红色的,领章是红色的,帽徽是红色的,古城墙也是红色的。这凝固的红色在夏日的高温下开始熔动,象红色的沥青流将文明的一切无情地覆盖了。林彪那鬼怪似的呼喊声在古都的上空回响着,挥之不去。夜幕垂降,红卫兵身披落日的余辉,挟天子之威,挥舞着手中的武装带,冲向社会。血从人的身体中喷出,染红了街道、校园。书在燃烧,文物在燃烧,在昼夜不停地开动的焚尸炉中,人的尸骨在燃烧。那腾腾的火焰也是红色的。这就是红八月,这就是高潮中的红卫兵运动。•公安部在“红八月”中曾发表公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许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红卫兵成了不被任何法律约束的无法无天之徒。抄家,杀人,破坏文物,无恶不做。仅事隔三个月,为了配合运动的发展,11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表《重要通告》,其中强调:对那些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现象要立即处理。有些在“红八月”身负血债和劣迹斑斑的东城,西城,海殿红卫兵纠察队的成员被公安局拘捕。例如:座落在天安门的西侧,中南海的东侧,人民大会堂的南侧的北京第六中学和北京第二十八中学,校内红卫兵的刑讯室曾经因其残无人道、杀人如麻而恶名远扬。遇罗克烈士在他的遗作中曾经用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过红卫兵在北京六中和二十八中犯下的罪行。这两所中学的红卫兵都有人因此而入监。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中央文革”和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的矛盾终于在毛泽东毫不退让的政治路线的贯彻中突现出来。•有关“联动”•当1967年春天,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反“中央文革”的政治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北京聚合,在1966年和1967年之交的冬季掀起了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