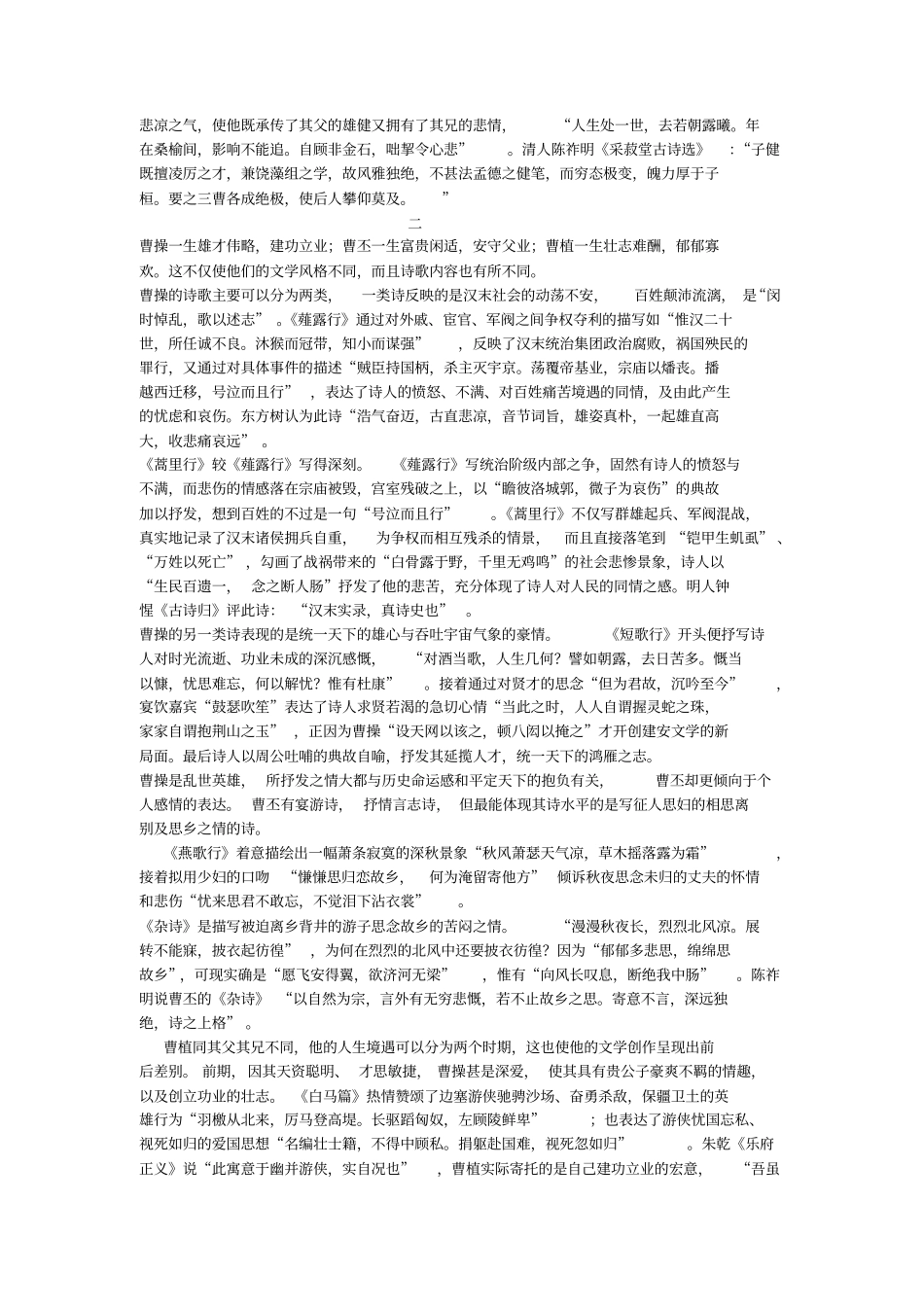浅析“三曹”人生及其诗歌创作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三曹”即汉、魏间诗人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他们政治地位显赫,文学成就很高,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关键词:三曹建安风骨刚健婉约慷慨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转变时期,此时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它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但写此心,而不虑及其余。曹氏父子是建安诗歌的集大成者,引领一代文坛。“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邈英逸,故俊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正是曹氏父子的诗歌创作为建安文学的兴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珠并光照后世。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使这三人的思想感情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形成迥异的文学内涵和艺术风格。一建安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这为想建功立业之人提供了可能,激发了士人追求功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事事多变,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这种环境为士人创造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境,从而形成了诗歌慷慨悲凉的独特格调,“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的诗歌中更是充满了“高古之骨,苍凉之气”(钟惺《古诗归》),但由于性格、际遇的不同,这种慷慨悲凉之气亦各有不同。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是一个很有胆识的统治者。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在他的诗歌中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有军事家的豪迈壮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文学家的深邃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由于他一生戎马倥璁,因此“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如《观沧海》中对波涛水阔、海岛耸立、草木繁盛、气象万千的描写有吞吐宇宙之势。徐世薄讲:“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在曹操的诗文中也有悲凉之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其诗还是以豪迈纵横、气韵沉雄为主调。曹操的诗苍劲雄浑,开一代诗风,鲜明地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特色。“诗有文之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敏感而多情,对人生的凄凉惆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多了悲凉之感而少了豪迈之气。“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欢?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催肝肺”,“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曹丕的诗清丽婉转,低徊哀怨,一改其父的豪迈之气,而充满“婉娈细秀”的公子气、文士气。“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曹植是建安诗的集大成者,古人称为“建安之杰”。他的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生乎乱,长乎军”,曾随父“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这使他少年得志,豪情满怀,诗也呈现出慷慨之情,“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但是后来的政治囚徒生活,给他的慷慨笼罩了一层悲凉之气,使他既承传了其父的雄健又拥有了其兄的悲情,“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曦。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挈令心悲”。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子健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