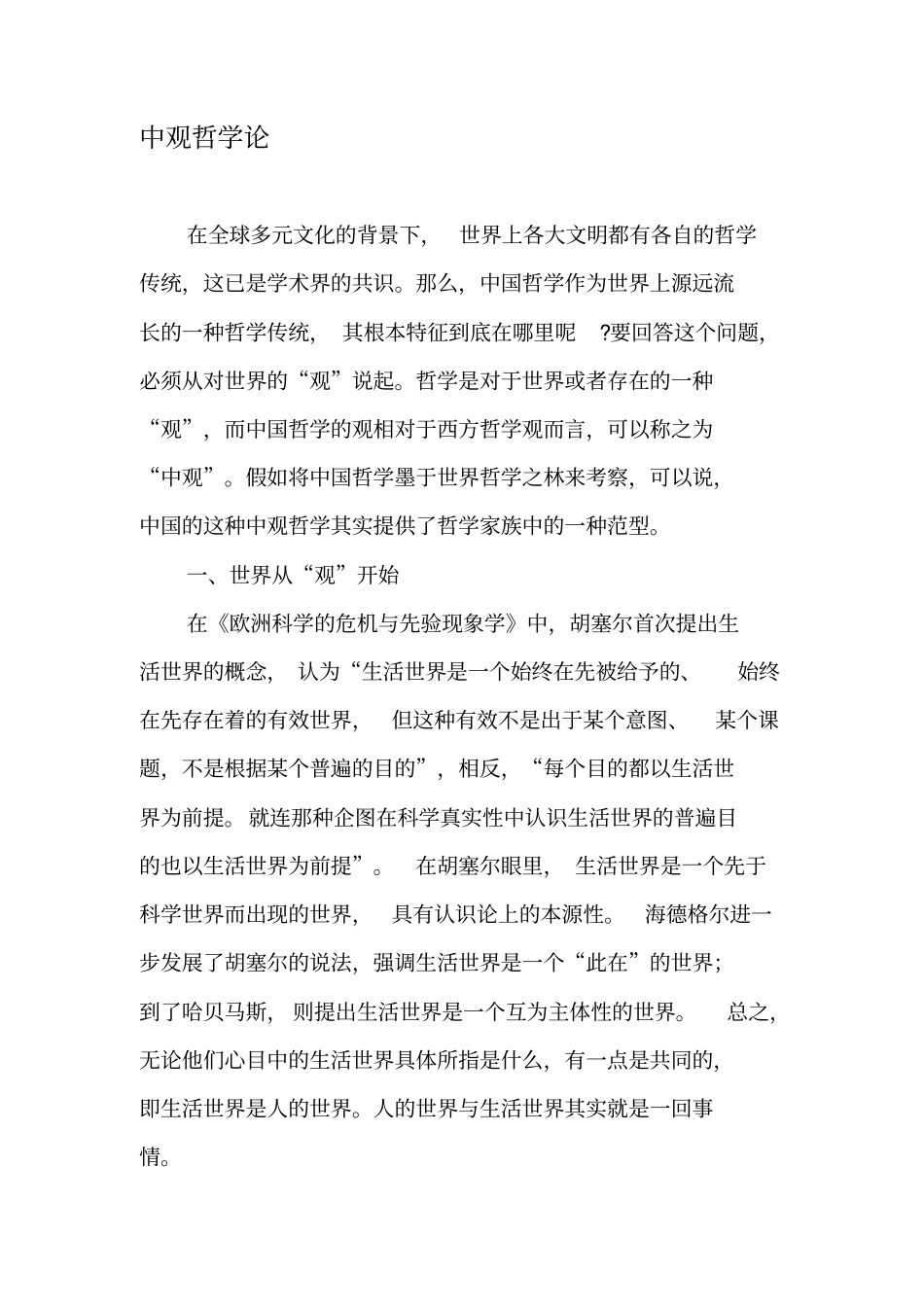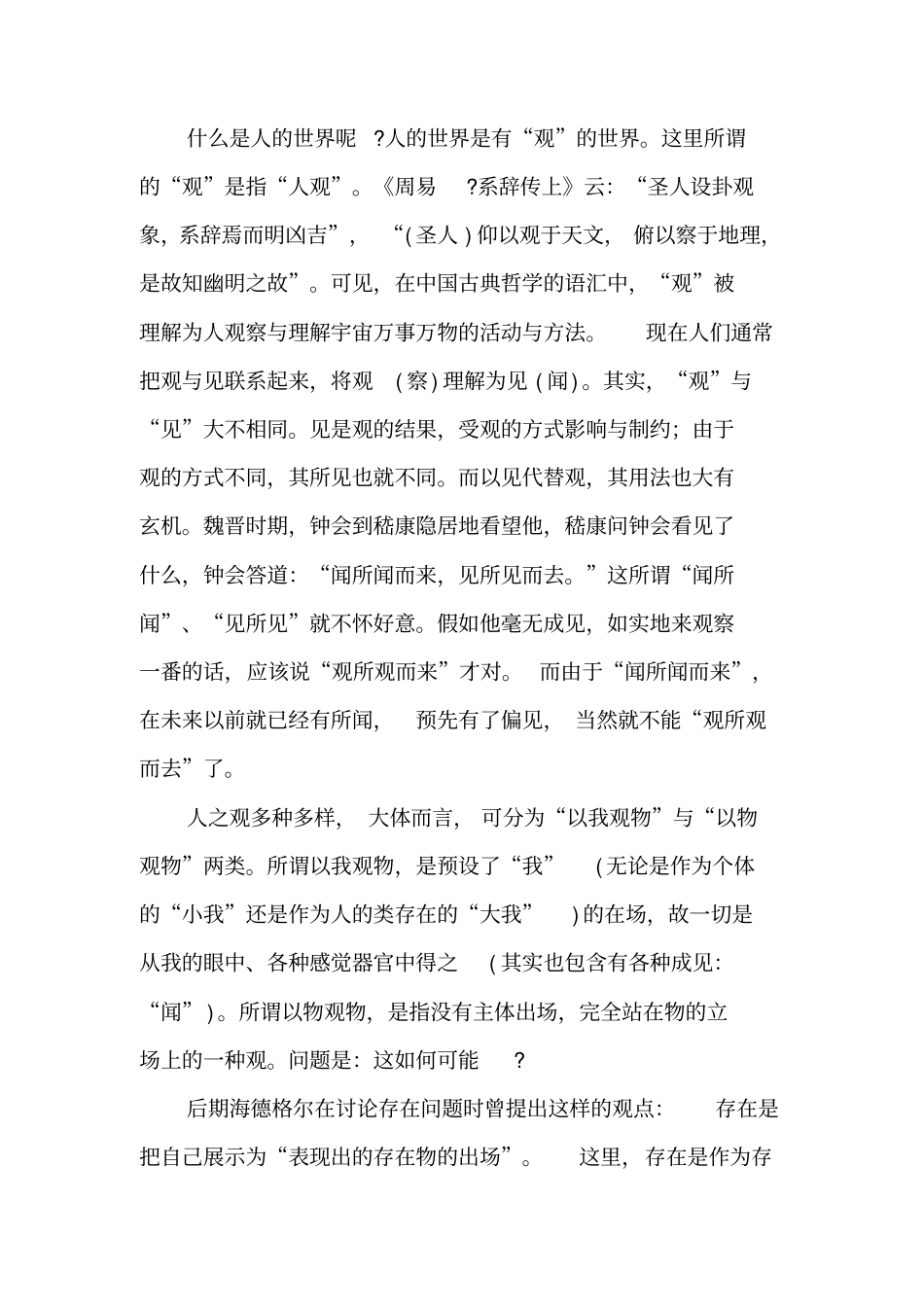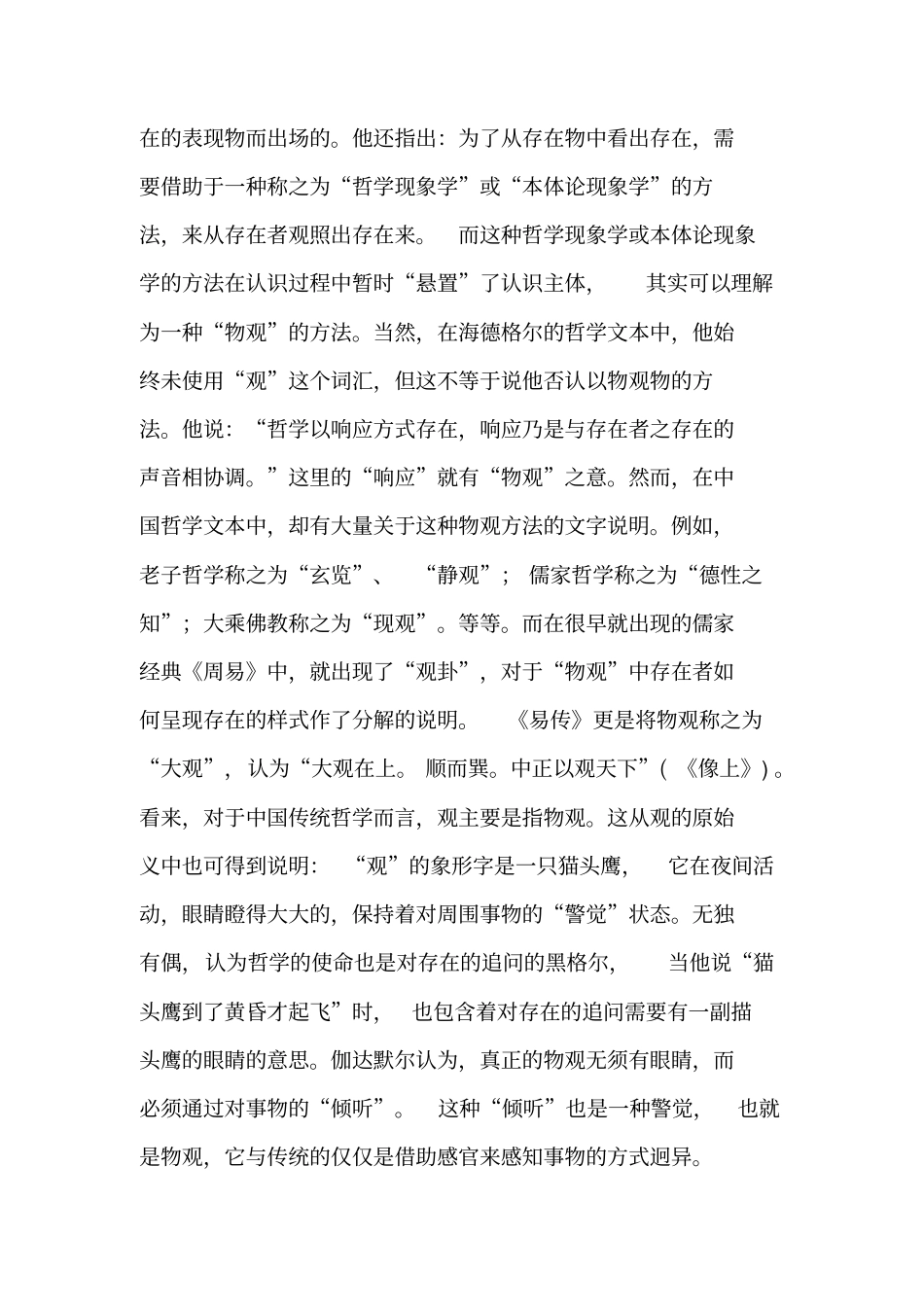中观哲学论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世界上各大文明都有各自的哲学传统,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那么,中国哲学作为世界上源远流长的一种哲学传统,其根本特征到底在哪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对世界的“观”说起。哲学是对于世界或者存在的一种“观”,而中国哲学的观相对于西方哲学观而言,可以称之为“中观”。假如将中国哲学墨于世界哲学之林来考察,可以说,中国的这种中观哲学其实提供了哲学家族中的一种范型。一、世界从“观”开始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首次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的有效世界,但这种有效不是出于某个意图、某个课题,不是根据某个普遍的目的”,相反,“每个目的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就连那种企图在科学真实性中认识生活世界的普遍目的也以生活世界为前提”。在胡塞尔眼里,生活世界是一个先于科学世界而出现的世界,具有认识论上的本源性。海德格尔进一步发展了胡塞尔的说法,强调生活世界是一个“此在”的世界;到了哈贝马斯,则提出生活世界是一个互为主体性的世界。总之,无论他们心目中的生活世界具体所指是什么,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生活世界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与生活世界其实就是一回事情。什么是人的世界呢?人的世界是有“观”的世界。这里所谓的“观”是指“人观”。《周易?系辞传上》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凶吉”,“(圣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可见,在中国古典哲学的语汇中,“观”被理解为人观察与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活动与方法。现在人们通常把观与见联系起来,将观(察)理解为见(闻)。其实,“观”与“见”大不相同。见是观的结果,受观的方式影响与制约;由于观的方式不同,其所见也就不同。而以见代替观,其用法也大有玄机。魏晋时期,钟会到嵇康隐居地看望他,嵇康问钟会看见了什么,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所谓“闻所闻”、“见所见”就不怀好意。假如他毫无成见,如实地来观察一番的话,应该说“观所观而来”才对。而由于“闻所闻而来”,在未来以前就已经有所闻,预先有了偏见,当然就不能“观所观而去”了。人之观多种多样,大体而言,可分为“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两类。所谓以我观物,是预设了“我”(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小我”还是作为人的类存在的“大我”)的在场,故一切是从我的眼中、各种感觉器官中得之(其实也包含有各种成见:“闻”)。所谓以物观物,是指没有主体出场,完全站在物的立场上的一种观。问题是:这如何可能?后期海德格尔在讨论存在问题时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存在是把自己展示为“表现出的存在物的出场”。这里,存在是作为存在的表现物而出场的。他还指出:为了从存在物中看出存在,需要借助于一种称之为“哲学现象学”或“本体论现象学”的方法,来从存在者观照出存在来。而这种哲学现象学或本体论现象学的方法在认识过程中暂时“悬置”了认识主体,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物观”的方法。当然,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文本中,他始终未使用“观”这个词汇,但这不等于说他否认以物观物的方法。他说:“哲学以响应方式存在,响应乃是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相协调。”这里的“响应”就有“物观”之意。然而,在中国哲学文本中,却有大量关于这种物观方法的文字说明。例如,老子哲学称之为“玄览”、“静观”;儒家哲学称之为“德性之知”;大乘佛教称之为“现观”。等等。而在很早就出现的儒家经典《周易》中,就出现了“观卦”,对于“物观”中存在者如何呈现存在的样式作了分解的说明。《易传》更是将物观称之为“大观”,认为“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像上》)。看来,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观主要是指物观。这从观的原始义中也可得到说明:“观”的象形字是一只猫头鹰,它在夜间活动,眼睛瞪得大大的,保持着对周围事物的“警觉”状态。无独有偶,认为哲学的使命也是对存在的追问的黑格尔,当他说“猫头鹰到了黄昏才起飞”时,也包含着对存在的追问需要有一副描头鹰的眼睛的意思。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物观无须有眼睛,而必须通过对事物的“倾听”。这种“倾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