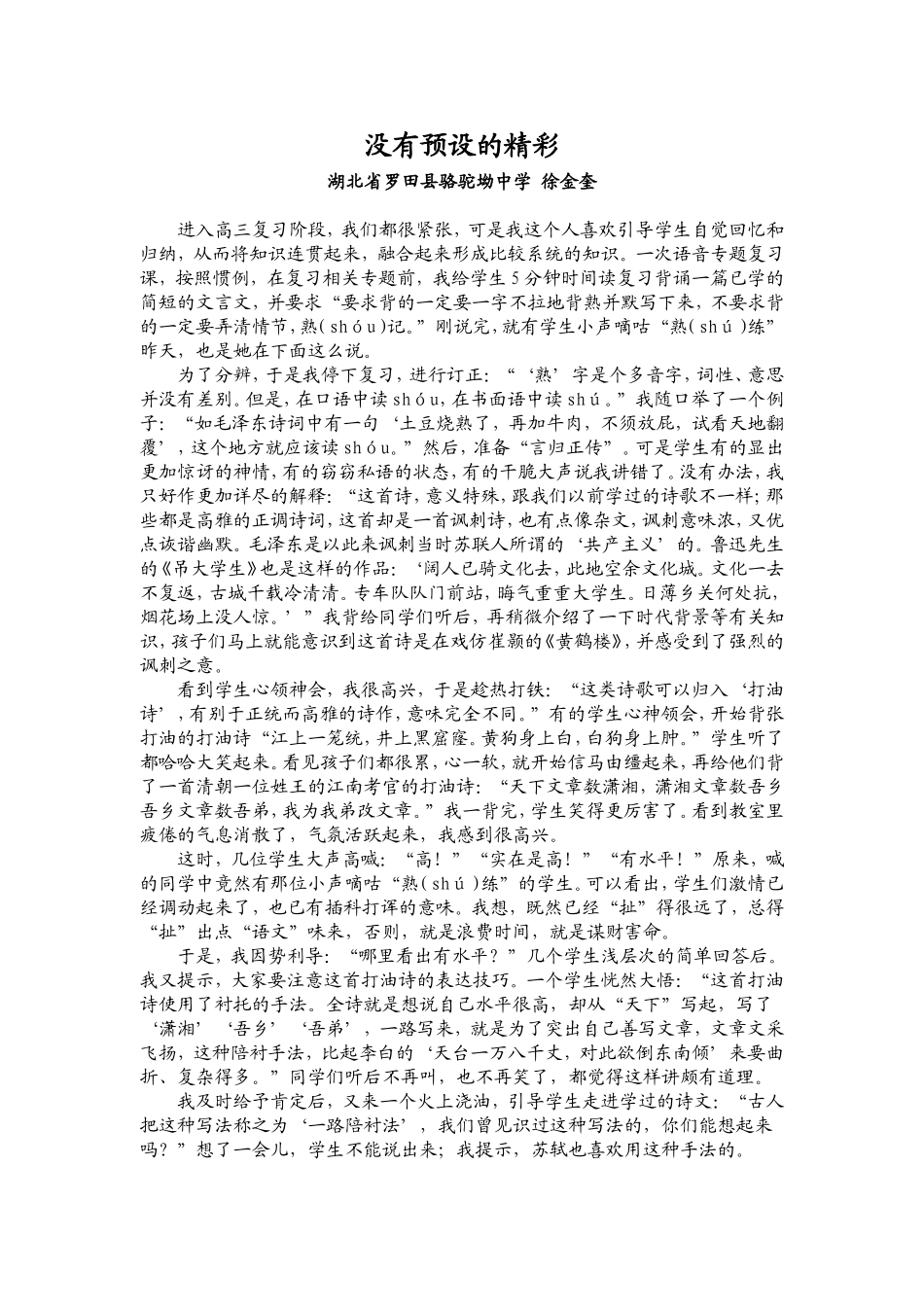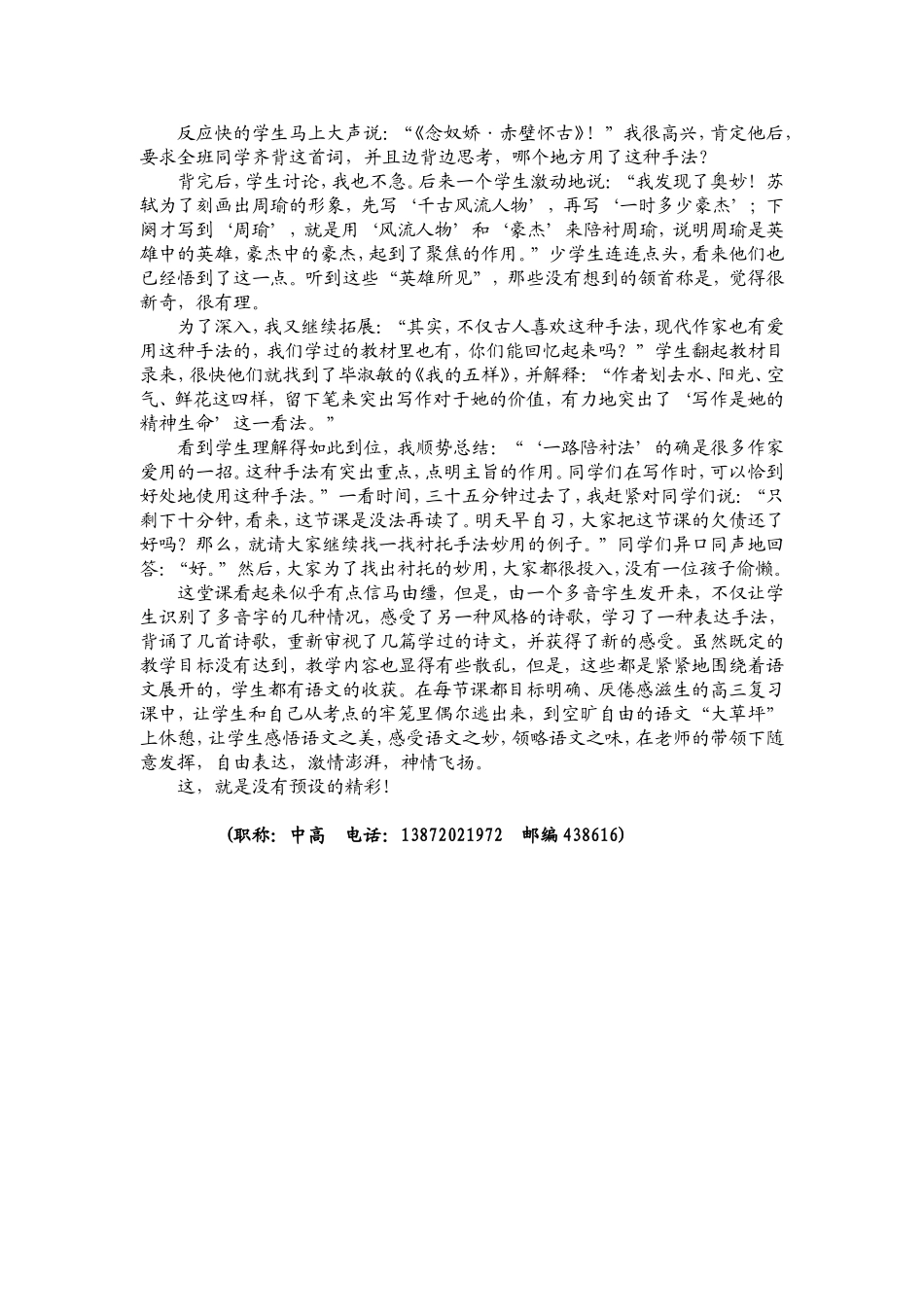没有预设的精彩湖北省罗田县骆驼坳中学徐金奎进入高三复习阶段,我们都很紧张,可是我这个人喜欢引导学生自觉回忆和归纳,从而将知识连贯起来,融合起来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一次语音专题复习课,按照惯例,在复习相关专题前,我给学生5分钟时间读复习背诵一篇已学的简短的文言文,并要求“要求背的一定要一字不拉地背熟并默写下来,不要求背的一定要弄清情节,熟(shóu)记。”刚说完,就有学生小声嘀咕“熟(shú)练”昨天,也是她在下面这么说。为了分辨,于是我停下复习,进行订正:“‘熟’字是个多音字,词性、意思并没有差别。但是,在口语中读shóu,在书面语中读shú。”我随口举了一个例子:“如毛泽东诗词中有一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个地方就应该读shóu。”然后,准备“言归正传”。可是学生有的显出更加惊讶的神情,有的窃窃私语的状态,有的干脆大声说我讲错了。没有办法,我只好作更加详尽的解释:“这首诗,意义特殊,跟我们以前学过的诗歌不一样;那些都是高雅的正调诗词,这首却是一首讽刺诗,也有点像杂文,讽刺意味浓,又优点诙谐幽默。毛泽东是以此来讽刺当时苏联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鲁迅先生的《吊大学生》也是这样的作品:‘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门前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乡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我背给同学们听后,再稍微介绍了一下时代背景等有关知识,孩子们马上就能意识到这首诗是在戏仿崔颢的《黄鹤楼》,并感受到了强烈的讽刺之意。看到学生心领神会,我很高兴,于是趁热打铁:“这类诗歌可以归入‘打油诗’,有别于正统而高雅的诗作,意味完全不同。”有的学生心神领会,开始背张打油的打油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学生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看见孩子们都很累,心一软,就开始信马由缰起来,再给他们背了一首清朝一位姓王的江南考官的打油诗:“天下文章数潇湘,潇湘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我为我弟改文章。”我一背完,学生笑得更厉害了。看到教室里疲倦的气息消散了,气氛活跃起来,我感到很高兴。这时,几位学生大声高喊:“高!”“实在是高!”“有水平!”原来,喊的同学中竟然有那位小声嘀咕“熟(shú)练”的学生。可以看出,学生们激情已经调动起来了,也已有插科打诨的意味。我想,既然已经“扯”得很远了,总得“扯”出点“语文”味来,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就是谋财害命。于是,我因势利导:“哪里看出有水平?”几个学生浅层次的简单回答后。我又提示,大家要注意这首打油诗的表达技巧。一个学生恍然大悟:“这首打油诗使用了衬托的手法。全诗就是想说自己水平很高,却从“天下”写起,写了‘潇湘’‘吾乡’‘吾弟’,一路写来,就是为了突出自己善写文章,文章文采飞扬,这种陪衬手法,比起李白的‘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来要曲折、复杂得多。”同学们听后不再叫,也不再笑了,都觉得这样讲颇有道理。我及时给予肯定后,又来一个火上浇油,引导学生走进学过的诗文:“古人把这种写法称之为‘一路陪衬法’,我们曾见识过这种写法的,你们能想起来吗?”想了一会儿,学生不能说出来;我提示,苏轼也喜欢用这种手法的。反应快的学生马上大声说:“《念奴娇·赤壁怀古》!”我很高兴,肯定他后,要求全班同学齐背这首词,并且边背边思考,哪个地方用了这种手法?背完后,学生讨论,我也不急。后来一个学生激动地说:“我发现了奥妙!苏轼为了刻画出周瑜的形象,先写‘千古风流人物’,再写‘一时多少豪杰’;下阕才写到‘周瑜’,就是用‘风流人物’和‘豪杰’来陪衬周瑜,说明周瑜是英雄中的英雄,豪杰中的豪杰,起到了聚焦的作用。”少学生连连点头,看来他们也已经悟到了这一点。听到这些“英雄所见”,那些没有想到的颔首称是,觉得很新奇,很有理。为了深入,我又继续拓展:“其实,不仅古人喜欢这种手法,现代作家也有爱用这种手法的,我们学过的教材里也有,你们能回忆起来吗?”学生翻起教材目录来,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毕淑敏的《我的五样》,并解释:“作者划去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