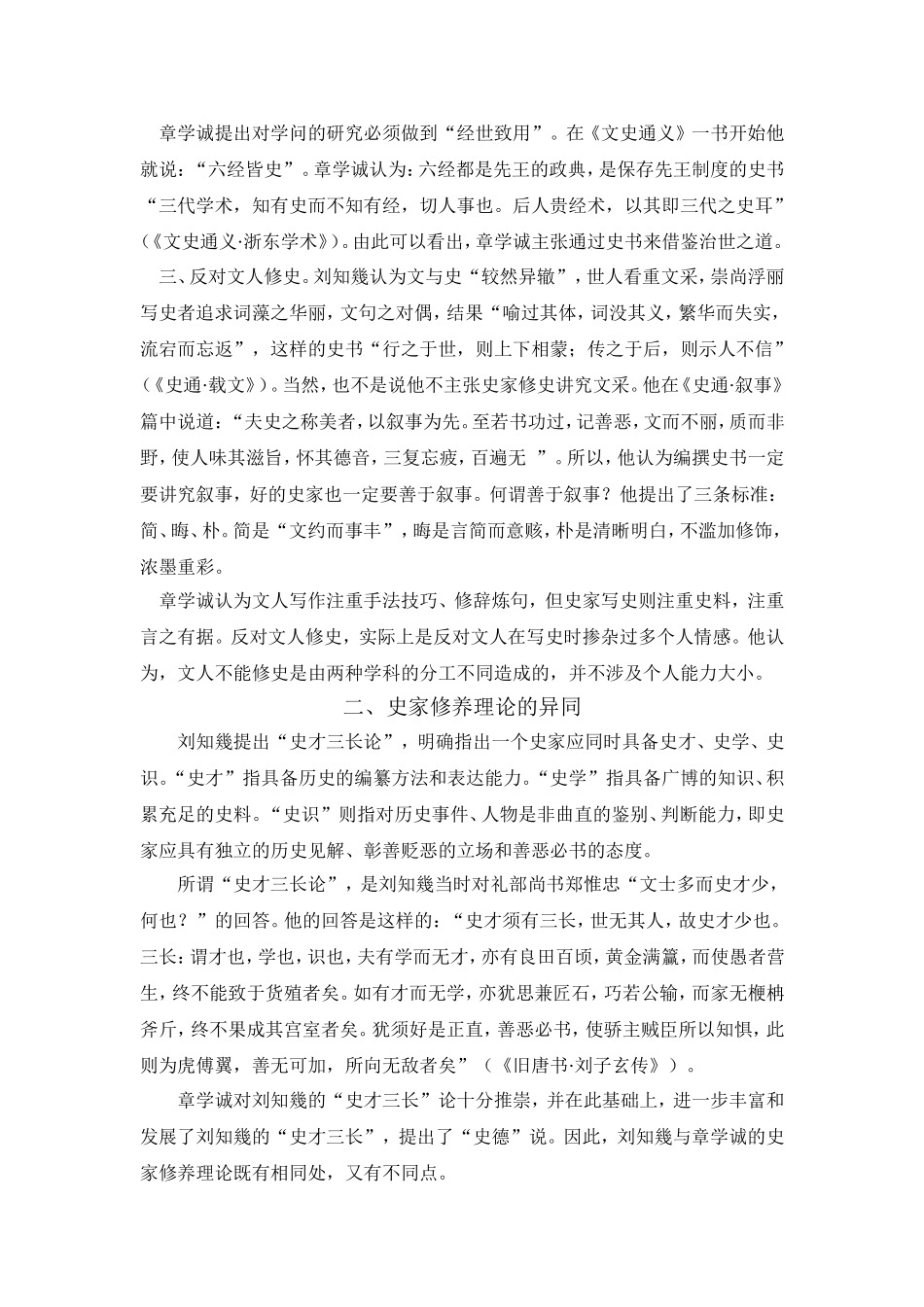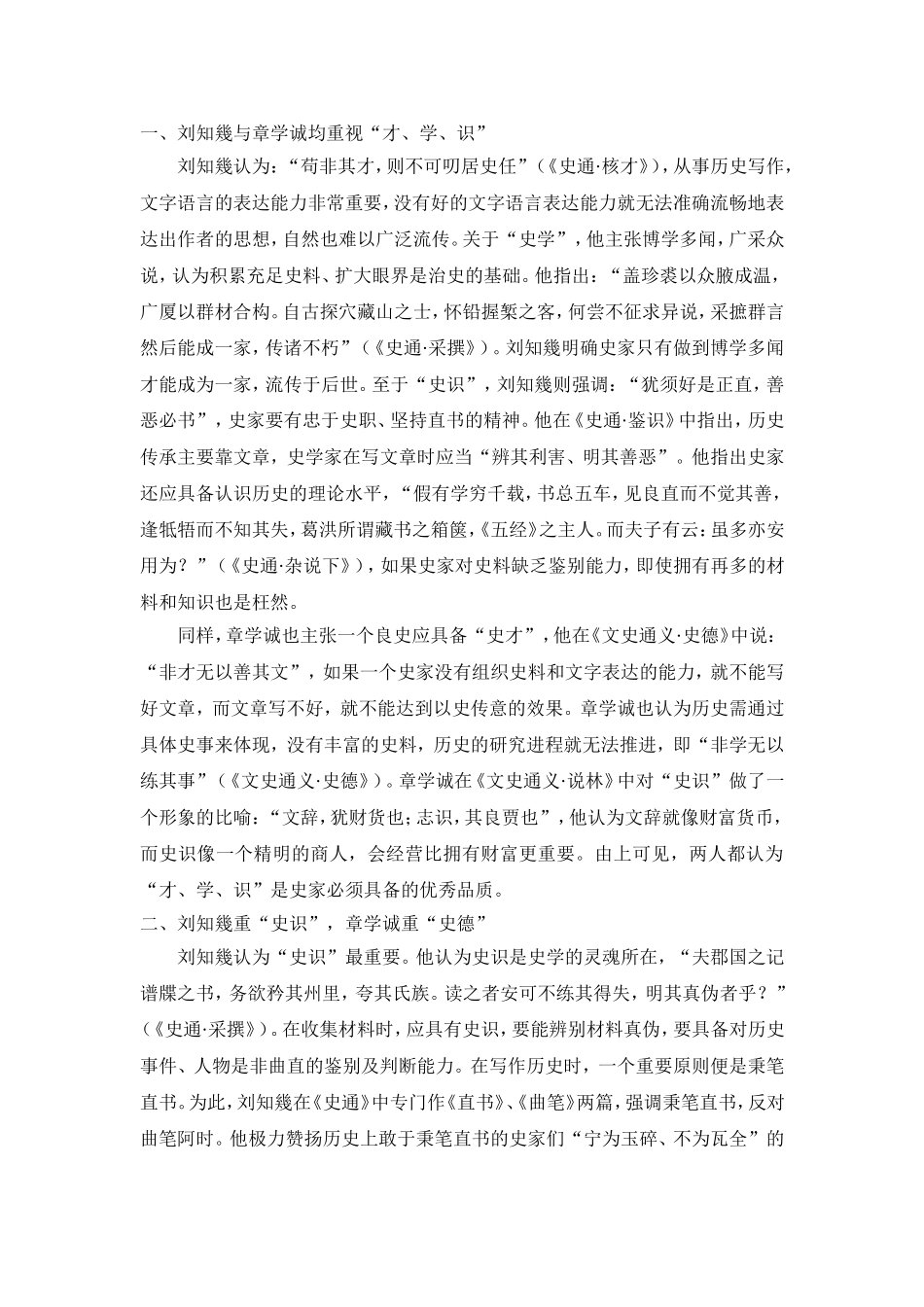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思想之比——《史通》与《文史通义》读书札记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史通》及《文史通义》则是两人思想精髓的体现,他们的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因此两人的思想在史学批判理论、史家修养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但同时两人又在史识与史德、史法与史意及史书编纂等地方各有其独到的见解。一、史学批判理论的共通之处在中国古代史学批判发展历程中,刘知幾奠定了古代史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而章学诚则完善了史学批判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因此,他们的史学批判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表现在:一、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刘知幾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两种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操守,他本人倾向于撰述能够“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他强调史家写史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史通·直书》)。在史书文风上,他强调贵在“质朴”,切不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史通·载言》),否则就会在写作时失实,导致以文害事。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幾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即在史书的书写中应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测成分。二、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即“经世致用”。刘知幾在修史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立言宗旨。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同时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笔》),他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章学诚提出对学问的研究必须做到“经世致用”。在《文史通义》一书开始他就说:“六经皆史”。章学诚认为: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是保存先王制度的史书“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主张通过史书来借鉴治世之道。三、反对文人修史。刘知幾认为文与史“较然异辙”,世人看重文采,崇尚浮丽写史者追求词藻之华丽,文句之对偶,结果“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这样的史书“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史通·载文》)。当然,也不是说他不主张史家修史讲究文采。他在《史通·叙事》篇中说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所以,他认为编撰史书一定要讲究叙事,好的史家也一定要善于叙事。何谓善于叙事?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简、晦、朴。简是“文约而事丰”,晦是言简而意赅,朴是清晰明白,不滥加修饰,浓墨重彩。章学诚认为文人写作注重手法技巧、修辞炼句,但史家写史则注重史料,注重言之有据。反对文人修史,实际上是反对文人在写史时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他认为,文人不能修史是由两种学科的分工不同造成的,并不涉及个人能力大小。二、史家修养理论的异同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明确指出一个史家应同时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指具备历史的编纂方法和表达能力。“史学”指具备广博的知识、积累充足的史料。“史识”则指对历史事件、人物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即史家应具有独立的历史见解、彰善贬恶的立场和善恶必书的态度。所谓“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幾当时对礼部尚书郑惟忠“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的回答。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