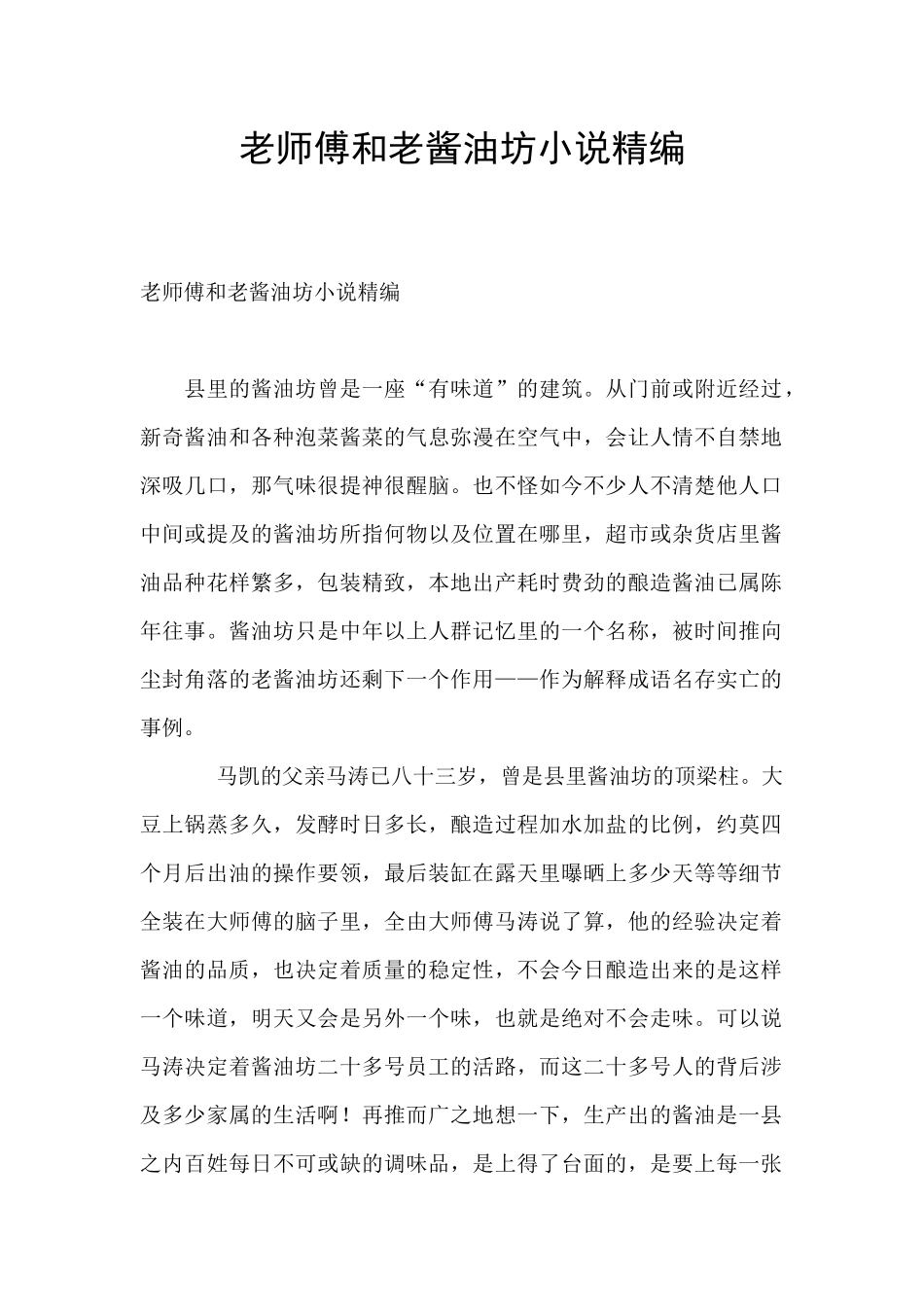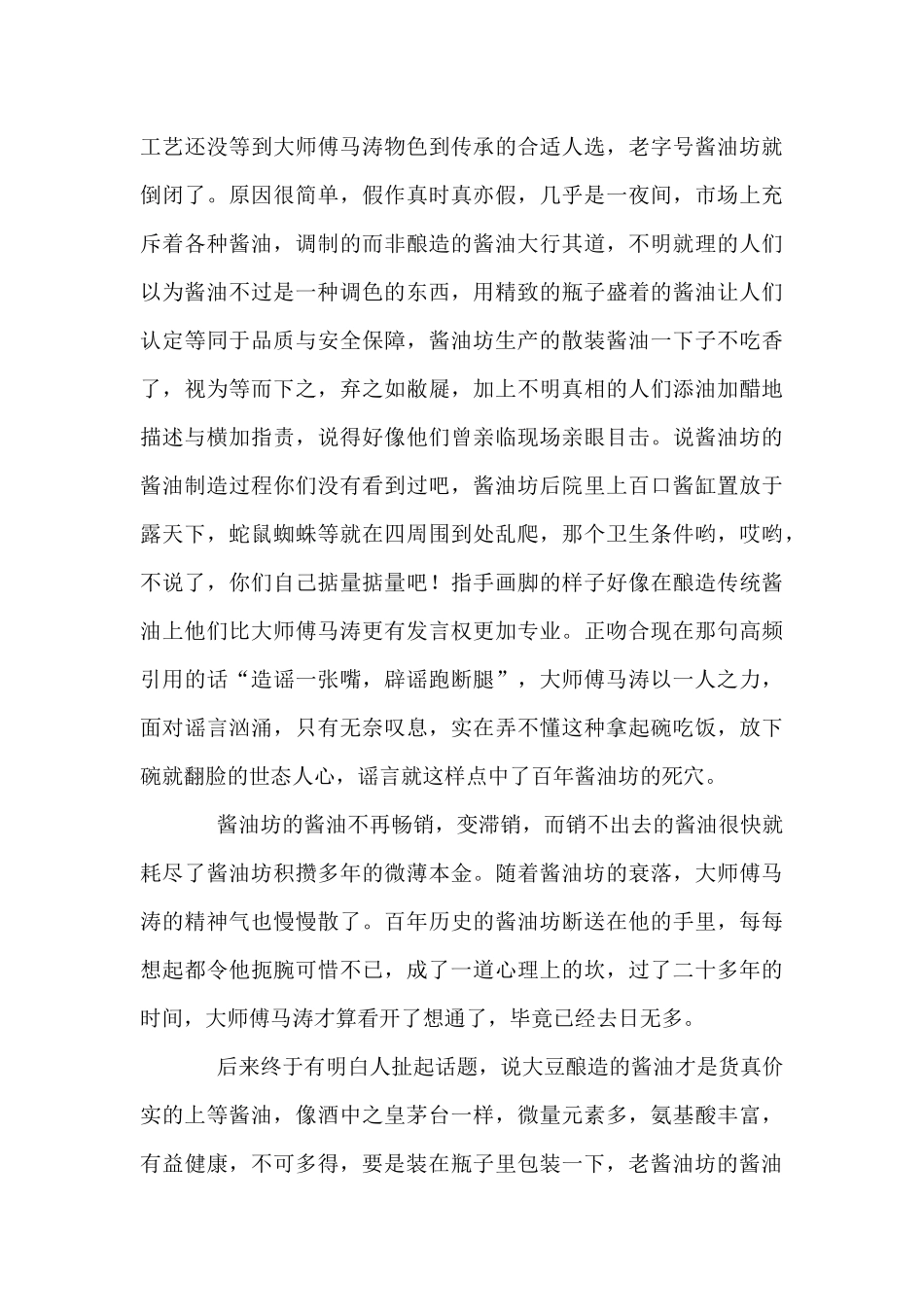老师傅和老酱油坊小说精编 老师傅和老酱油坊小说精编 县里的酱油坊曾是一座“有味道”的建筑。从门前或附近经过,新奇酱油和各种泡菜酱菜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深吸几口,那气味很提神很醒脑。也不怪如今不少人不清楚他人口中间或提及的酱油坊所指何物以及位置在哪里,超市或杂货店里酱油品种花样繁多,包装精致,本地出产耗时费劲的酿造酱油已属陈年往事。酱油坊只是中年以上人群记忆里的一个名称,被时间推向尘封角落的老酱油坊还剩下一个作用——作为解释成语名存实亡的事例。 马凯的父亲马涛已八十三岁,曾是县里酱油坊的顶梁柱。大豆上锅蒸多久,发酵时日多长,酿造过程加水加盐的比例,约莫四个月后出油的操作要领,最后装缸在露天里曝晒上多少天等等细节全装在大师傅的脑子里,全由大师傅马涛说了算,他的经验决定着酱油的品质,也决定着质量的稳定性,不会今日酿造出来的是这样一个味道,明天又会是另外一个味,也就是绝对不会走味。可以说马涛决定着酱油坊二十多号员工的活路,而这二十多号人的背后涉及多少家属的生活啊!再推而广之地想一下,生产出的酱油是一县之内百姓每日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是上得了台面的,是要上每一张饭桌的,是要进入几乎每一道菜的。说得夸张一些,一县之内,缺个县长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徽菜素来重油重酱色重火功,若是没有了酱油,老百姓不答应,生活虽说不会停摆,但生活就会不得劲,少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打了一个让人不快乐的折扣。能吃得上酱油,吃得起酱油,是日子风平浪静的一种外在表现,是生活还能顺风顺水继续下去的一种符号象征!退一万步来讲,没有菜,打个酱油汤呗,嘴里没味,搞个酱油拌饭呗,贫富的日子都离不开这个玩意儿。回忆起来,当年在本地打酱油曾经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事情之一,是一件日子过得还算不赖的标志。那时的酱油真是够味啊,领命去打酱油的孩子往往一脸兴奋,这是莫大的荣誉,也是家长给的额外福利,在打回酱油的路上,伸出小舌条愉快地舔一舔酱油瓶口的事情,信任有大把大把孩子干过吧! 马涛作为酱油坊的大师傅很吃香,举足轻重,想不受人敬重都不行啊,实力不允许。鉴别什么品质的大豆用于酿造酱油不会出问题,闻一闻发酵中的大豆的气味,探一探大缸中的温度,真正意义上的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就知行不行!蒸豆、制曲、发酵、酿制、出油、曝晒这些技术问题说起来简单,实际过程却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最具技术含量的细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