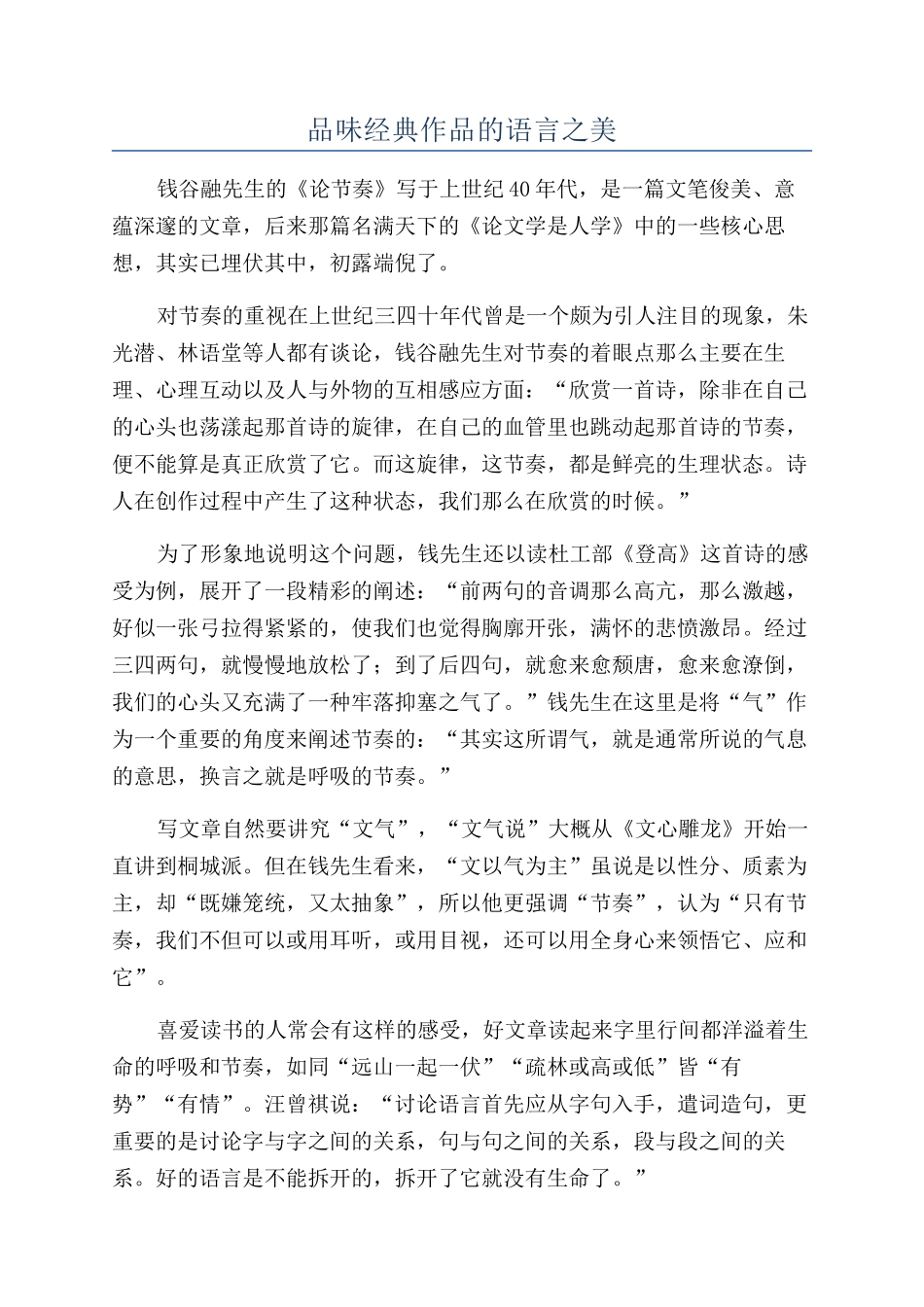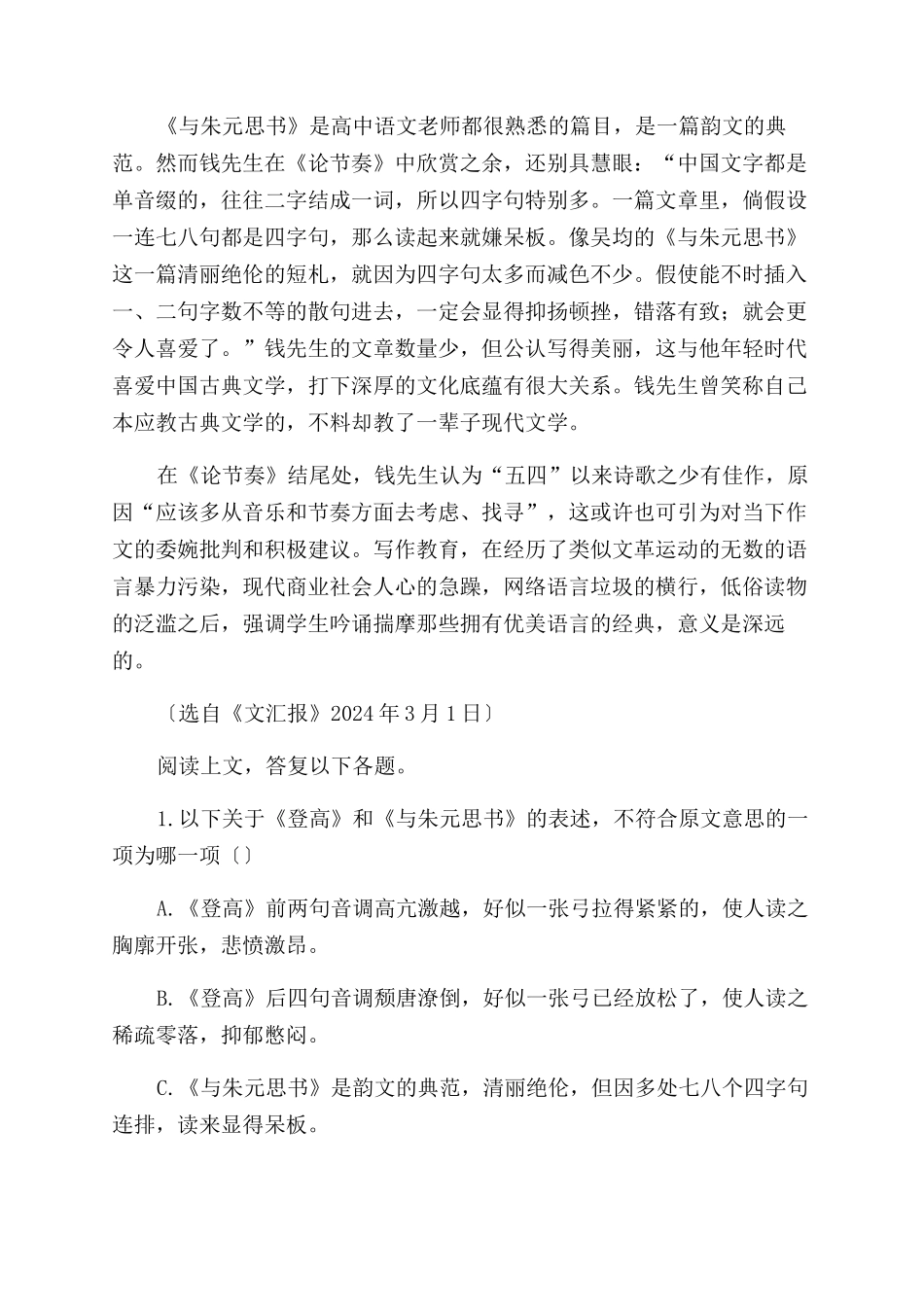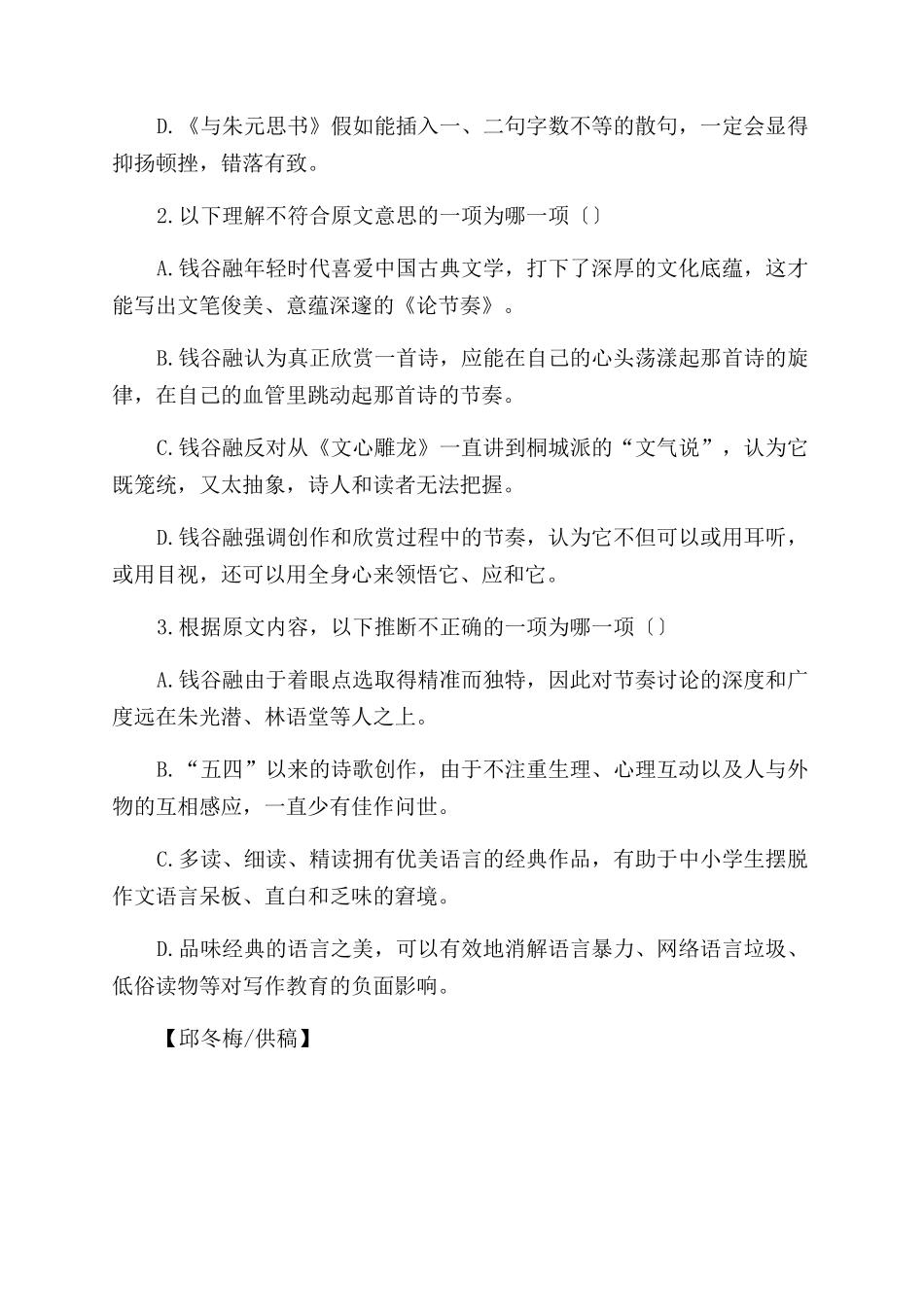品味经典作品的语言之美钱谷融先生的《论节奏》写于上世纪 40 年代,是一篇文笔俊美、意蕴深邃的文章,后来那篇名满天下的《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一些核心思想,其实已埋伏其中,初露端倪了。对节奏的重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朱光潜、林语堂等人都有谈论,钱谷融先生对节奏的着眼点那么主要在生理、心理互动以及人与外物的互相感应方面:“欣赏一首诗,除非在自己的心头也荡漾起那首诗的旋律,在自己的血管里也跳动起那首诗的节奏,便不能算是真正欣赏了它。而这旋律,这节奏,都是鲜亮的生理状态。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产生了这种状态,我们那么在欣赏的时候。”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钱先生还以读杜工部《登高》这首诗的感受为例,展开了一段精彩的阐述:“前两句的音调那么高亢,那么激越,好似一张弓拉得紧紧的,使我们也觉得胸廓开张,满怀的悲愤激昂。经过三四两句,就慢慢地放松了;到了后四句,就愈来愈颓唐,愈来愈潦倒,我们的心头又充满了一种牢落抑塞之气了。”钱先生在这里是将“气”作为一个重要的角度来阐述节奏的:“其实这所谓气,就是通常所说的气息的意思,换言之就是呼吸的节奏。”写文章自然要讲究“文气”,“文气说”大概从《文心雕龙》开始一直讲到桐城派。但在钱先生看来,“文以气为主”虽说是以性分、质素为主,却“既嫌笼统,又太抽象”,所以他更强调“节奏”,认为“只有节奏,我们不但可以或用耳听,或用目视,还可以用全身心来领悟它、应和它”。喜爱读书的人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好文章读起来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生命的呼吸和节奏,如同“远山一起一伏”“疏林或高或低”皆“有势”“有情”。汪曾祺说:“讨论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讨论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与朱元思书》是高中语文老师都很熟悉的篇目,是一篇韵文的典范。然而钱先生在《论节奏》中欣赏之余,还别具慧眼:“中国文字都是单音缀的,往往二字结成一词,所以四字句特别多。一篇文章里,倘假设一连七八句都是四字句,那么读起来就嫌呆板。像吴均的《与朱元思书》这一篇清丽绝伦的短札,就因为四字句太多而减色不少。假使能不时插入一、二句字数不等的散句进去,一定会显得抑扬顿挫,错落有致;就会更令人喜爱了。”钱先生的文章数量少,但公认写得美丽,这与他年轻时代喜爱中国古典文学,打下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