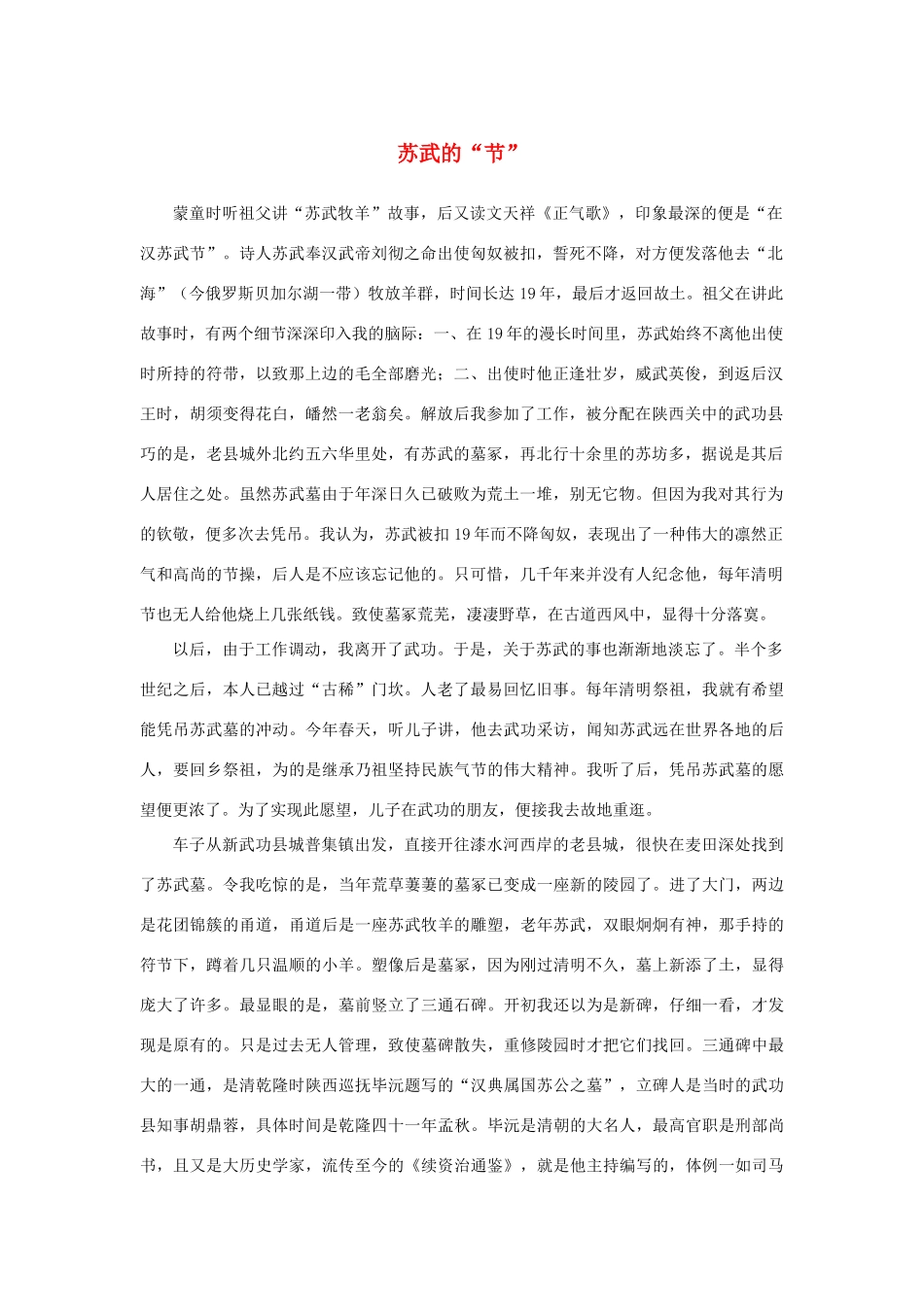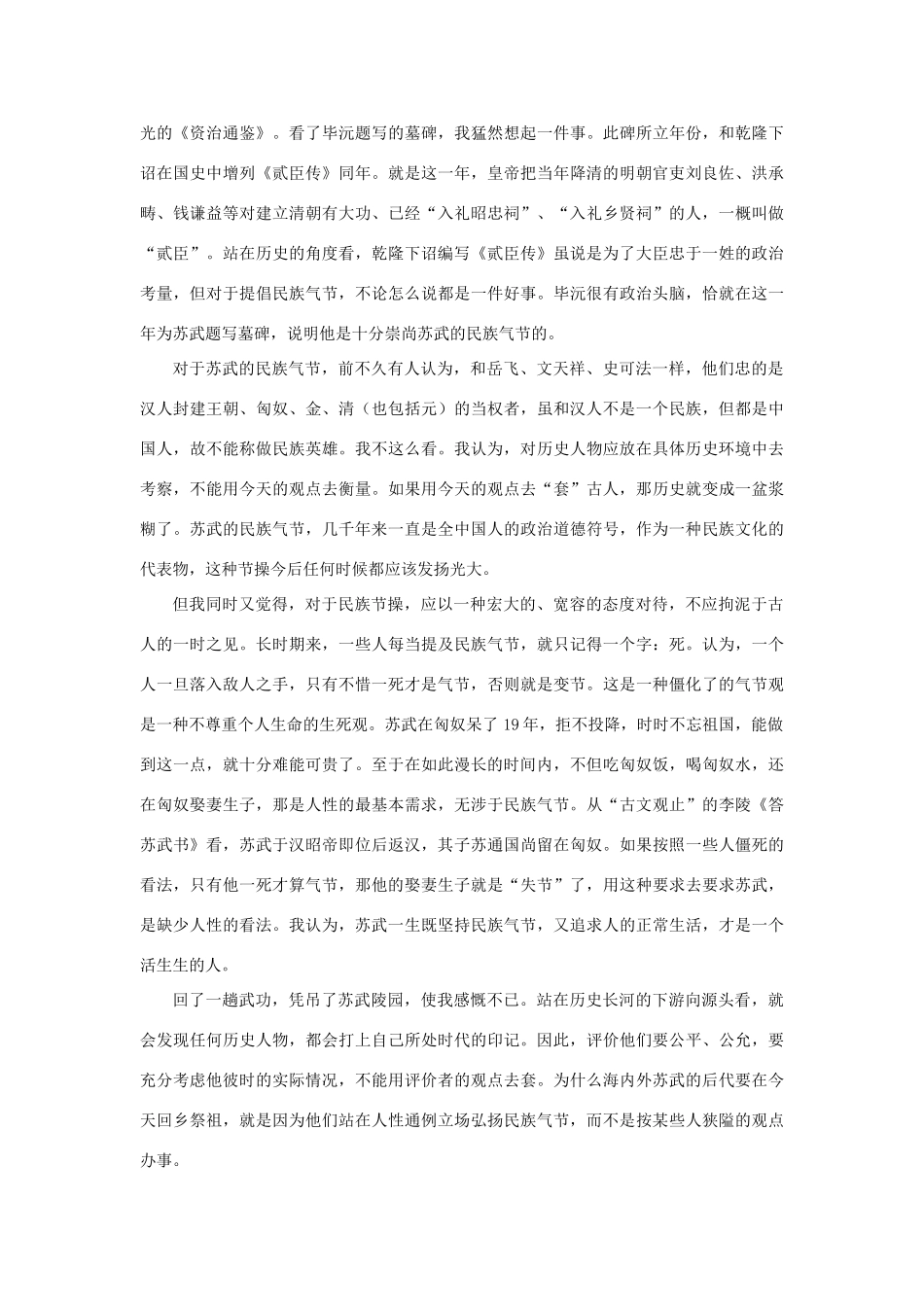苏武的“节”蒙童时听祖父讲“苏武牧羊”故事,后又读文天祥《正气歌》,印象最深的便是“在汉苏武节”。诗人苏武奉汉武帝刘彻之命出使匈奴被扣,誓死不降,对方便发落他去“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牧放羊群,时间长达 19 年,最后才返回故土。祖父在讲此故事时,有两个细节深深印入我的脑际:一、在 19 年的漫长时间里,苏武始终不离他出使时所持的符带,以致那上边的毛全部磨光;二、出使时他正逢壮岁,威武英俊,到返后汉王时,胡须变得花白,皤然一老翁矣。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在陕西关中的武功县巧的是,老县城外北约五六华里处,有苏武的墓冢,再北行十余里的苏坊多,据说是其后人居住之处。虽然苏武墓由于年深日久已破败为荒土一堆,别无它物。但因为我对其行为的钦敬,便多次去凭吊。我认为,苏武被扣 19 年而不降匈奴,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的凛然正气和高尚的节操,后人是不应该忘记他的。只可惜,几千年来并没有人纪念他,每年清明节也无人给他烧上几张纸钱。致使墓冢荒芜,凄凄野草,在古道西风中,显得十分落寞。以后,由于工作调动,我离开了武功。于是,关于苏武的事也渐渐地淡忘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本人已越过“古稀”门坎。人老了最易回忆旧事。每年清明祭祖,我就有希望能凭吊苏武墓的冲动。今年春天,听儿子讲,他去武功采访,闻知苏武远在世界各地的后人,要回乡祭祖,为的是继承乃祖坚持民族气节的伟大精神。我听了后,凭吊苏武墓的愿望便更浓了。为了实现此愿望,儿子在武功的朋友,便接我去故地重逛。车子从新武功县城普集镇出发,直接开往漆水河西岸的老县城,很快在麦田深处找到了苏武墓。令我吃惊的是,当年荒草萋萋的墓冢已变成一座新的陵园了。进了大门,两边是花团锦簇的甬道,甬道后是一座苏武牧羊的雕塑,老年苏武,双眼炯炯有神,那手持的符节下,蹲着几只温顺的小羊。塑像后是墓冢,因为刚过清明不久,墓上新添了土,显得庞大了许多。最显眼的是,墓前竖立了三通石碑。开初我还以为是新碑,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原有的。只是过去无人管理,致使墓碑散失,重修陵园时才把它们找回。三通碑中最大的一通,是清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题写的“汉典属国苏公之墓”,立碑人是当时的武功县知事胡鼎蓉,具体时间是乾隆四十一年孟秋。毕沅是清朝的大名人,最高官职是刑部尚书,且又是大历史学家,流传至今的《续资治通鉴》,就是他主持编写的,体例一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看了毕沅题写的墓碑,我猛然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