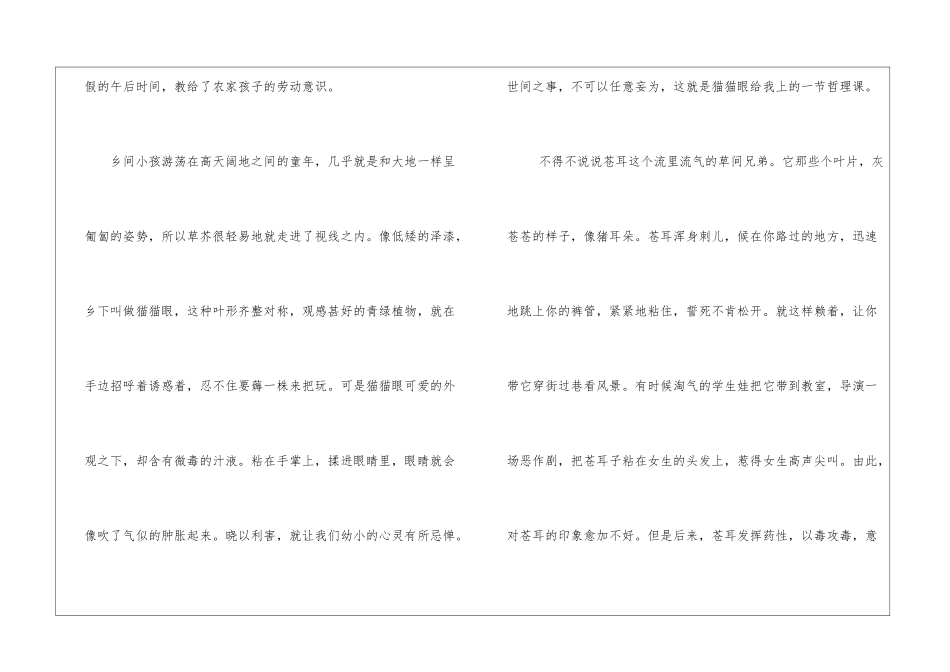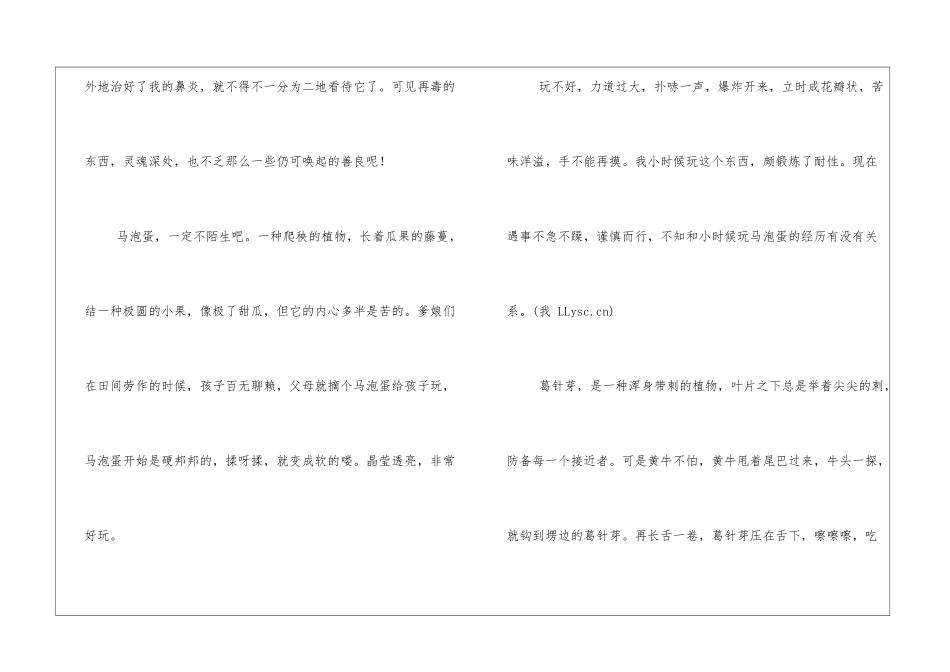(最新)芳草萋萋现代散文(推举) 每一种植物,都像是生长在乡间田塍的汉字,而野草,是其中豪放不羁的笔画。它们挤挤挨挨,丰富着广袤大地的册页。 八月间,野草就开始疯狂地扩张自己的领地。它们风风火火,蔓延在田间地头,沟崖河畔,阡陌小径,村舍墙角。彼此挤眉弄眼,摩肩接踵,喧闹着喧腾着,旁若无人地张扬个性。每一棵草芥,就是一个微小的灵魂。在生活娱乐相对枯寂落寞的乡间,通常与我沟通的,缺少不了这些野草。 我最熟悉的,当属马唐草了。十里不同名,津西地区叫抓地龙,到津东,称鸡爪草。这种东西,直立或者斜生,茎节蔓延飞快,葳蕤在荒野间,像跑在地面的绿皮火车,噌噌噌地席卷着宽阔大地。喂牛割草,马唐草是不错的选择。片刻的工夫,就能割下一竹篮子。割马唐草,算是我参加田间劳动的入门课,就如同学校汉语启蒙的“上中下,人口手”,简单而易学。割马唐草,占据了农村孩子暑假的午后时间,教给了农家孩子的劳动意识。 乡间小孩游荡在高天阔地之间的童年,几乎就是和大地一样呈匍匐的姿势,所以草芥很轻易地就走进了视线之内。像低矮的泽漆,乡下叫做猫猫眼,这种叶形齐整对称,观感甚好的青绿植物,就在手边招呼着诱惑着,忍不住要薅一株来把玩。可是猫猫眼可爱的外观之下,却含有微毒的汁液。粘在手掌上,揉进眼睛里,眼睛就会像吹了气似的肿胀起来。晓以利害,就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有所忌惮。世间之事,不可以任意妄为,这就是猫猫眼给我上的一节哲理课。 不得不说说苍耳这个流里流气的草间兄弟。它那些个叶片,灰苍苍的样子,像猪耳朵。苍耳浑身刺儿,候在你路过的地方,迅速地跳上你的裤管,紧紧地粘住,誓死不肯松开。就这样赖着,让你带它穿街过巷看风景。有时候淘气的学生娃把它带到教室,导演一场恶作剧,把苍耳子粘在女生的头发上,惹得女生高声尖叫。由此,对苍耳的印象愈加不好。但是后来,苍耳发挥药性,以毒攻毒,意外地治好了我的鼻炎,就不得不一分为二地看待它了。可见再毒的东西,灵魂深处,也不乏那么一些仍可唤起的善良呢! 马泡蛋,一定不陌生吧。一种爬秧的植物,长着瓜果的藤蔓,结一种极圆的小果,像极了甜瓜,但它的内心多半是苦的。爹娘们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孩子百无聊赖,父母就摘个马泡蛋给孩子玩,马泡蛋开始是硬邦邦的,揉呀揉,就变成软的喽。晶莹透亮,非常好玩。 玩不好,力道过大,扑哧一声,爆炸开来,立时成花瓣状,苦味洋溢,手不能再摸。我小时候玩这个东西,颇锻炼了耐性。现在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