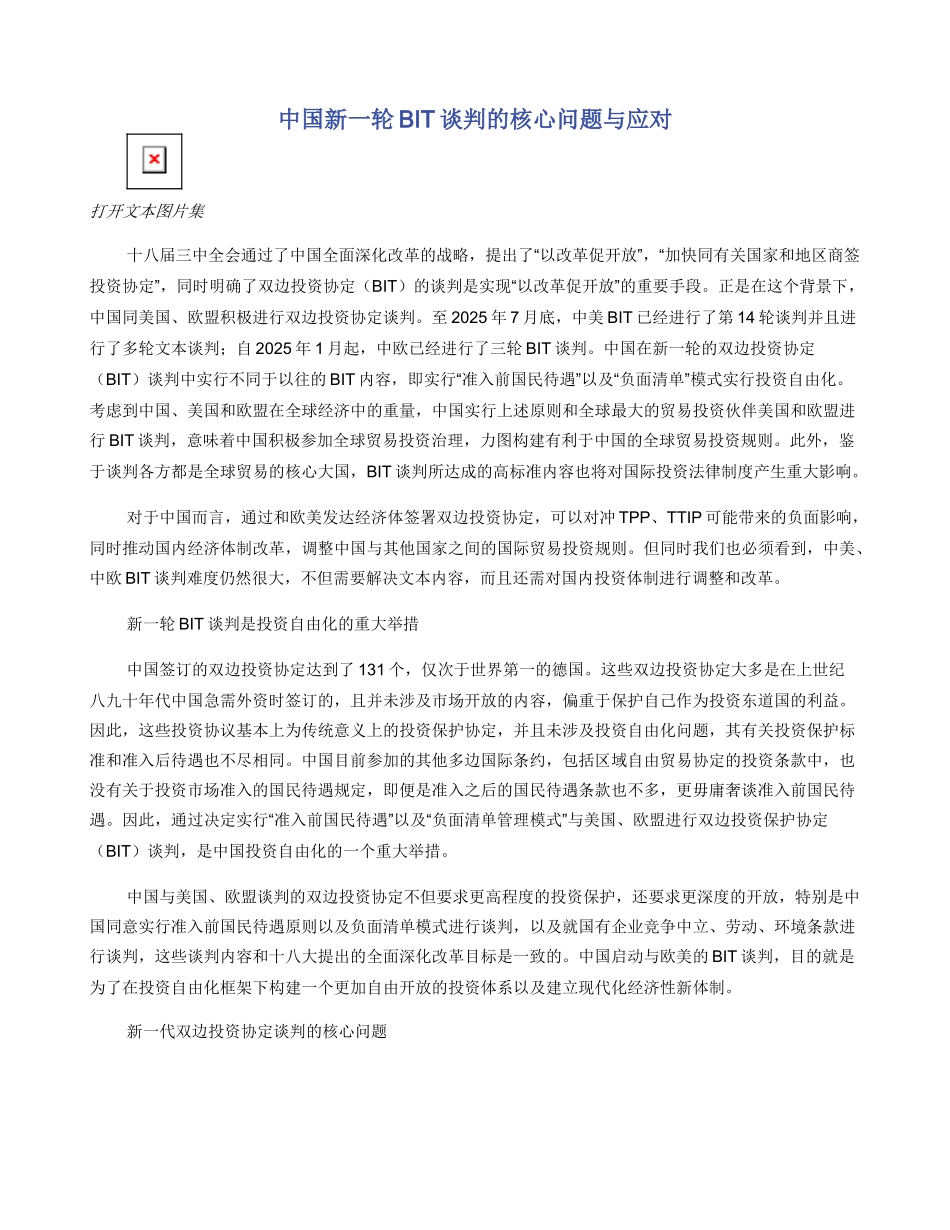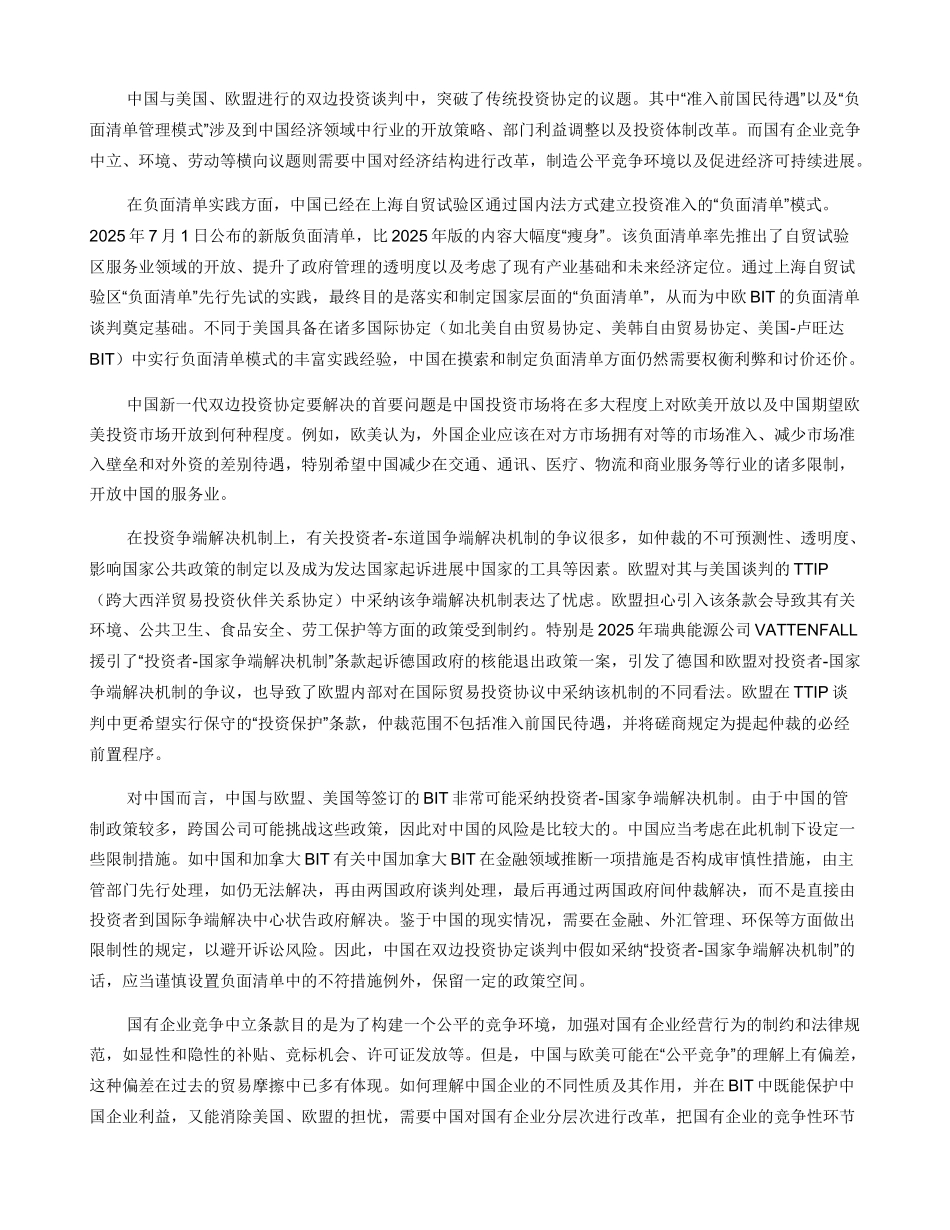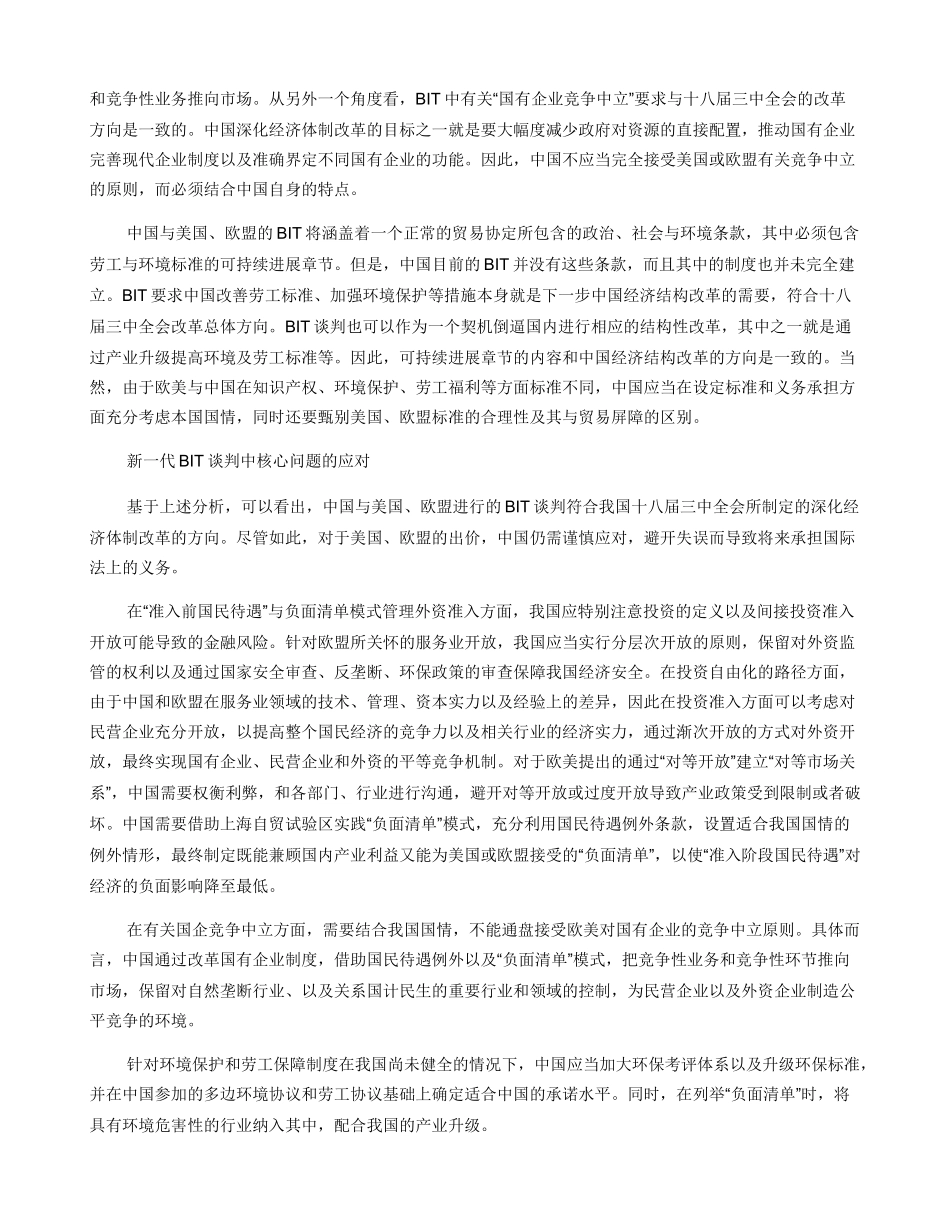中国新一轮 BIT 谈判的核心问题与应对打开文本图片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提出了“以改革促开放”,“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同时明确了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是实现“以改革促开放”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同美国、欧盟积极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至 2025 年 7 月底,中美 BIT 已经进行了第 14 轮谈判并且进行了多轮文本谈判;自 2025 年 1 月起,中欧已经进行了三轮 BIT 谈判。中国在新一轮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实行不同于以往的 BIT 内容,即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模式实行投资自由化。考虑到中国、美国和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重量,中国实行上述原则和全球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美国和欧盟进行 BIT 谈判,意味着中国积极参加全球贸易投资治理,力图构建有利于中国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此外,鉴于谈判各方都是全球贸易的核心大国,BIT 谈判所达成的高标准内容也将对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和欧美发达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对冲 TPP、TTIP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美、中欧 BIT 谈判难度仍然很大,不但需要解决文本内容,而且还需对国内投资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新一轮 BIT 谈判是投资自由化的重大举措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达到了 131 个,仅次于世界第一的德国。这些双边投资协定大多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急需外资时签订的,且并未涉及市场开放的内容,偏重于保护自己作为投资东道国的利益。因此,这些投资协议基本上为传统意义上的投资保护协定,并且未涉及投资自由化问题,其有关投资保护标准和准入后待遇也不尽相同。中国目前参加的其他多边国际条约,包括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条款中,也没有关于投资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规定,即便是准入之后的国民待遇条款也不多,更毋庸奢谈准入前国民待遇。因此,通过决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美国、欧盟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是中国投资自由化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国与美国、欧盟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不但要求更高程度的投资保护,还要求更深度的开放,特别是中国同意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以及负面清单模式进行谈判,以及就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劳动、环境条款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内容和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