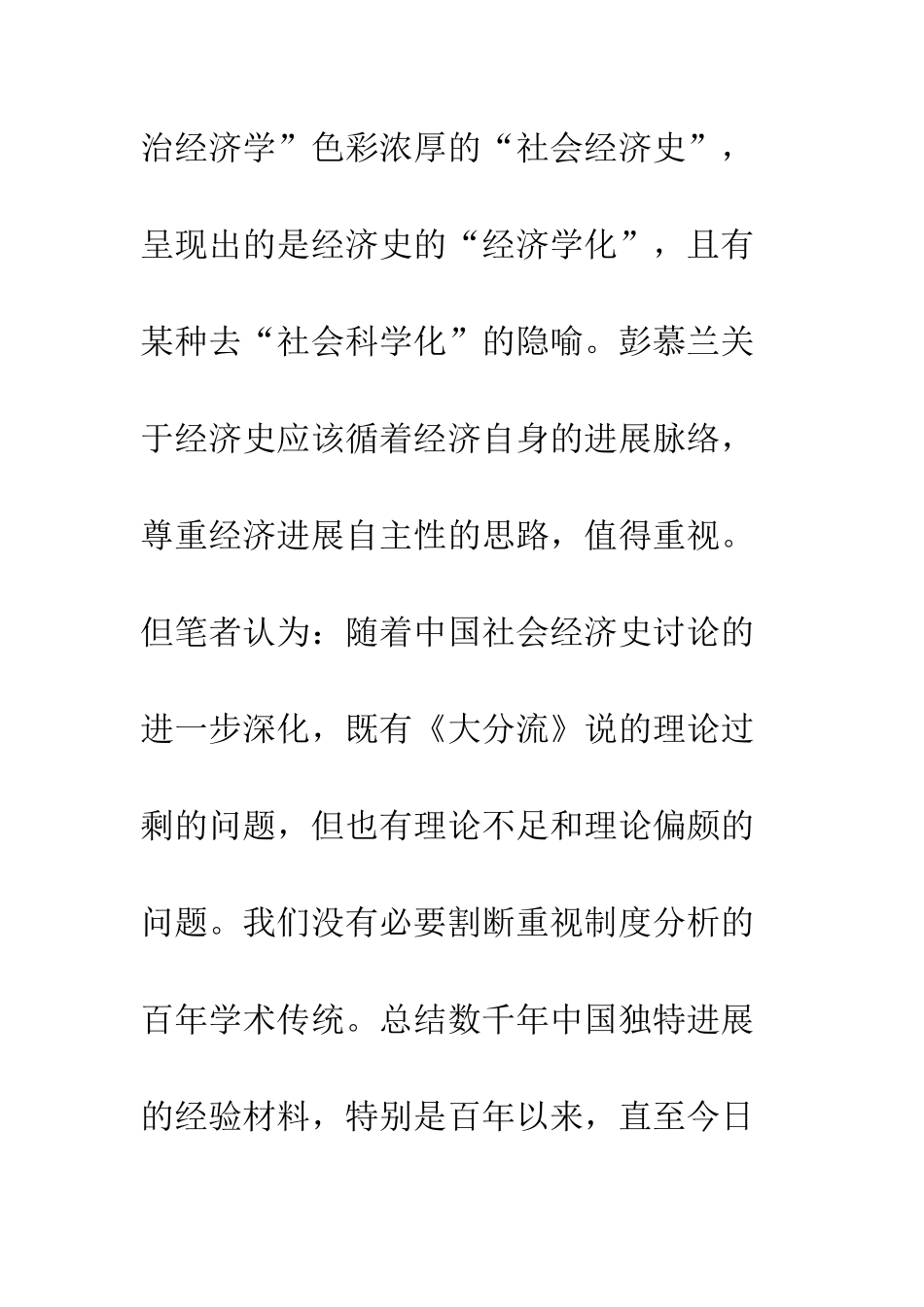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按:作者对《大分流》的回应,拟分实证与理论两部分陆续展开。本文仅就讨论理念与思路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应《史林》之约刊载于此,目的是向诸位同仁征求意见。 [摘要]《大分流》的讨论风格,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进展脉络,尊重经济进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的进一步深化,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总结数千年中国独特进展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化的经济改革实践,提升经济史理论水平的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关键词]《大分流》;经济史;问题意识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史学,有越来越走向细密化的趋势。它作为学术深化与学科成熟的体现,是合理的,应该为之兴奋。但我以为其中也不无隐忧。比较明显的一点,便是在对“史学宏大叙事”疏离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对理论淡漠的心理,并有可能导致对整体历史理解热情的消退。我对前此魏德曼发出的警戒颇有同感,史学“意义”的淡出,很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史学社会责任感的冷却,以及史学的淡出“社会”。正是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工作者应该感谢彭慕兰的《大分流》,包括前此翻译出版的弗兰克《白银资本》。因为两书都强烈刺激着中国史学工作者,重燃起了关注理论争论与整体历史评价的热情。平允而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领域,宏观与微观的失衡表现得相对不算典型。但,它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挑战:当“宏大叙事”已经扩展到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比较讨论之时,我们在衡定和检讨中国社会经济进展的历史经验时,需要继续做出哪些改善和努力,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讨论品位?假若《大分流》对我们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决不止只是对 17-18 世纪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经济的历史比较给出新的视角,或对明清江南经济给予了高得有些意外的好评。正如一些国内学者多次向读者申论的那样,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有一种理念的革新,即是对既有讨论“理论范式”――欧洲中心主义的“颠覆”。这种外来的震撼,对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意味着什么?假如回溯一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生、进展的历程,就比较容易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