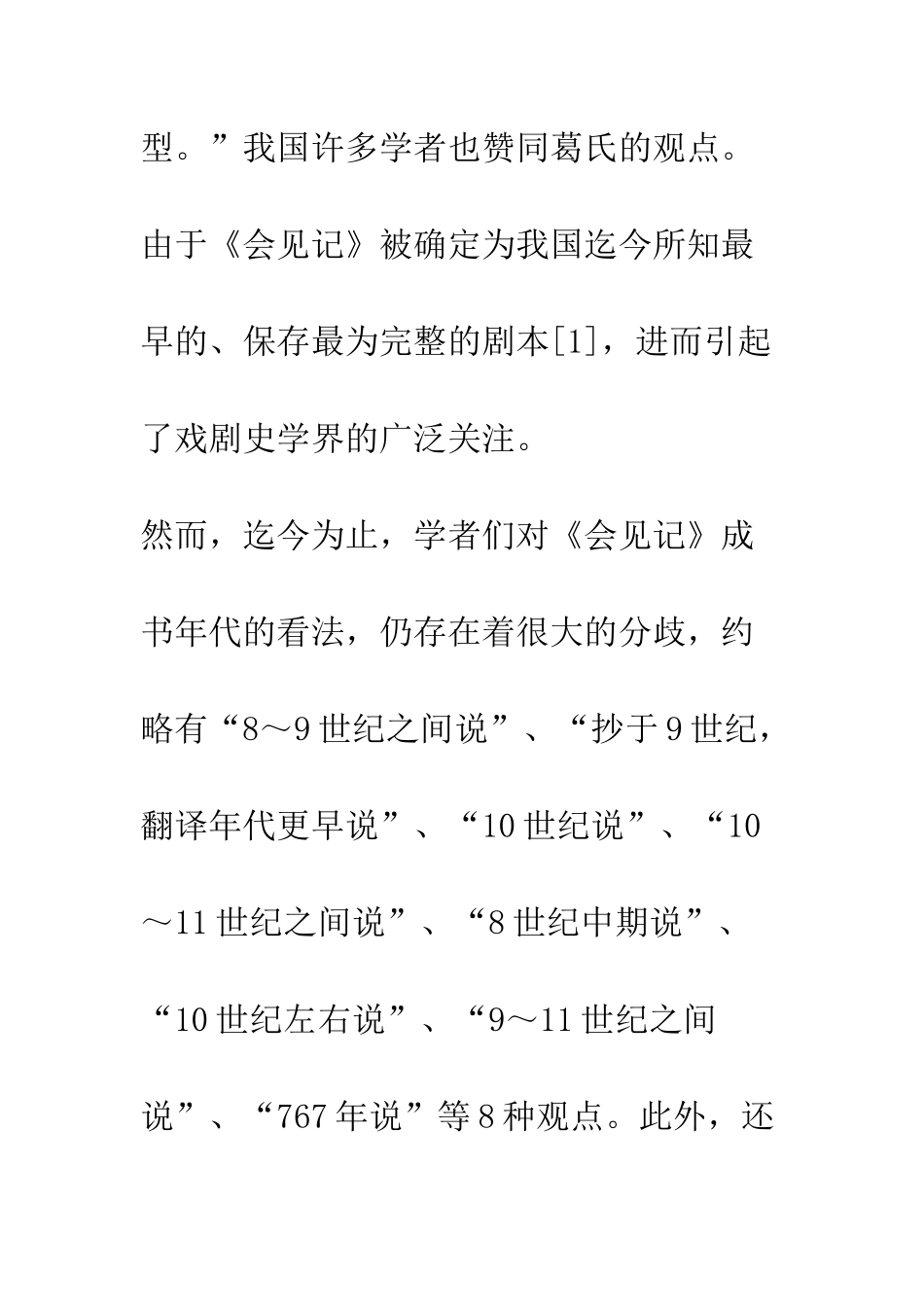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 27幕的古代大型佛教剧本。迄今共发现约 7个抄本:其中 6 个抄本是以 A·V·勒柯克为首的德国考古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吐鲁番木头沟和胜金口等地发现的残叶,分藏于梅因茨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通常称之为“吐鲁番本”;第 7 个抄本是 1959 年 4月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脱米尔提大队的农民于一古建筑遗址发现的,较为完整,总有 293 叶,是国内收藏的篇幅最大的回鹘文写本,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通常称之为“哈密本”。此外,还发现有两个焉耆语写本:一为德国考古队于焉耆舒尔楚克获得,现存德国;另一个于 1965年出土于焉耆锡克锡千佛洞,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59 年和 1961 年,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教授分别影印、刊布了分藏两处的“吐鲁番本”。她在讨论了这些残叶后称:“《弥勒会见记》可以说是回鹘戏剧艺术的雏型。”我国许多学者也赞同葛氏的观点。由于《会见记》被确定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1],进而引起了戏剧史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会见记》成书年代的看法,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约略有“8~9 世纪之间说”、“抄于 9 世纪,翻译年代更早说”、“10 世纪说”、“10~11 世纪之间说”、“8 世纪中期说”、“10 世纪左右说”、“9~11 世纪之间说”、“767 年说”等 8 种观点。此外,还有学者称:“似可将其看成或肯定为公元初的戏剧艺术史上的重要代表作。”由于诸说多是根据语言和书法特点所做的推测,都没能列出可信的断代依据,而未能获得学术界的共识。可以说,《会见记》的译写年代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笔者认为,必须将探讨《会见记》的译写年代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而要明确其社会背景,则首先应正确认识高昌居民的构成特点、高昌地区的文化特点以及突厥语族群信仰佛教和使用文字的起始时间等基本问题。一、高昌居民的构成及其文化特点从汉到唐,高昌地区一直是突厥语族群、印欧语族群和汉语族群聚居的地区。乌古斯居民为当地的土着。《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姑师”、“车师”均为 O uzʁ的不同音译,车师前国为乌古斯部族之一部,亦即《突厥语大词典》中的AlqaBølyk 部落。北魏太平真君六年,车师前部王车伊洛率军随魏师西征焉耆,留其子歇驻守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