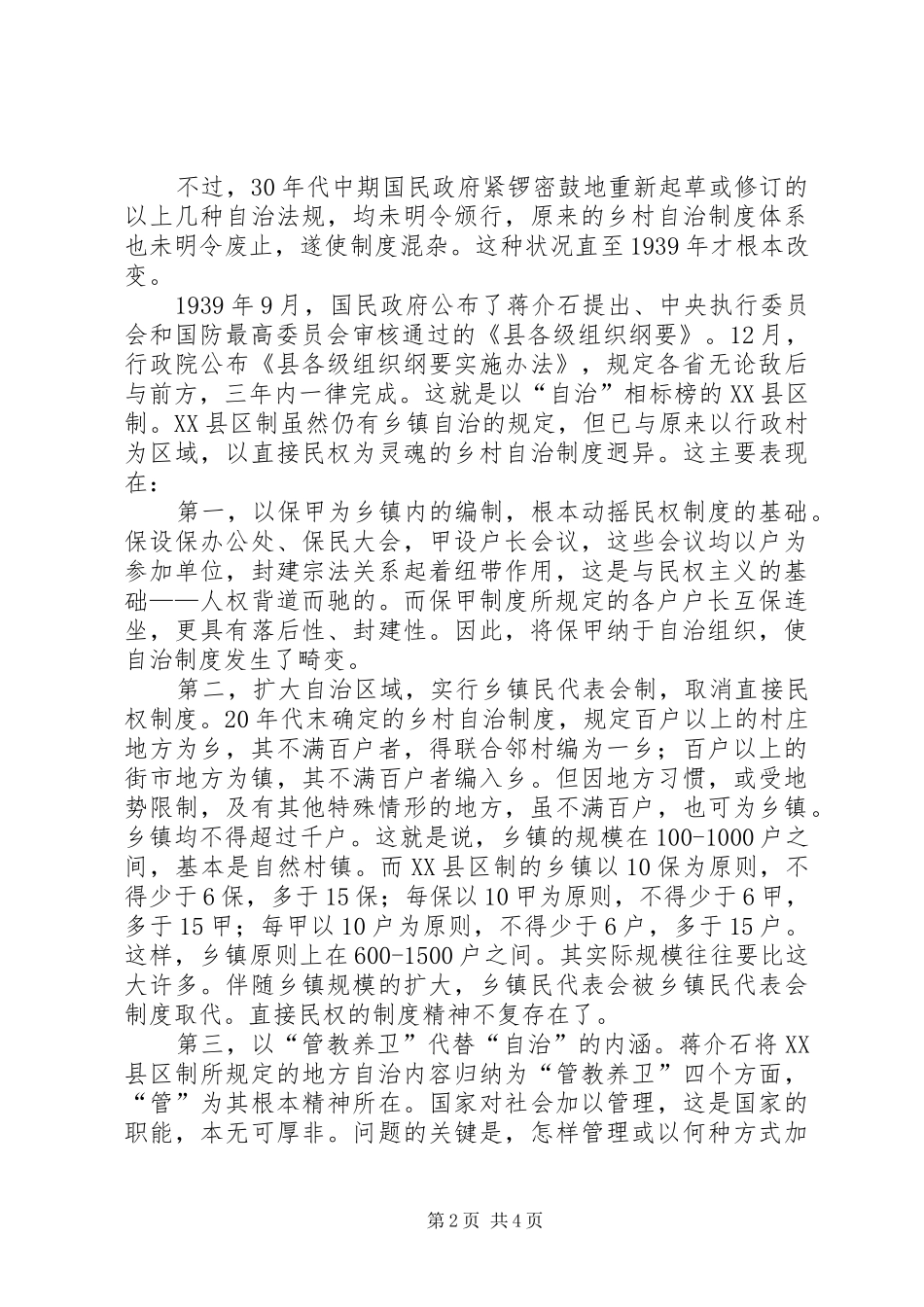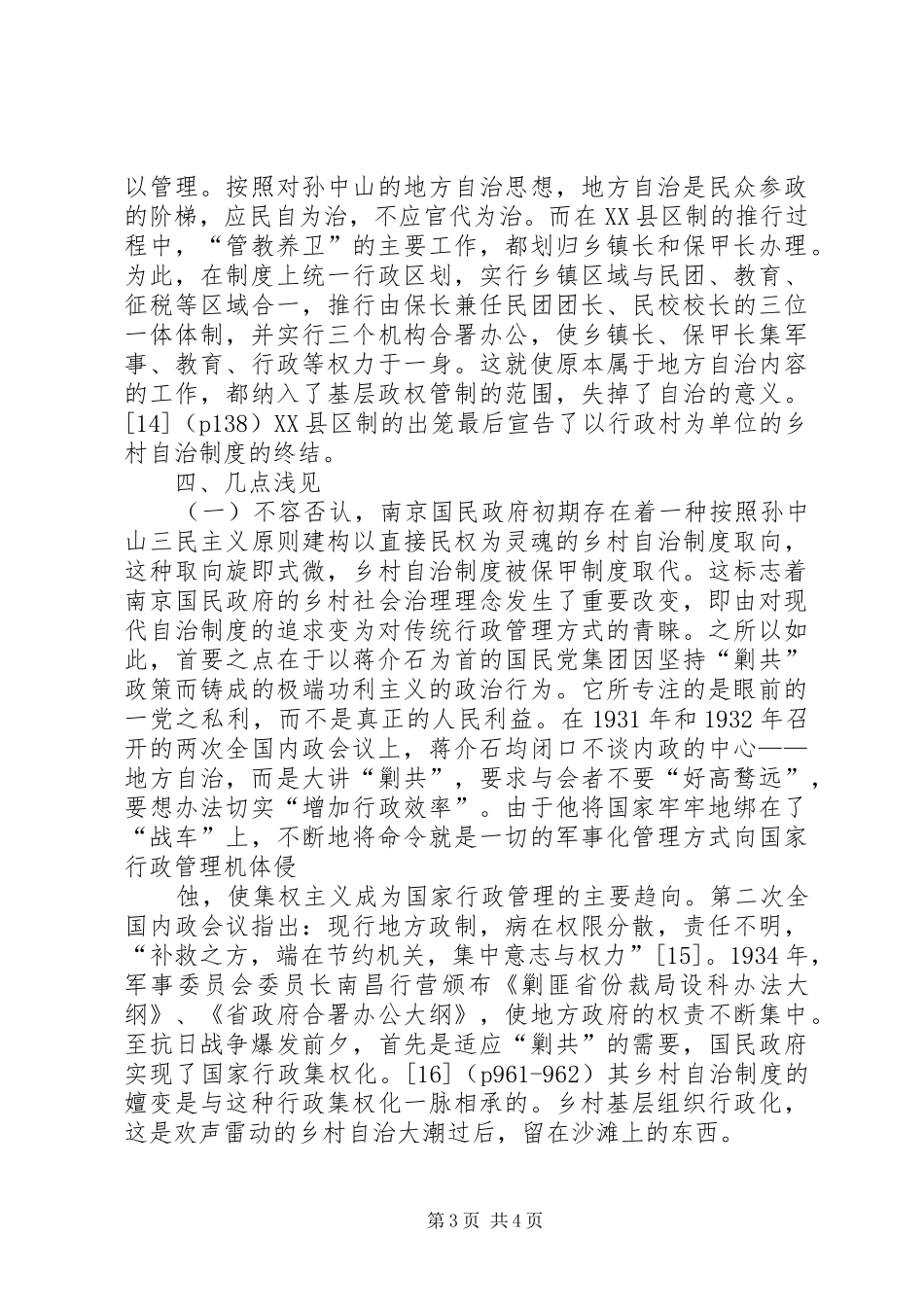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制度述论织法规,区或乡镇以下施行保甲制度案》,推销其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四省废自治行保甲的经验。会后,陕西、福建、浙江等省纷纷改行保甲。至1934年10月,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地方保甲工作,关系地方警卫,为地方自治之基础,应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提前办理。”[11](p263)于是保甲制度迅速在全国大部分省份确立起来。保甲制度是自治制度的对立物。时人指出。保甲的功用是安定社会秩序,自治则是地方人民参政的阶梯,是整个地方政府体制上的变革;保甲是辅佐官治的制度,保甲人员虽然由户长甲长推选,但最后选委大权操在政府之手,自治则是整个宪政系统中的基层组织,一切自治人员均由人民公选。[12]内政部承认,“保甲制度之本身,与现行自治制度,不无抵触”[11](p263)。为解决保甲与自治之间的矛盾,内政部建议将保甲与自治融为一体,即以保甲代替闾邻,以乡镇代替联保。1936年5月,行政院长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通过了关于融保甲于自治中的地方自治议案。三个月后,中央政治会议据此通过了厘定法规原则,正式决定容纳保甲于自治之中,乡镇的编制为保甲。1937年7月,立法院通过《保甲条例》,作为《县自治法》的补充。这样,国民政府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保甲在自治组织中的地位,使保甲获得了所谓“新生命”:“依县自治法,县以下为乡镇一级,并未因施行保甲制度而稍有变更,于办理自治事务,训练民众使用四权,毫不发生影响。在自治未完成前,依照现在事实,甲长由本甲内各户户长公推,保长由本保内各甲甲长公推,至自治已有相当之成绩,人民已受四权使用之训练,保甲长由乡镇区长,召集所属保甲公民推举之,仍与自治法上,以公民为单位之本旨,不相违背。”“是由自治法产生之保甲条例,与在剿匪区内产生之编查保甲户口条例,性质上稍有不同”。[13]30年代初期以来与自治相对立,且已形成取而代之之势的保甲制度,经过立法解释,被融入了所谓自治制度之中。第1页共4页不过,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紧锣密鼓地重新起草或修订的以上几种自治法规,均未明令颁行,原来的乡村自治制度体系也未明令废止,遂使制度混杂。这种状况直至1939年才根本改变。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蒋介石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县各级组织纲要》。12月,行政院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规定各省无论敌后与前方,三年内一律完成。这就是以“自治”相标榜的XX县区制。XX县区制虽然仍有乡镇自治的规定,但已与原来以行政村为区域,以直接民权为灵魂的乡村自治制度迥异。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以保甲为乡镇内的编制,根本动摇民权制度的基础。保设保办公处、保民大会,甲设户长会议,这些会议均以户为参加单位,封建宗法关系起着纽带作用,这是与民权主义的基础——人权背道而驰的。而保甲制度所规定的各户户长互保连坐,更具有落后性、封建性。因此,将保甲纳于自治组织,使自治制度发生了畸变。第二,扩大自治区域,实行乡镇民代表会制,取消直接民权制度。20年代末确定的乡村自治制度,规定百户以上的村庄地方为乡,其不满百户者,得联合邻村编为一乡;百户以上的街市地方为镇,其不满百户者编入乡。但因地方习惯,或受地势限制,及有其他特殊情形的地方,虽不满百户,也可为乡镇。乡镇均不得超过千户。这就是说,乡镇的规模在100-1000户之间,基本是自然村镇。而XX县区制的乡镇以10保为原则,不得少于6保,多于15保;每保以10甲为原则,不得少于6甲,多于15甲;每甲以10户为原则,不得少于6户,多于15户。这样,乡镇原则上在600-1500户之间。其实际规模往往要比这大许多。伴随乡镇规模的扩大,乡镇民代表会被乡镇民代表会制度取代。直接民权的制度精神不复存在了。第三,以“管教养卫”代替“自治”的内涵。蒋介石将XX县区制所规定的地方自治内容归纳为“管教养卫”四个方面,“管”为其根本精神所在。国家对社会加以管理,这是国家的职能,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管理或以何种方式加第2页共4页以管理。按照对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地方自治是民众参政的阶梯,应民自为治,不应官代为治。而在XX县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