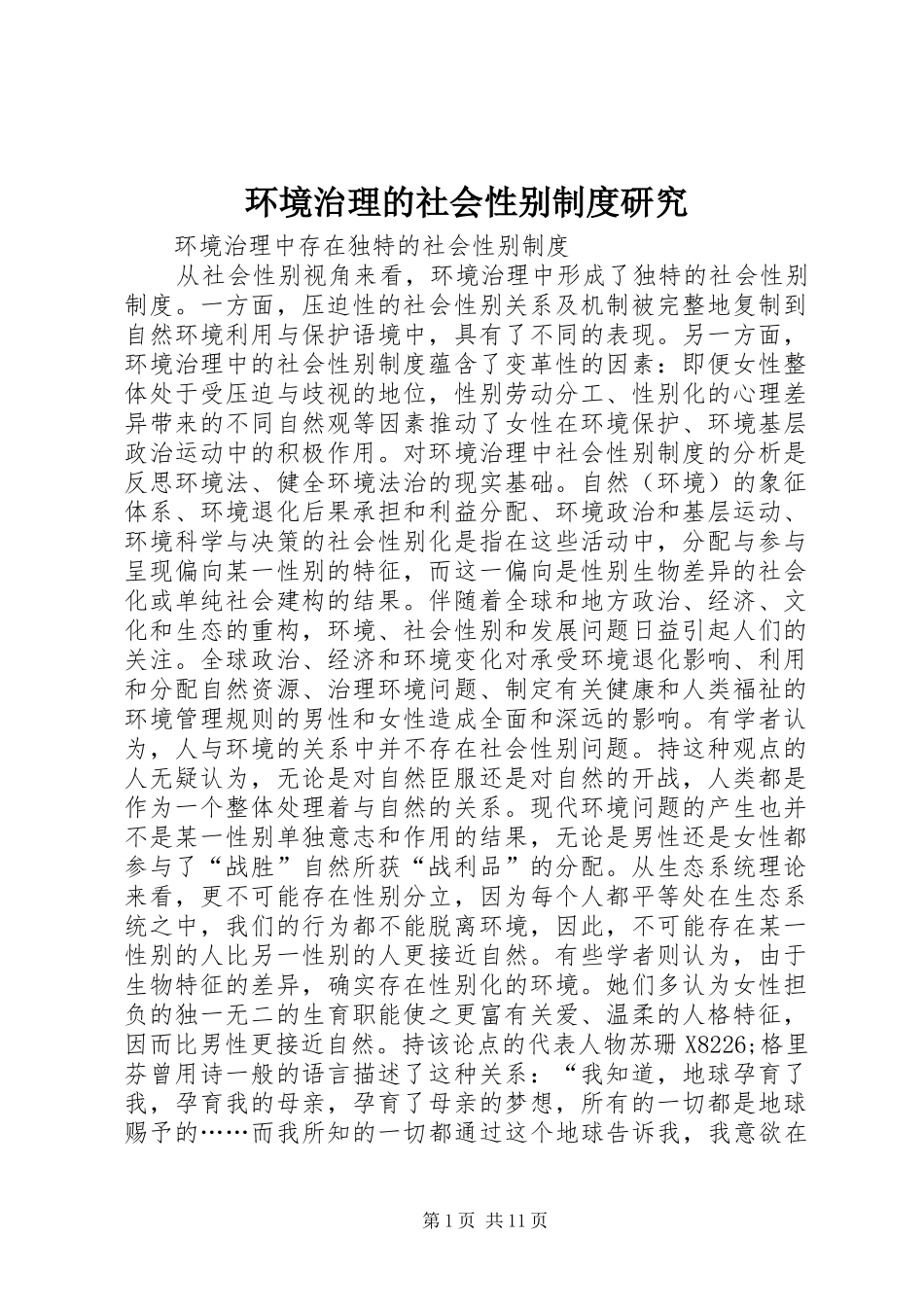环境治理的社会性别制度研究环境治理中存在独特的社会性别制度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环境治理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制度。一方面,压迫性的社会性别关系及机制被完整地复制到自然环境利用与保护语境中,具有了不同的表现。另一方面,环境治理中的社会性别制度蕴含了变革性的因素:即便女性整体处于受压迫与歧视的地位,性别劳动分工、性别化的心理差异带来的不同自然观等因素推动了女性在环境保护、环境基层政治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对环境治理中社会性别制度的分析是反思环境法、健全环境法治的现实基础。自然(环境)的象征体系、环境退化后果承担和利益分配、环境政治和基层运动、环境科学与决策的社会性别化是指在这些活动中,分配与参与呈现偏向某一性别的特征,而这一偏向是性别生物差异的社会化或单纯社会建构的结果。伴随着全球和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重构,环境、社会性别和发展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变化对承受环境退化影响、利用和分配自然资源、治理环境问题、制定有关健康和人类福祉的环境管理规则的男性和女性造成全面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并不存在社会性别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无疑认为,无论是对自然臣服还是对自然的开战,人类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处理着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生也并不是某一性别单独意志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参与了“战胜”自然所获“战利品”的分配。从生态系统理论来看,更不可能存在性别分立,因为每个人都平等处在生态系统之中,我们的行为都不能脱离环境,因此,不可能存在某一性别的人比另一性别的人更接近自然。有些学者则认为,由于生物特征的差异,确实存在性别化的环境。她们多认为女性担负的独一无二的生育职能使之更富有关爱、温柔的人格特征,因而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持该论点的代表人物苏珊X8226;格里芬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这种关系:“我知道,地球孕育了我,孕育我的母亲,孕育了母亲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是地球赐予的……而我所知的一切都通过这个地球告诉我,我意欲在第1页共11页此与你们分享:你就是地球,我们知道,希望在我们自己手中。”[4]227实践中,社会性别范畴中的女性被独立出来,与环境议题结合,引发大量的争论。197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印度物理学家范当娜X8226;席瓦(vandanashiva)率先提出“女性与环境”之说,引起一片哗然。她报告了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女性开展的契普可运动(chipkomovement)①。当地的女性为了反对商业化次生林的种植,保护赖以生存的原始林,拥抱大树,以身躯抵挡伐木者。当地政府和产业界为获取商业利益,不顾原始林地为当地居民提供燃料、木料、食物和小商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事实,联合砍伐,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为主导的环境保护运动。自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类似的“女性环境保护”运动不胜枚举,她们为女性的土地权益而斗争,反对农村和城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耗竭和有害的大型技术项目。这些女性环境保护运动常与种族/民族区域重叠。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更多地面对环境退化的不利后果,她们将这些问题看做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女性和环境的结盟被称做“为未来而结盟”[5]178。为什么会出现某一个性别与环境的“结盟”。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发现,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我们采取了一种统一战线策略,将环境问题作为共同的敌人,这使得在统一战线中的人暂时放弃了差异,而分享环境问题冲击的危机感和改进环境状况的喜悦感。由此,人类是被当做一块没有凸凹、没有色差的平板置入环境管理体系。但是,这种人为创造的一体感并不能彻底抹除统一战线内部的差异和对抗,即便在一体的规范下,并不是人人平等的享有环境权利,也并不是人人承担同样的环境恶果。实际上,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是高度社会性别化的,社会性别及其权力关系和制度影响和塑造了人们的自然观、现实权利义务分配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方式。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中确实存在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而非臆想的,是显著而非隐秘的,是全面而非偶发的。这种社会性别的差异并非根植于人的生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