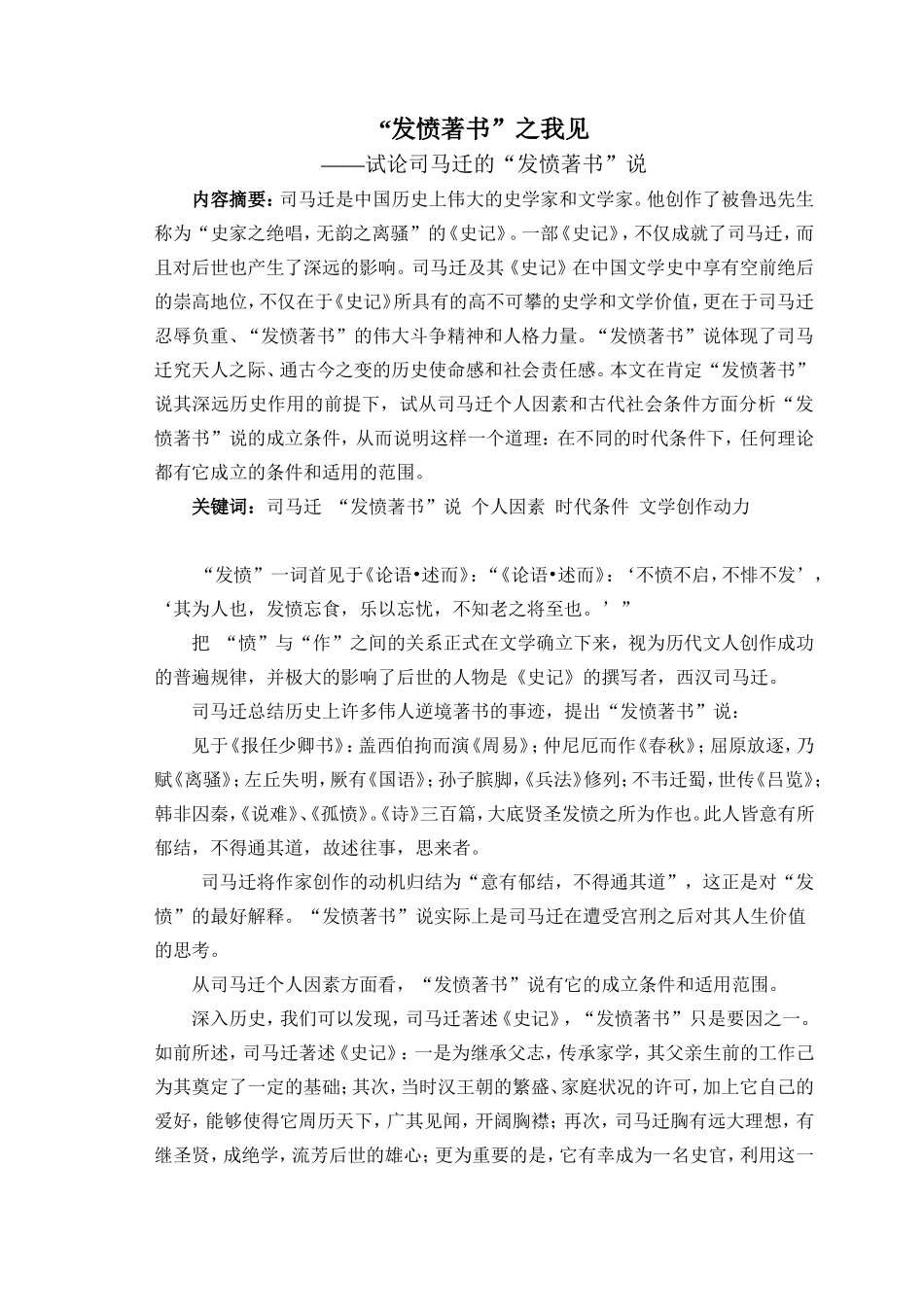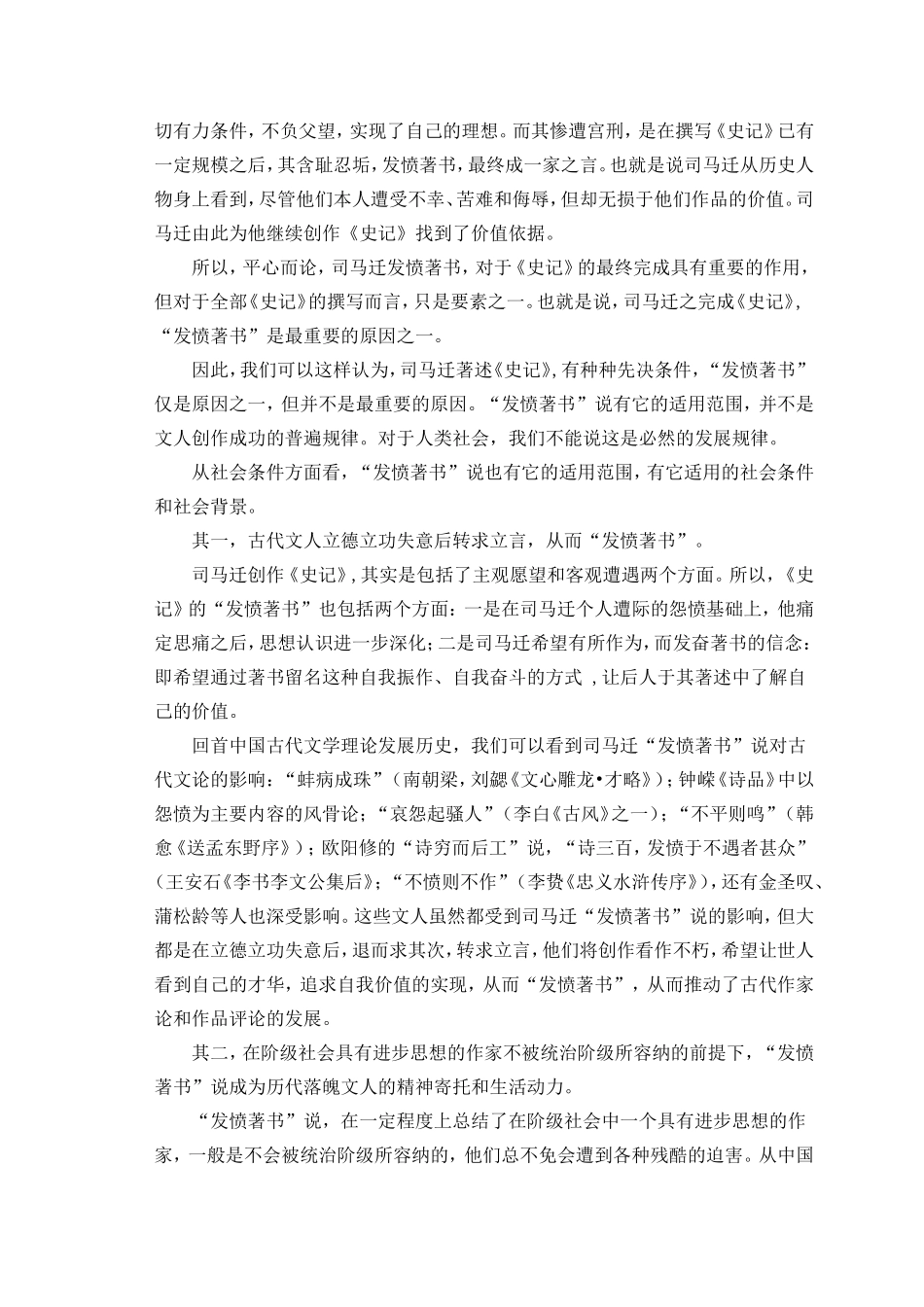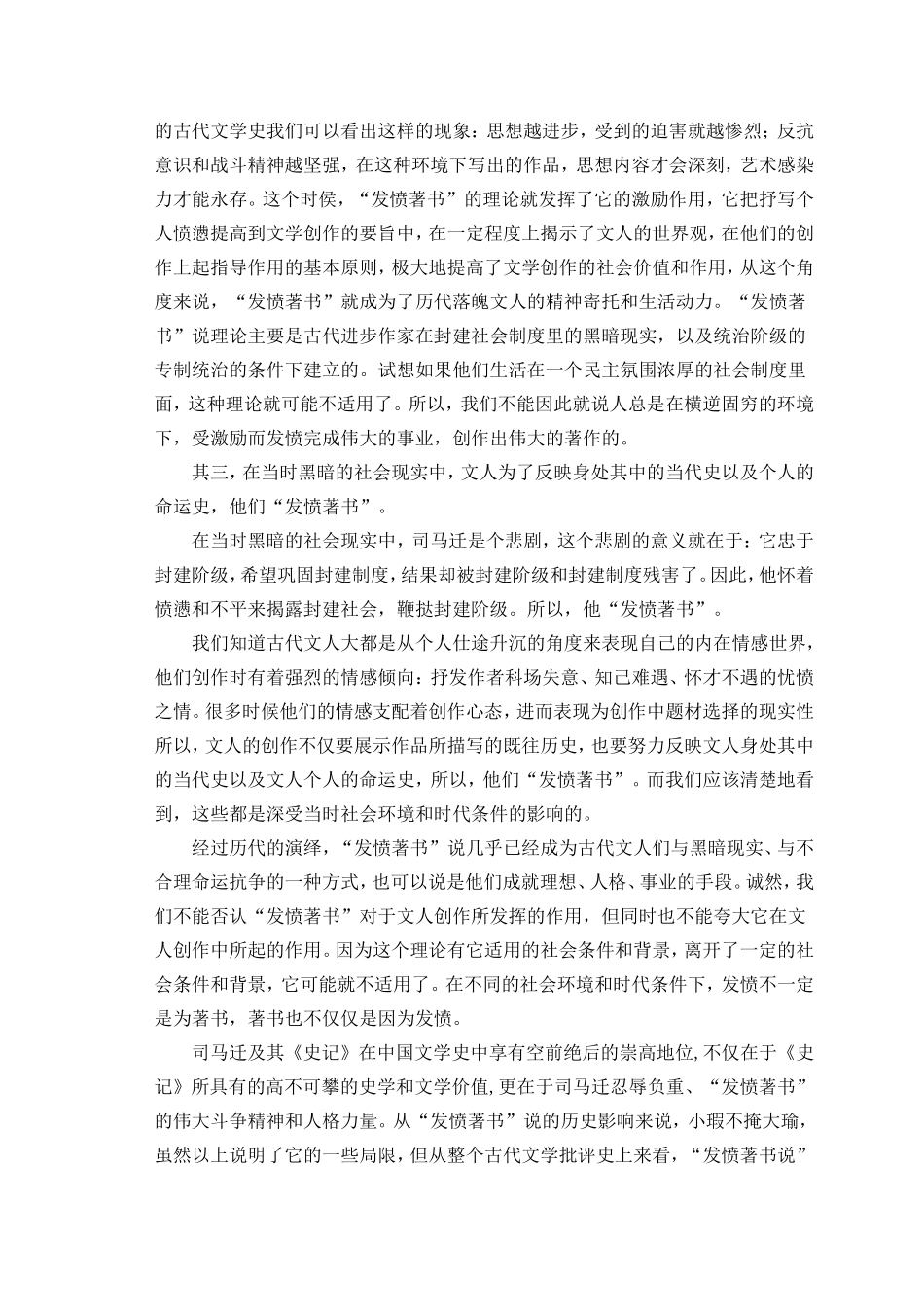“发愤著书”之我见——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内容摘要: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了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部《史记》,不仅成就了司马迁,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于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发愤著书”说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本文在肯定“发愤著书”说其深远历史作用的前提下,试从司马迁个人因素和古代社会条件方面分析“发愤著书”说的成立条件,从而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任何理论都有它成立的条件和适用的范围。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个人因素时代条件文学创作动力“发愤”一词首见于《论语•述而》:“《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把“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文学确立下来,视为历代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并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人物是《史记》的撰写者,西汉司马迁。司马迁总结历史上许多伟人逆境著书的事迹,提出“发愤著书”说:见于《报任少卿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这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发愤著书”说实际上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对其人生价值的思考。从司马迁个人因素方面看,“发愤著书”说有它的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深入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著述《史记》,“发愤著书”只是要因之一。如前所述,司马迁著述《史记》:一是为继承父志,传承家学,其父亲生前的工作己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当时汉王朝的繁盛、家庭状况的许可,加上它自己的爱好,能够使得它周历天下,广其见闻,开阔胸襟;再次,司马迁胸有远大理想,有继圣贤,成绝学,流芳后世的雄心;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幸成为一名史官,利用这一切有力条件,不负父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其惨遭宫刑,是在撰写《史记》已有一定规模之后,其含耻忍垢,发愤著书,最终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从历史人物身上看到,尽管他们本人遭受不幸、苦难和侮辱,但却无损于他们作品的价值。司马迁由此为他继续创作《史记》找到了价值依据。所以,平心而论,司马迁发愤著书,对于《史记》的最终完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全部《史记》的撰写而言,只是要素之一。也就是说,司马迁之完成《史记》,“发愤著书”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司马迁著述《史记》,有种种先决条件,“发愤著书”仅是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发愤著书”说有它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对于人类社会,我们不能说这是必然的发展规律。从社会条件方面看,“发愤著书”说也有它的适用范围,有它适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其一,古代文人立德立功失意后转求立言,从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创作《史记》,其实是包括了主观愿望和客观遭遇两个方面。所以,《史记》的“发愤著书”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司马迁个人遭际的怨愤基础上,他痛定思痛之后,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二是司马迁希望有所作为,而发奋著书的信念:即希望通过著书留名这种自我振作、自我奋斗的方式,让后人于其著述中了解自己的价值。回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对古代文论的影响:“蚌病成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钟嵘《诗品》中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之一);“不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王安石《李书李文公集后》;“不愤则不作”(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