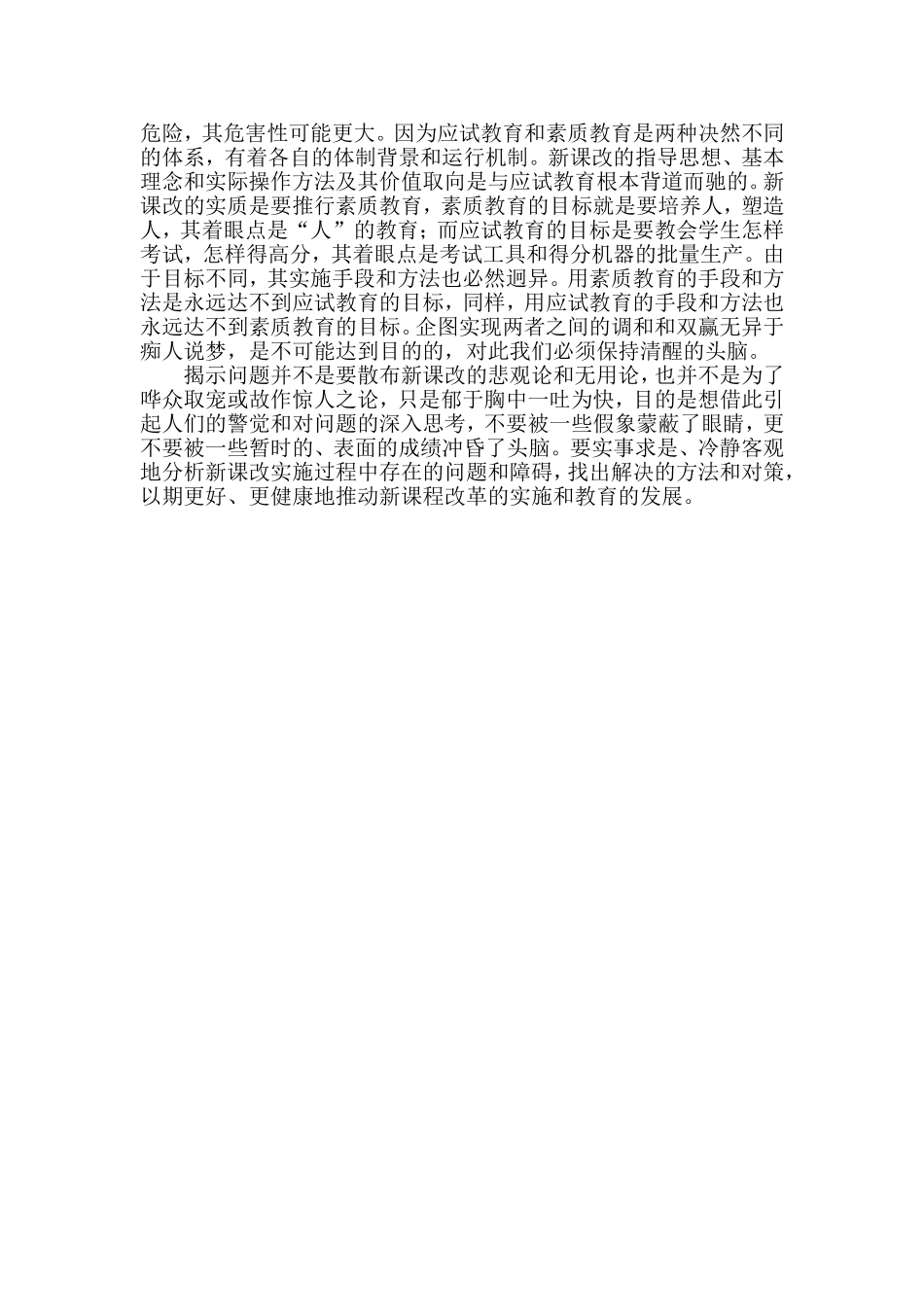(作者:叶维取2006年11月13日以《新课改:挂羊头,卖狗肉?》为题发表在《合肥晚报·教育视线》头版头条,后收入《合肥晚报·教育视线》五周年优秀作品选《谁左右了我们的视线》一书)新课改的现状到底怎么样?安徽省合肥市庐东学校叶维取素有“总理工程”之称的新课程改革,自2001年9月开始实验以来,至今已整整五年了。其成效和现状到底如何,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最近看了一篇发表在某报上的有关文章,似乎让人感觉到,现在新课改的推进在广大基层学校和老师中已是如火如荼,欣欣向荣,到处是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然而不幸的是,在赞歌唱得最响、最动听的地方,也许就是问题最突出、最严重的地方。看不到这一点,一味唱赞歌,不是对现实和基层现状不了解,就是睁着眼睛说假话。地球人都知道,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应试教育历史上最好、最火爆的时期,应试教育在神州大地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和炉火纯青的境界!哪所中小学校不是在加班加点给学生延长时间补课,星期日变成了“星期七”;哪个老师不是每天给学生布置一套又一套的训练题和考试卷,成了讨债的“黄世仁”;哪个学生不是成天背着沉重的书包、戴着厚厚的眼镜成为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最苦最累的人,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学习,比“包身工”好不了多少。在此情况下,学生除了上课、做题、考试之外,谁还有时间和精力阅读课外书、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学生有的只是对学校和老师的憎恨,对学习生活的厌恶与冷漠,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大堆身体和心理问题。应试教育就是这样通过对学生生命的漠视,以牺牲学生身心健康和透支学生的学习潜力和后劲为代价成就其辉煌的。可以说,新课改的一切精髓和成果都被应试教育彻底消解了。无庸讳言,在新课改推行之初,广大一线教师确实感到很激动、很振奋,对新课改充满了信心和期望,看到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曙光。大家都满腔热情地欢迎新课改,投身新课改,自觉学习和踊跃接受、实践新课改的理念和方法。然而在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面前,他们又感到极其困惑与无助。面对应试教育的强大威力,他们深感个体力量的渺小和回天乏力。于是在一阵新鲜和激动之后,大家又退回到从前,重新祭起了应试教育的大旗,出现了轰轰烈烈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应试教育的局面。而作为具体实践素质教育的新课改,从此就处在专家和专职教研人员的一片叫好声中和理论研究的自恋式内部循环当中,在实践层面上依然是应试教育的天下。特别是在一些学校,新课改依然只是作为教研教改的一种点缀或者是为了装潢门面而存在,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课题研究的汇报中,谁也不愿或不敢在实践中真正应用,即使应用,也是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挂新课改的羊头,卖应试教育的狗肉,教师真正操作的还是传统应试教育的一套做法——讲与灌、练与做。因为应试教育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包括学校领导在内谁也不敢拿学校和学生的前途命运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而把宝押在新课改上。如果单纯搞新课改,谁也不能保证在中、高考中保持和提高升学率。只有靠加班加点、拼体力、拼时间、强化训练、题海战术、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办法才能保证万无一失,而且谁也不敢走出这样的“囚徒困境”,事实也不可能走出这样一个困境。因为大家都怀着同样的担心和害怕:我不搞加班加点、题海战术、强化训练,我在搞素质教育和新课改,如果别人不这样怎么办?别人就要超过我,我就要在中、高考竞争中失败,就要遭到残酷地淘汰,学校的生源、声誉、生存和发展以及依附于此的教师奖金福利等物质利益的东西就要受到威胁和影响。于是别人花十小时,我就要花十一、十二小时;别人让学生做一套试卷,我就要让学生做两套、三套甚至更多套试卷,就是要在各个方面超过别人。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效法,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和困境。在这种恶性竞争中没有最后的真正赢家,大家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失败者,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全社会都被捆绑在应试教育的战车上,任其疯狂奔跑而无法停下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连设计新课程改革的著名专家如上海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