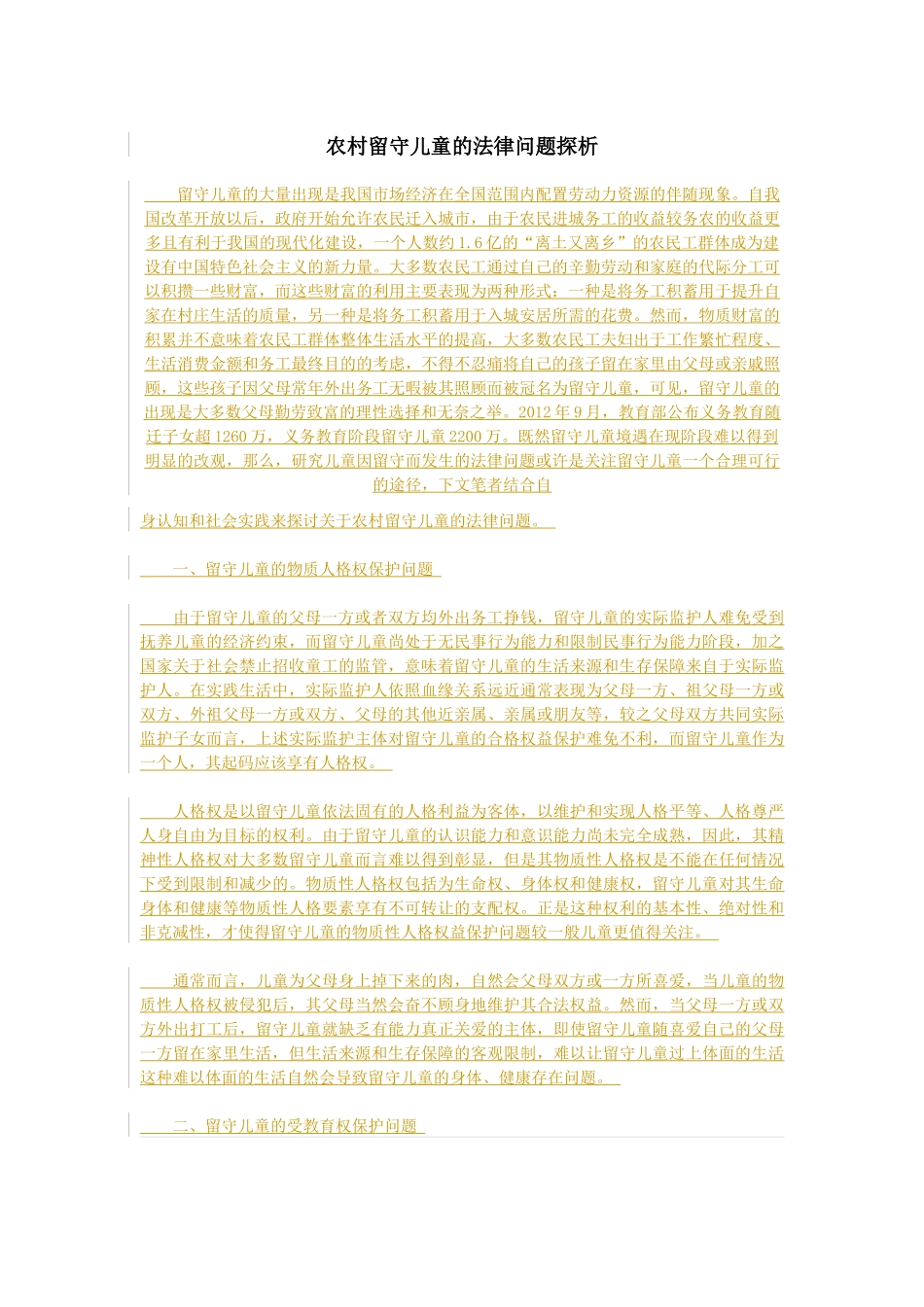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问题探析留守儿童的大量出现是我国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伴随现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迁入城市,由于农民进城务工的收益较务农的收益更多且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人数约1.6亿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力量。大多数农民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家庭的代际分工可以积攒一些财富,而这些财富的利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务工积蓄用于提升自家在村庄生活的质量,另一种是将务工积蓄用于入城安居所需的花费。然而,物质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群体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农民工夫妇出于工作繁忙程度、生活消费金额和务工最终目的的考虑,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由父母或亲戚照顾,这些孩子因父母常年外出务工无暇被其照顾而被冠名为留守儿童,可见,留守儿童的出现是大多数父母勤劳致富的理性选择和无奈之举。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义务教育随迁子女超1260万,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2200万。既然留守儿童境遇在现阶段难以得到明显的改观,那么,研究儿童因留守而发生的法律问题或许是关注留守儿童一个合理可行的途径,下文笔者结合自身认知和社会实践来探讨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问题。一、留守儿童的物质人格权保护问题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均外出务工挣钱,留守儿童的实际监护人难免受到抚养儿童的经济约束,而留守儿童尚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阶段,加之国家关于社会禁止招收童工的监管,意味着留守儿童的生活来源和生存保障来自于实际监护人。在实践生活中,实际监护人依照血缘关系远近通常表现为父母一方、祖父母一方或双方、外祖父母一方或双方、父母的其他近亲属、亲属或朋友等,较之父母双方共同实际监护子女而言,上述实际监护主体对留守儿童的合格权益保护难免不利,而留守儿童作为一个人,其起码应该享有人格权。人格权是以留守儿童依法固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以维护和实现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为目标的权利。由于留守儿童的认识能力和意识能力尚未完全成熟,因此,其精神性人格权对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难以得到彰显,但是其物质性人格权是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受到限制和减少的。物质性人格权包括为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留守儿童对其生命身体和健康等物质性人格要素享有不可转让的支配权。正是这种权利的基本性、绝对性和非克减性,才使得留守儿童的物质性人格权益保护问题较一般儿童更值得关注。通常而言,儿童为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自然会父母双方或一方所喜爱,当儿童的物质性人格权被侵犯后,其父母当然会奋不顾身地维护其合法权益。然而,当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后,留守儿童就缺乏有能力真正关爱的主体,即使留守儿童随喜爱自己的父母一方留在家里生活,但生活来源和生存保障的客观限制,难以让留守儿童过上体面的生活这种难以体面的生活自然会导致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存在问题。二、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保护问题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义务复合型权利,由于留守儿童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因此,留守儿童是受教育权的权利主体,父母、实际监护人、学校、老师等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受教育权的主体均为义务主体。较之一般儿童受教育情况而言,由于在学习上缺少能够辅导、督促和引导的天然老师一些留守儿童表现出学习惰性,加之现行应试教育的弊端,使其被动地接受学习,学习水平和知识状况令人堪忧。由于留守儿童需要依靠父母从外出务工的辛苦钱,而其学习又不能为老师和家人满意,自然免不了劝诫、责备乃至挨打,加之留守儿童在感情上缺少最亲近人的关爱和沟通,更容易产生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难以得到疏通时其逆反心理将得以加强,从而使他们养成一些德行较差的坏毛病。留守儿童的坏毛病难以得到改掉或者愈发引人注意时,出于对其他儿童教育环境的良好塑造,留守儿童常常成为学校里不受欢迎、待见和接纳的对象。如果其父母在外打工的运气较好能够获得较一般知识人高的报酬,其父母对子女就更不抱有靠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幻想,在留守儿童混到能够在外打工的年龄后,其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