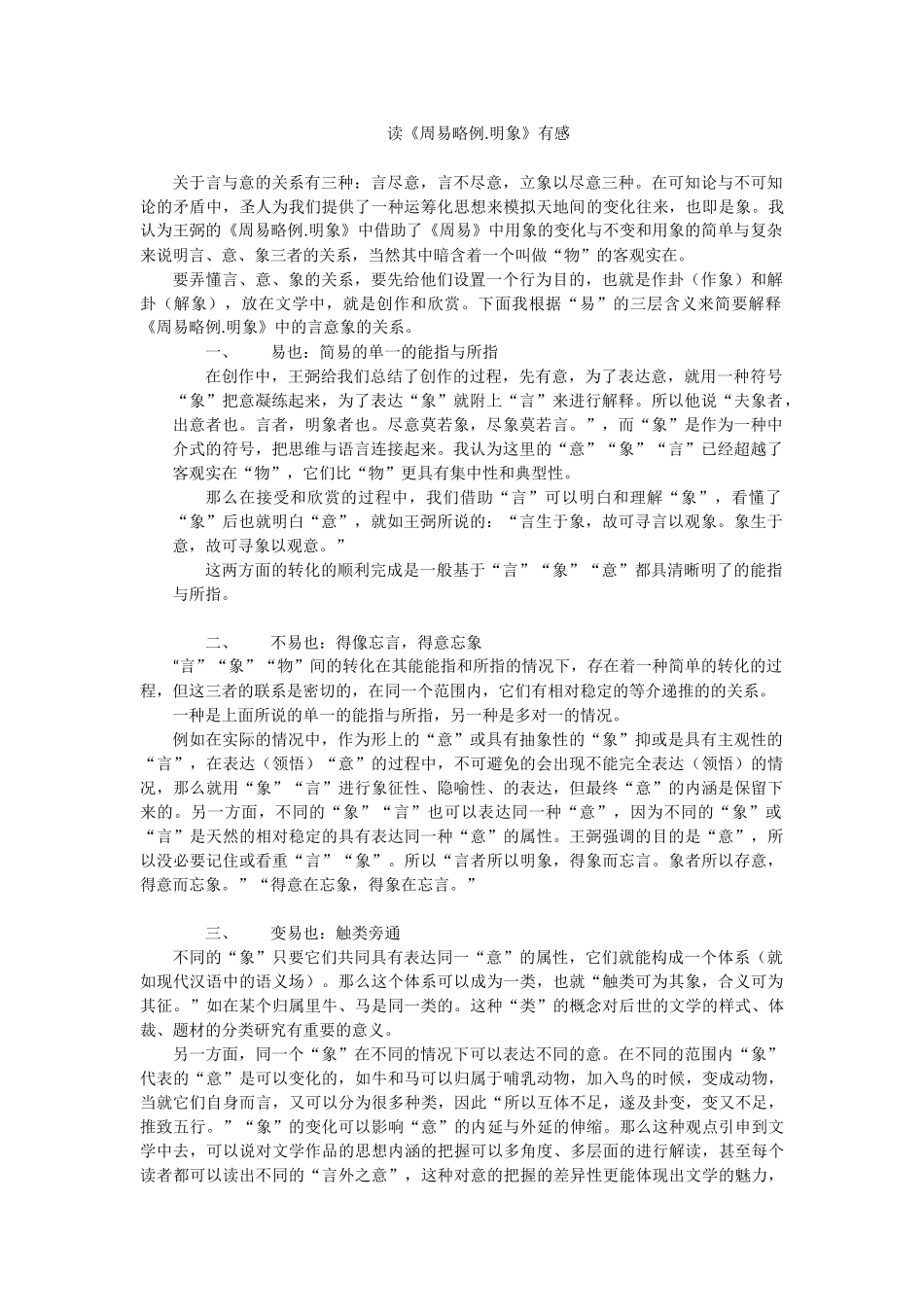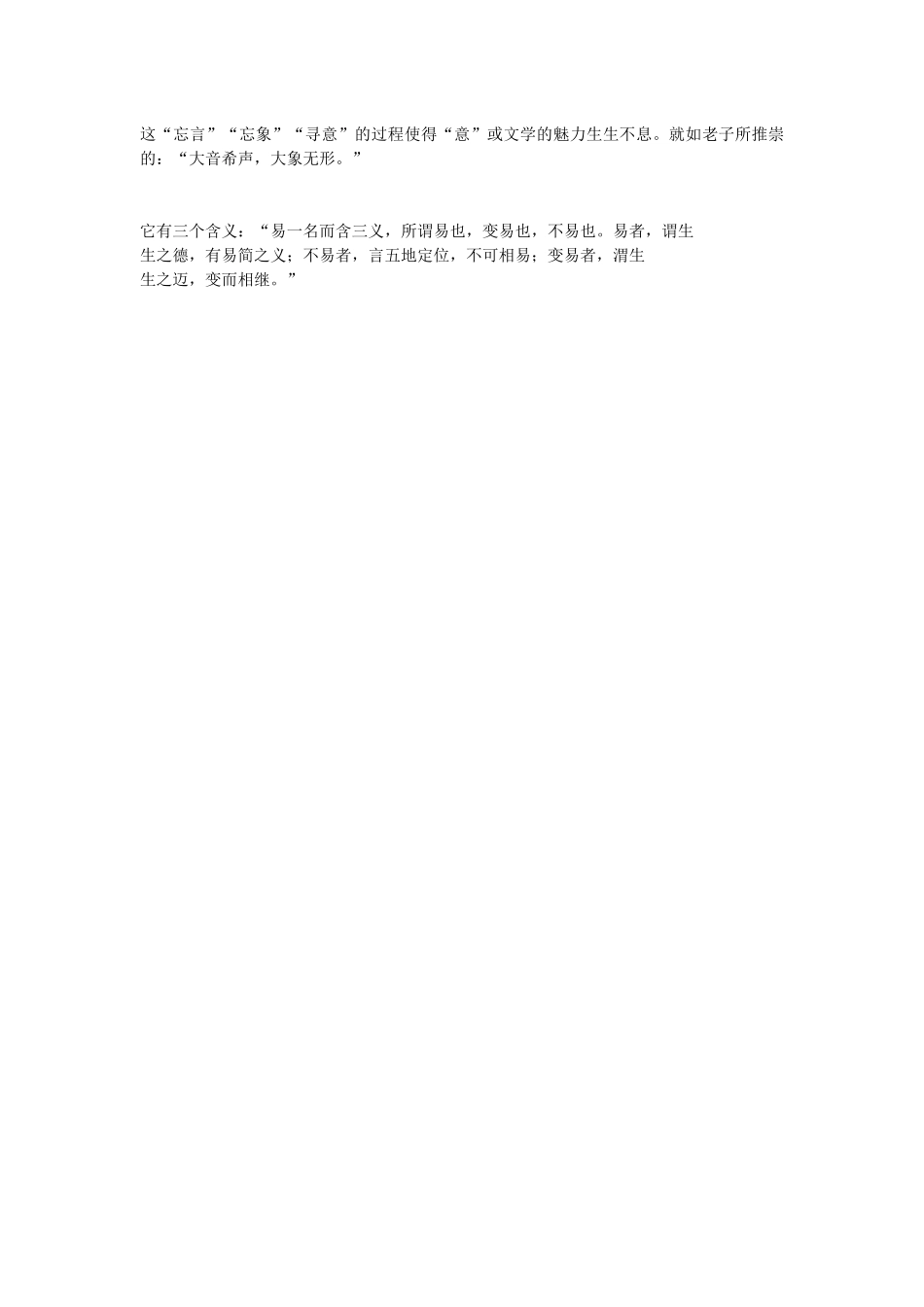读《周易略例.明象》有感关于言与意的关系有三种:言尽意,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三种。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矛盾中,圣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运筹化思想来模拟天地间的变化往来,也即是象。我认为王弼的《周易略例.明象》中借助了《周易》中用象的变化与不变和用象的简单与复杂来说明言、意、象三者的关系,当然其中暗含着一个叫做“物”的客观实在。要弄懂言、意、象的关系,要先给他们设置一个行为目的,也就是作卦(作象)和解卦(解象),放在文学中,就是创作和欣赏。下面我根据“易”的三层含义来简要解释《周易略例.明象》中的言意象的关系。一、易也:简易的单一的能指与所指在创作中,王弼给我们总结了创作的过程,先有意,为了表达意,就用一种符号“象”把意凝练起来,为了表达“象”就附上“言”来进行解释。所以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而“象”是作为一种中介式的符号,把思维与语言连接起来。我认为这里的“意”“象”“言”已经超越了客观实在“物”,它们比“物”更具有集中性和典型性。那么在接受和欣赏的过程中,我们借助“言”可以明白和理解“象”,看懂了“象”后也就明白“意”,就如王弼所说的:“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这两方面的转化的顺利完成是一般基于“言”“象”“意”都具清晰明了的能指与所指。二、不易也:得像忘言,得意忘象“言”“象”“物”间的转化在其能能指和所指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种简单的转化的过程,但这三者的联系是密切的,在同一个范围内,它们有相对稳定的等介递推的的关系。一种是上面所说的单一的能指与所指,另一种是多对一的情况。例如在实际的情况中,作为形上的“意”或具有抽象性的“象”抑或是具有主观性的“言”,在表达(领悟)“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不能完全表达(领悟)的情况,那么就用“象”“言”进行象征性、隐喻性、的表达,但最终“意”的内涵是保留下来的。另一方面,不同的“象”“言”也可以表达同一种“意”,因为不同的“象”或“言”是天然的相对稳定的具有表达同一种“意”的属性。王弼强调的目的是“意”,所以没必要记住或看重“言”“象”。所以“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三、变易也:触类旁通不同的“象”只要它们共同具有表达同一“意”的属性,它们就能构成一个体系(就如现代汉语中的语义场)。那么这个体系可以成为一类,也就“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如在某个归属里牛、马是同一类的。这种“类”的概念对后世的文学的样式、体裁、题材的分类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同一个“象”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表达不同的意。在不同的范围内“象”代表的“意”是可以变化的,如牛和马可以归属于哺乳动物,加入鸟的时候,变成动物,当就它们自身而言,又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因此“所以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象”的变化可以影响“意”的内延与外延的伸缩。那么这种观点引申到文学中去,可以说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的把握可以多角度、多层面的进行解读,甚至每个读者都可以读出不同的“言外之意”,这种对意的把握的差异性更能体现出文学的魅力,这“忘言”“忘象”“寻意”的过程使得“意”或文学的魅力生生不息。就如老子所推崇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有三个含义:“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谓生生之德,有易简之义;不易者,言五地定位,不可相易;变易者,渭生生之迈,变而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