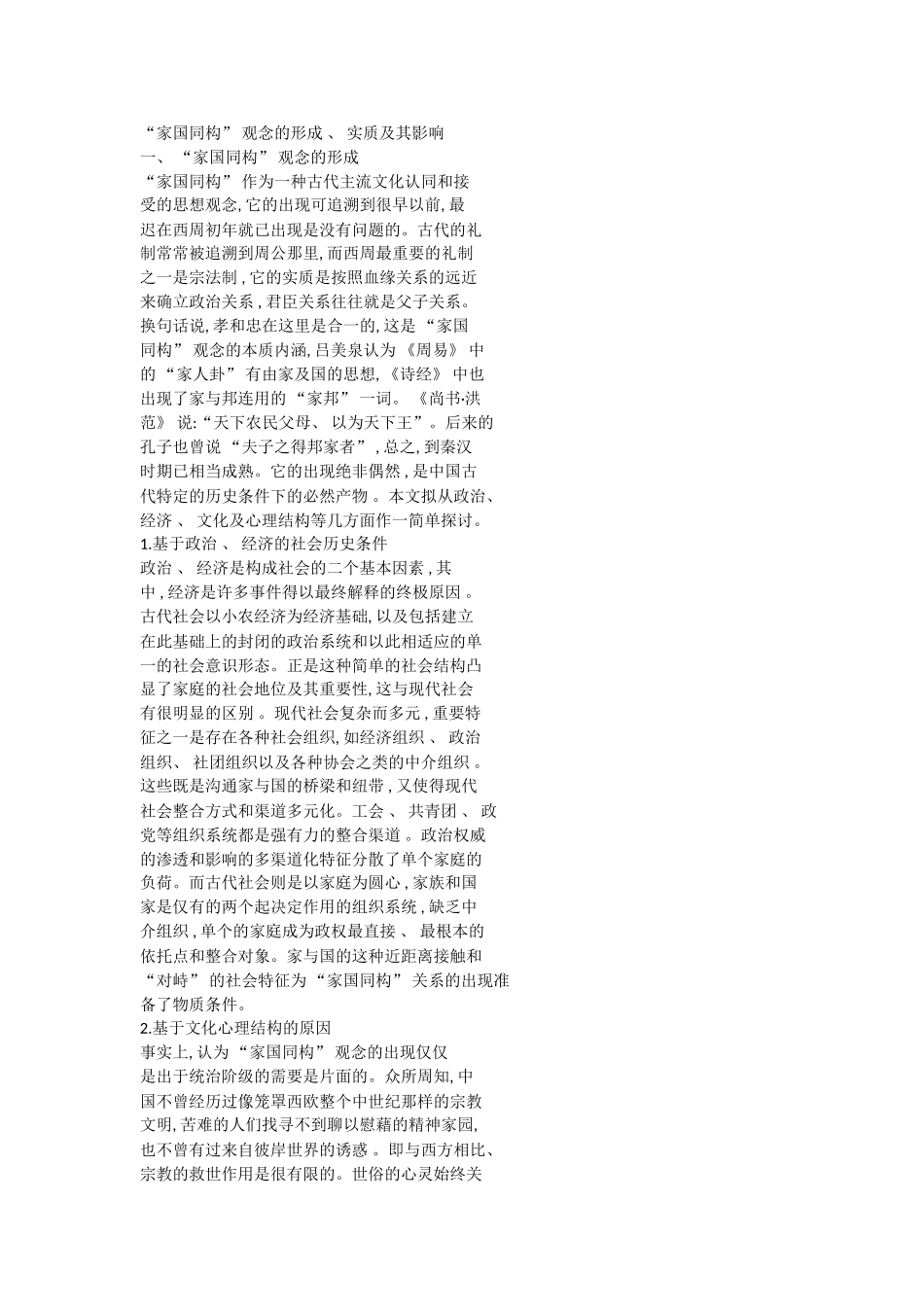“家国同构”观念的形成、实质及其影响一、“家国同构”观念的形成“家国同构”作为一种古代主流文化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它的出现可追溯到很早以前,最迟在西周初年就已出现是没有问题的。古代的礼制常常被追溯到周公那里,而西周最重要的礼制之一是宗法制,它的实质是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立政治关系,君臣关系往往就是父子关系。换句话说,孝和忠在这里是合一的,这是“家国同构”观念的本质内涵,吕美泉认为《周易》中的“家人卦”有由家及国的思想,《诗经》中也出现了家与邦连用的“家邦”一词。《尚书·洪范》说:“天下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后来的孔子也曾说“夫子之得邦家者”,总之,到秦汉时期已相当成熟。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是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本文拟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心理结构等几方面作一简单探讨。1.基于政治、经济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是构成社会的二个基本因素,其中,经济是许多事件得以最终解释的终极原因。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及包括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闭的政治系统和以此相适应的单一的社会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简单的社会结构凸显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及其重要性,这与现代社会有很明显的区别。现代社会复杂而多元,重要特征之一是存在各种社会组织,如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团组织以及各种协会之类的中介组织。这些既是沟通家与国的桥梁和纽带,又使得现代社会整合方式和渠道多元化。工会、共青团、政党等组织系统都是强有力的整合渠道。政治权威的渗透和影响的多渠道化特征分散了单个家庭的负荷。而古代社会则是以家庭为圆心,家族和国家是仅有的两个起决定作用的组织系统,缺乏中介组织,单个的家庭成为政权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托点和整合对象。家与国的这种近距离接触和“对峙”的社会特征为“家国同构”关系的出现准备了物质条件。2.基于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因事实上,认为“家国同构”观念的出现仅仅是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片面的。众所周知,中国不曾经历过像笼罩西欧整个中世纪那样的宗教文明,苦难的人们找寻不到聊以慰藉的精神家园,也不曾有过来自彼岸世界的诱惑。即与西方相比、宗教的救世作用是很有限的。世俗的心灵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于是,他们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而将完善的政治和理想的社会寄托于“圣人”,所谓“圣人出,黄河清”。孔子和孟子等思想家则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心悦之,犹解倒悬也。”“今夫天下之牧,未有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以上思想直接反映了民众对明君的渴望情绪。同时,无处不在的君主权威和“无终食之间违仁”的道德说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民众的思想,这大体上从心理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家国同构”的事实能被接受和默认的原因。当然,直接催生这一观念的主要因素是儒家伦理学说。儒家历来主张以己推人,由近及远,将处理血缘关系的原则推广到社会关系之中。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按这种由近及远的思想逻辑,儒家认为:家是缩小的国,国则是放大的家。《荀子·致士》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礼记·大学》说:“古之人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于其国,先齐其家”。《孝经·士章》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国。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总之,父与君,家与国的连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非常普遍,直到汉代经学家提出“家国同构”后,这一观念就相当成熟了。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正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结构几种主要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最终导致了“家国同构”观念的出现。二、“家国同构”的深层内涵观念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更深层的内涵。揭示“家国同构”观念的深层内涵,才能对它作更清楚明白的说明。1.血缘:“家国同构”的基本依托点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观点出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出现的剩余产品逐渐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经济地位的不同导致了阶级对立的出现,标志国家特征的“公共权力”逐渐独立和上移到某个或某几个统治集团,而这几个集团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