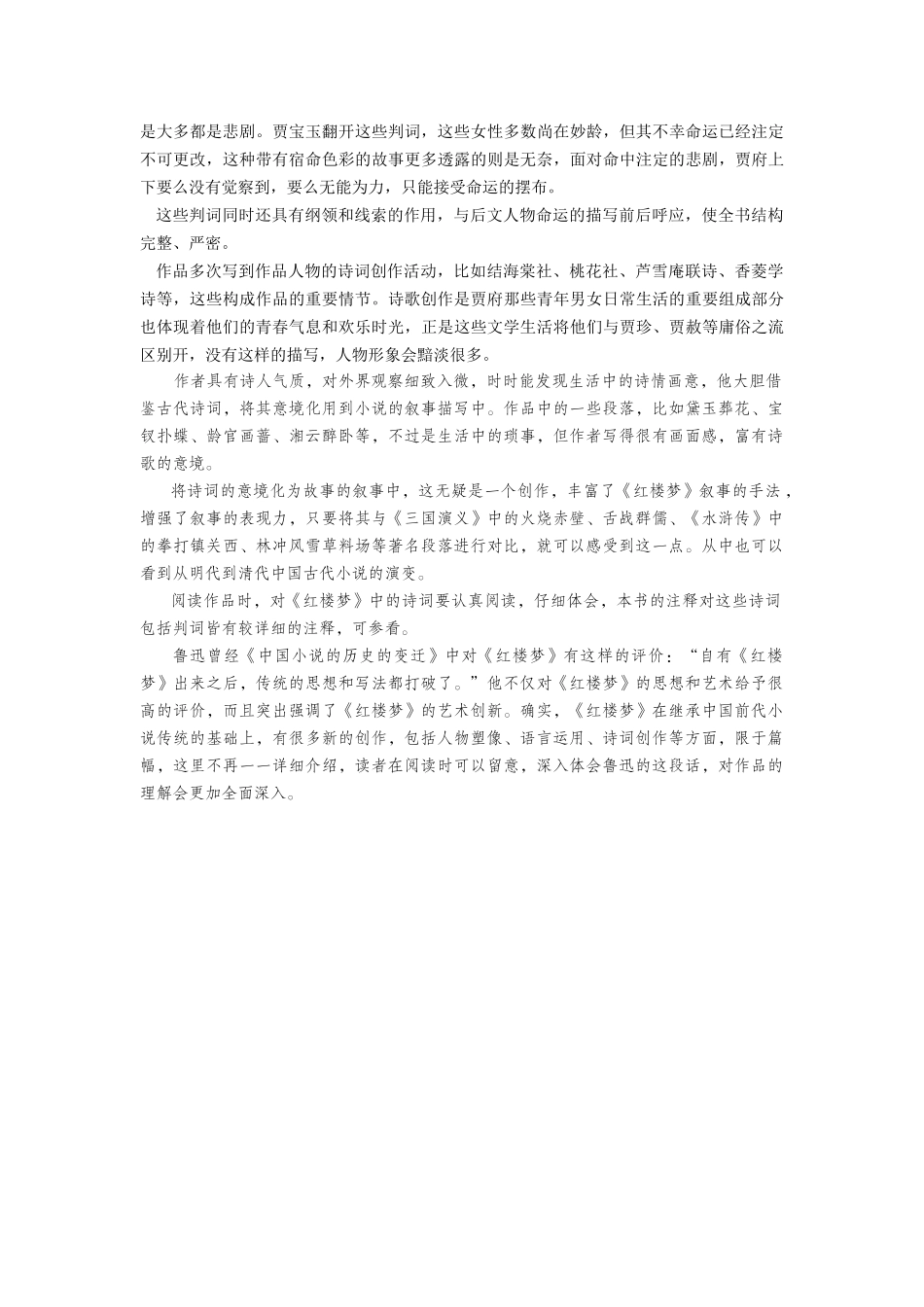《红楼梦》诗词导读阅读《红楼梦》,除人物、情节外,还有不少读者对其中的诗词印象深刻,其中一些名篇,比如金陵十二钗的判词、林黛玉的葬花词、贾宝玉的芙蓉诔等甚至可以达到背诵的程度。在诗词的运用方面,《红楼梦》有不少创新,这种创新既体现在诗词自身的创作上,也体现诗词与小说的有机融合上。《红楼梦》中各类诗词曲达到一百多首,数量还是相当多的,从文体上看,诗、词、曲皆有。从内容和功能来看,可分叙事与抒情两类,也有两者兼有者。小说文备众体,可以容纳各类文体。作品写到贾府人物特别是林黛玉等青年男女的文艺生活,特别是写到海棠社、桃花社、香菱学诗等,自然会写到诗词。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朋友敦诚、敦敏、张宜泉等都多次提及这一点。其诗作有奇气,“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敦诚《佩刀质酒歌》),才思敏捷如曹植,“诗才忆曹植”(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风格如唐代诗人李贺,“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敦诚《寄怀曹雪芹霑》)。曹雪芹的画作今天已无法看到了,但他的诗作则可以通过《红楼梦》来领略。能诗就决定了作品中诗作的高水准。其中有很多名篇比如脍炙人口的葬花词。即便是放在中国诗词史上,《红楼梦》的这些作品也是高水准的。当然,在作品中插入诗词不是为了卖弄才华,而是为了塑造人物、设计情节、抒发情感的艺术需要。比如林黛玉,她是一位高贵的女诗人形象,才华横溢,如果没有她做葬花词没有她教香菱做诗,其形象会暗淡很多,显得单薄。正是有了葬花词,有了菊花诗,有了与史湘云的联句,一位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女才子形象才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诗词成为塑造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薛宝钗、史湘云的形象也作品中的诗词,多通过作品中人物写出,作者采取按头戴帽的写法,那就是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修养来为其量身定做,做到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比如林黛玉,其诗风清丽脱俗,与薛宝钗的温柔敦厚截然不同,与史湘云、探春等人的风格也不一样。以第三十七回的秋爽斋偶结海棠社为例。在这一回里,作者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探春、史湘云多个人物出场,用同样的题目做诗,因各人性格、修养、造诣、理解不同,所写海棠诗自然各具特色,作者为每个人设计合乎其身份的诗歌作品,由此凸显每个人的性格。不仅各人诗作不同,而且做诗过程中的表现也都不一样,比如宝钗的沉稳,史湘云的性急,林黛玉的胸有成竹等,皆得到表现。这是需要高超的写作技巧的,比一般的诗词写作更难。且不说作者还要替薛蟠设计那种俗不可耐、令人喷饭的嗡嗡诗。这些诗词作品除了契合人物身份,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揭示了作品的内涵,增加了作品的抒情性。比如作品第五回的人物判词和套曲,预示了贾府及主要人物的命运,同时也使作品带有浓郁的感伤色彩。以判词而言,作品通过贾宝玉的视角,展示了金陵十二钗全部正册和部分副册、又副册的判词,通过诗词的方式暗示了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些命运和结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多都是悲剧。贾宝玉翻开这些判词,这些女性多数尚在妙龄,但其不幸命运已经注定不可更改,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故事更多透露的则是无奈,面对命中注定的悲剧,贾府上下要么没有觉察到,要么无能为力,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这些判词同时还具有纲领和线索的作用,与后文人物命运的描写前后呼应,使全书结构完整、严密。作品多次写到作品人物的诗词创作活动,比如结海棠社、桃花社、芦雪庵联诗、香菱学诗等,这些构成作品的重要情节。诗歌创作是贾府那些青年男女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着他们的青春气息和欢乐时光,正是这些文学生活将他们与贾珍、贾赦等庸俗之流区别开,没有这样的描写,人物形象会黯淡很多。作者具有诗人气质,对外界观察细致入微,时时能发现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他大胆借鉴古代诗词,将其意境化用到小说的叙事描写中。作品中的一些段落,比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龄官画蔷、湘云醉卧等,不过是生活中的琐事,但作者写得很有画面感,富有诗歌的意境。将诗词的意境化为故事的叙事中,这无疑是一个创作,丰富了《红楼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