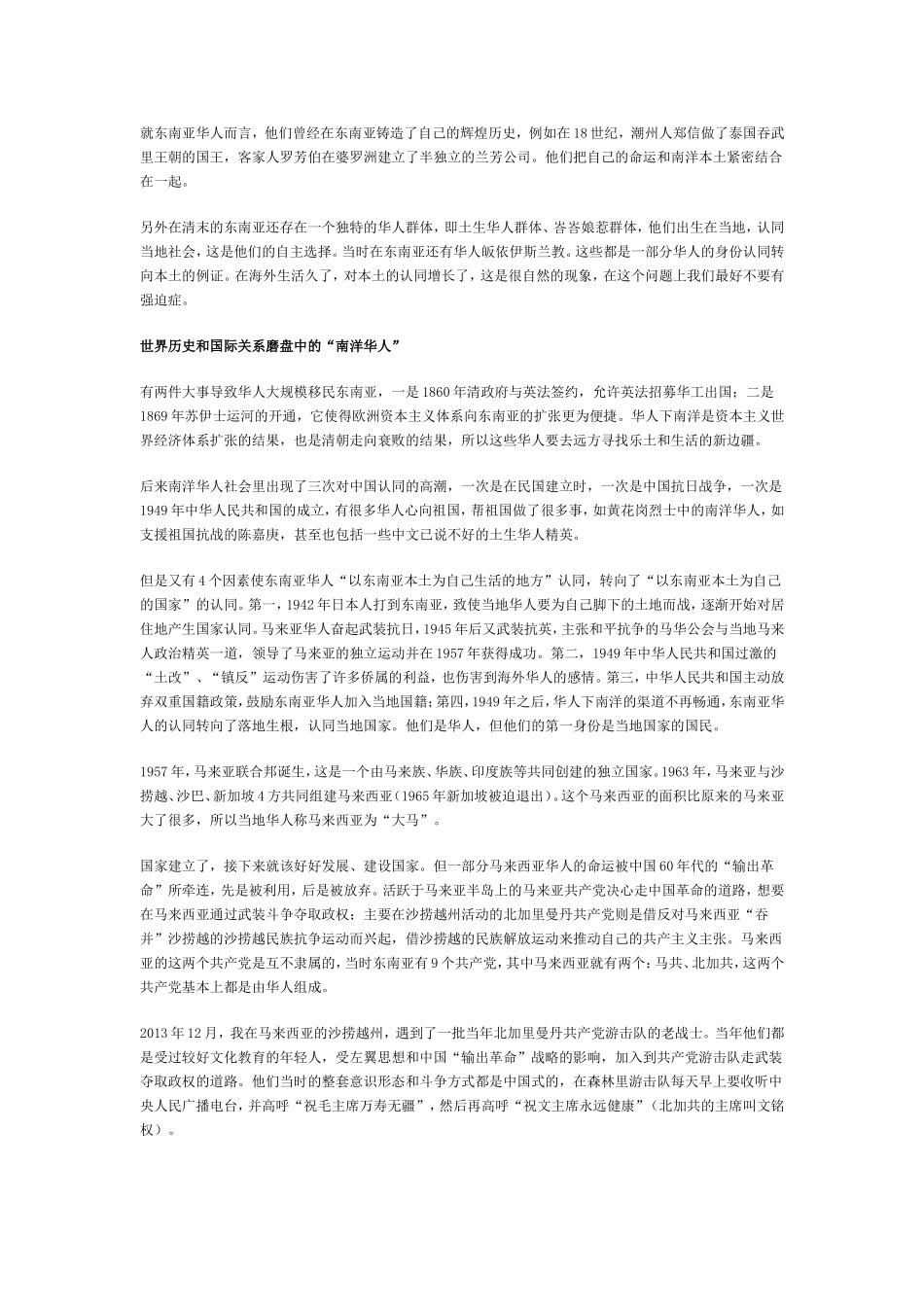庄礼伟华侨对中国有什么价值?2014-06-3016:31:20归档在我的博文|浏览130427次|评论100条5月3日的“2014东方历史日——新声·共鸣思想论坛”上,纪录片导演周兵、学者周少来和庄礼伟等就纪录片《下南洋》对南洋华人的生存与认同进行探讨。发言人: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避免以“中国中心”视角看待周边人民和他们的历史今天的主题是“下南洋”,但在亚洲东南区域这一块,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在人种、文化上都存在着双向交流的现象。其实中华民族与周边民族,历来在人种和文化上的交流都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曾说:汉族中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中有汉族。翦伯赞先生说得更明白:“中国人种的来源不是一元,而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即蒙古高原系与南太平洋系”,后者“从南太平洋出发沿马来半岛的海岸,向北推进,而达到了中国的南部”,成为中国西南夷和百越族的祖先。换言之,中国南方的先民们,身上还流动着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海岛人种的血液。东南亚曾经在人种和文化两个方面,都曾“北上”影响过中国,当然中国人种和文化也曾“南下”影响过东南亚。中国云桂粤闽地区与东南亚合在一起,在历史上可以算是一个亚洲的“历史次区域”,其内部的联系与交流是比较紧密的。周兵导演提到他在拍《下南洋》时非常小心要避免“中国中心”视角来看待东南亚华人。但在我看过的一些《下南洋》片段和刚才现场播放的片段中,色彩、旋律、文字的格调还是有点灰暗压抑,似乎在说──我们是中心,你们是无根漂泊,我们崛起了,你们还在困境当中。我们大陆中国人对海外华人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悲悯心态:他们离开中国失了根,日子是悲惨的,心情是绝望的,家山北望,终日以泪洗面,是需要被保护和被拯救的对象。但我接触过的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人不是这样的,他们过得很快乐充实,东南亚本土就是他们的家乡和祖国,当然也确实有一些老华人还是对“唐山”、祖籍地有很深的怀念和认同,但是东南亚华人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在东南亚本土出生的了。从华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来看,他们下南洋恰恰是为了摆脱在中国的凄苦命运,是为了摆脱家乡的“硕鼠”而去寻找远方的“乐土”。如果家乡很好、很宜居他们为什么要下南洋?孔夫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讲的也是跺脚要走、自由选择的心情。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华人下南洋,获得了很多改善个人命运的机会,他们在清末下南洋之后的几十年内,平均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祖籍地,并且在民风、智识上也有很大进步,所以他们积极支持中国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甚至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现在东南亚华人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当地国籍,都在脚踏实地地为自己的人生幸福而努力,他们不需要外界居高临下的悲悯。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妨做些社会学的比较调研,如自杀率、抑郁症发病率的比较,认真比较之后,也许我们对他们的认知、态度会有所改变。我们不要学欧洲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周边民族、我们的离散人口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悲悯。我们对海外华人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他们是海外游子,总是心系中国。但事实上海外华人的认同是多样化的,并且趋向于本土化。就东南亚华人而言,他们曾经在东南亚铸造了自己的辉煌历史,例如在18世纪,潮州人郑信做了泰国吞武里王朝的国王,客家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了半独立的兰芳公司。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南洋本土紧密结合在一起。另外在清末的东南亚还存在一个独特的华人群体,即土生华人群体、峇峇娘惹群体,他们出生在当地,认同当地社会,这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当时在东南亚还有华人皈依伊斯兰教。这些都是一部分华人的身份认同转向本土的例证。在海外生活久了,对本土的认同增长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不要有强迫症。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磨盘中的“南洋华人”有两件大事导致华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一是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签约,允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二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它使得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向东南亚的扩张更为便捷。华人下南洋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扩张的结果,也是清朝走向衰败的结果,所以这些华人要去远方寻找乐土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