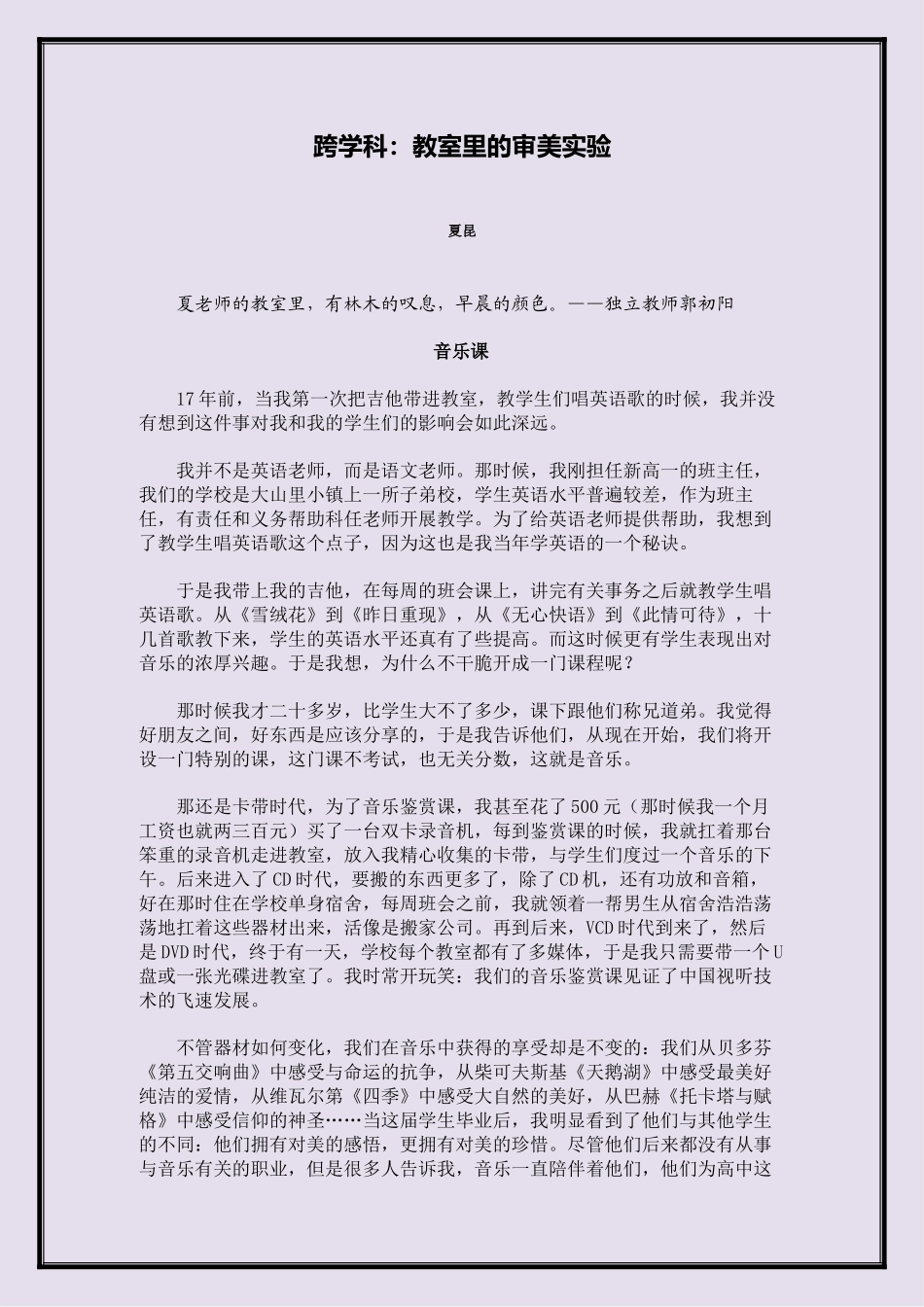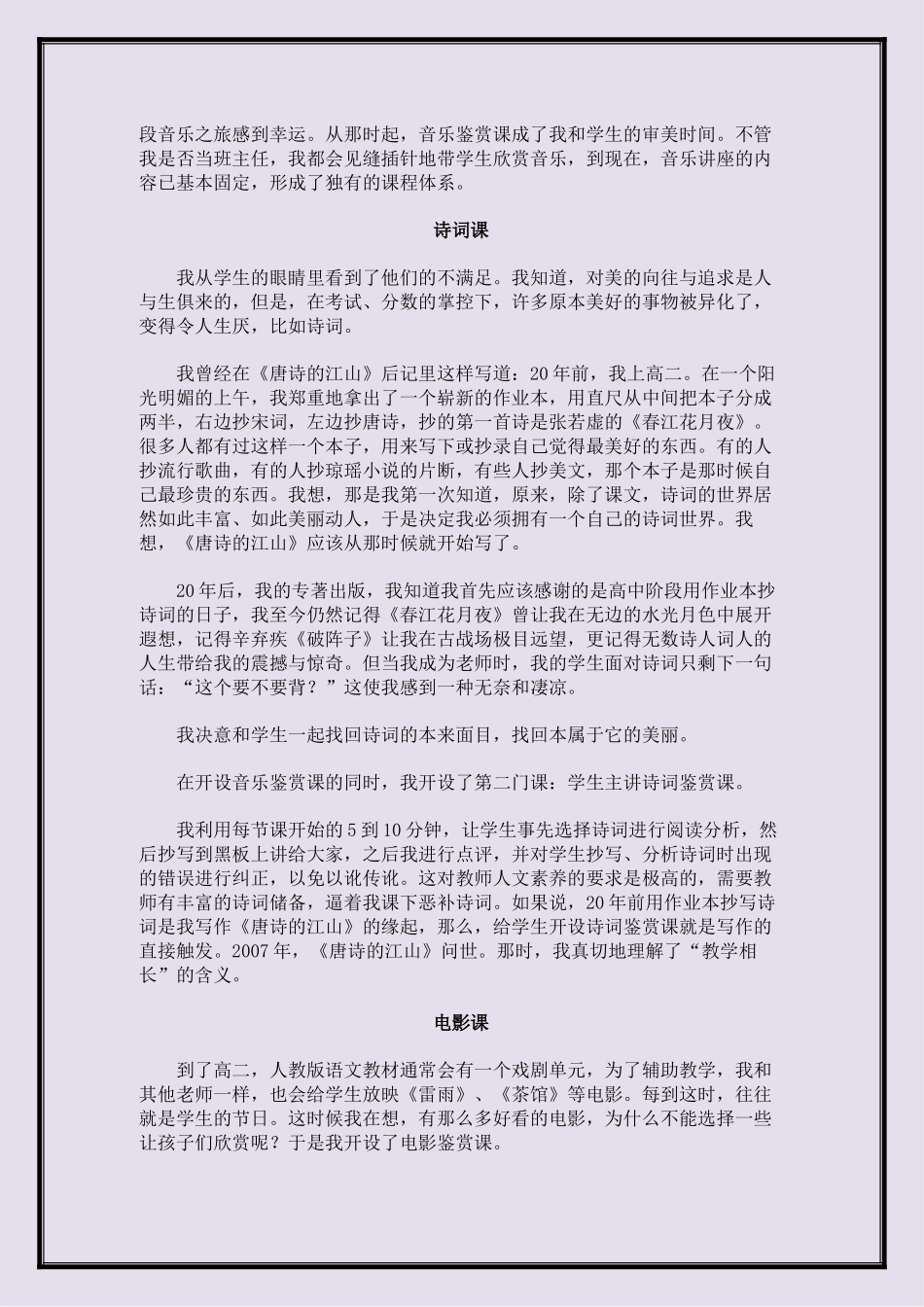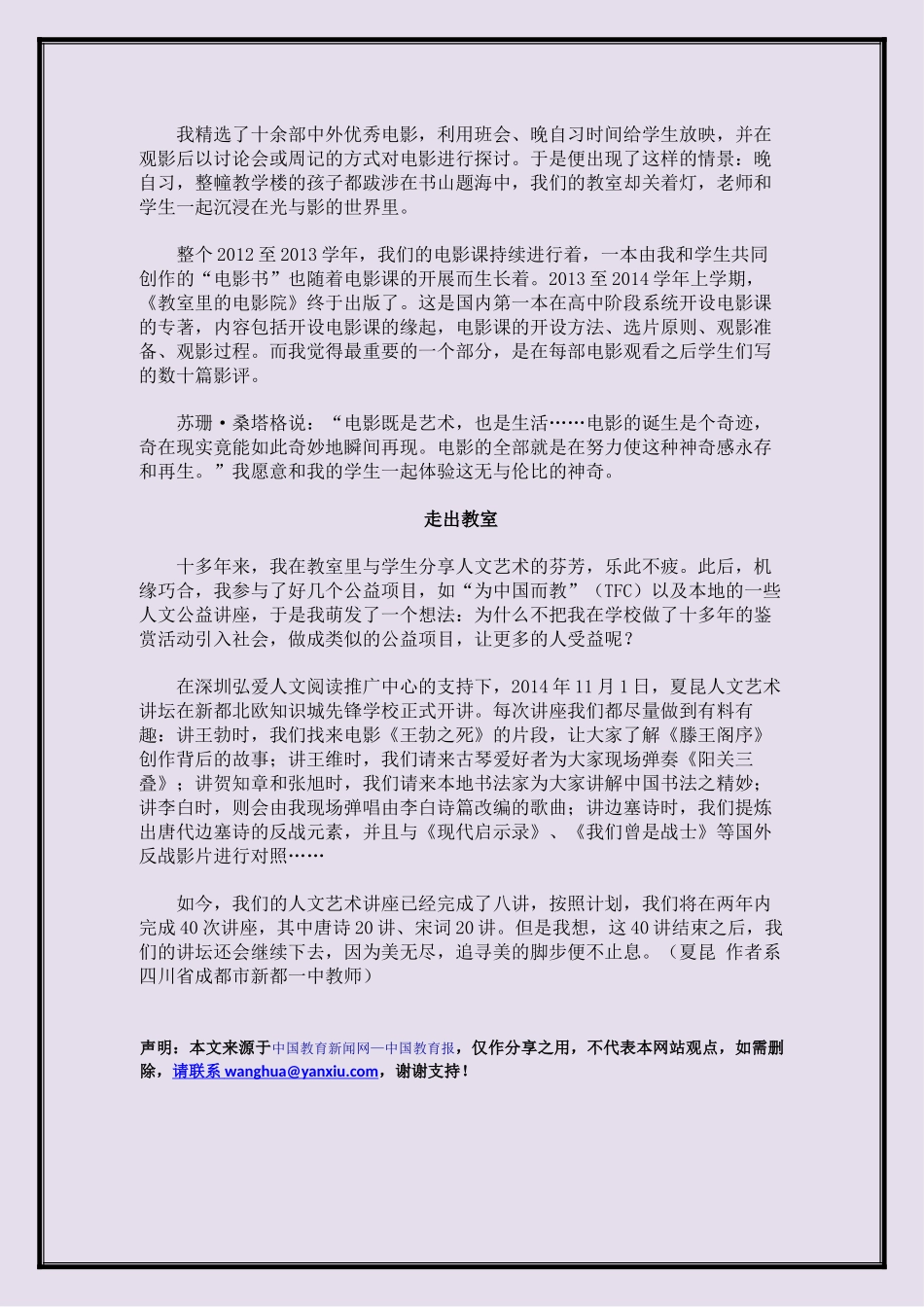跨学科:教室里的审美实验夏昆夏老师的教室里,有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独立教师郭初阳音乐课17年前,当我第一次把吉他带进教室,教学生们唱英语歌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件事对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影响会如此深远。我并不是英语老师,而是语文老师。那时候,我刚担任新高一的班主任,我们的学校是大山里小镇上一所子弟校,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差,作为班主任,有责任和义务帮助科任老师开展教学。为了给英语老师提供帮助,我想到了教学生唱英语歌这个点子,因为这也是我当年学英语的一个秘诀。于是我带上我的吉他,在每周的班会课上,讲完有关事务之后就教学生唱英语歌。从《雪绒花》到《昨日重现》,从《无心快语》到《此情可待》,十几首歌教下来,学生的英语水平还真有了些提高。而这时候更有学生表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于是我想,为什么不干脆开成一门课程呢?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比学生大不了多少,课下跟他们称兄道弟。我觉得好朋友之间,好东西是应该分享的,于是我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开设一门特别的课,这门课不考试,也无关分数,这就是音乐。那还是卡带时代,为了音乐鉴赏课,我甚至花了500元(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也就两三百元)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每到鉴赏课的时候,我就扛着那台笨重的录音机走进教室,放入我精心收集的卡带,与学生们度过一个音乐的下午。后来进入了CD时代,要搬的东西更多了,除了CD机,还有功放和音箱,好在那时住在学校单身宿舍,每周班会之前,我就领着一帮男生从宿舍浩浩荡荡地扛着这些器材出来,活像是搬家公司。再到后来,VCD时代到来了,然后是DVD时代,终于有一天,学校每个教室都有了多媒体,于是我只需要带一个U盘或一张光碟进教室了。我时常开玩笑:我们的音乐鉴赏课见证了中国视听技术的飞速发展。不管器材如何变化,我们在音乐中获得的享受却是不变的:我们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感受与命运的抗争,从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感受最美好纯洁的爱情,从维瓦尔第《四季》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从巴赫《托卡塔与赋格》中感受信仰的神圣……当这届学生毕业后,我明显看到了他们与其他学生的不同:他们拥有对美的感悟,更拥有对美的珍惜。尽管他们后来都没有从事与音乐有关的职业,但是很多人告诉我,音乐一直陪伴着他们,他们为高中这段音乐之旅感到幸运。从那时起,音乐鉴赏课成了我和学生的审美时间。不管我是否当班主任,我都会见缝插针地带学生欣赏音乐,到现在,音乐讲座的内容已基本固定,形成了独有的课程体系。诗词课我从学生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的不满足。我知道,对美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在考试、分数的掌控下,许多原本美好的事物被异化了,变得令人生厌,比如诗词。我曾经在《唐诗的江山》后记里这样写道:20年前,我上高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郑重地拿出了一个崭新的作业本,用直尺从中间把本子分成两半,右边抄宋词,左边抄唐诗,抄的第一首诗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本子,用来写下或抄录自己觉得最美好的东西。有的人抄流行歌曲,有的人抄琼瑶小说的片断,有些人抄美文,那个本子是那时候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除了课文,诗词的世界居然如此丰富、如此美丽动人,于是决定我必须拥有一个自己的诗词世界。我想,《唐诗的江山》应该从那时候就开始写了。20年后,我的专著出版,我知道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高中阶段用作业本抄诗词的日子,我至今仍然记得《春江花月夜》曾让我在无边的水光月色中展开遐想,记得辛弃疾《破阵子》让我在古战场极目远望,更记得无数诗人词人的人生带给我的震撼与惊奇。但当我成为老师时,我的学生面对诗词只剩下一句话:“这个要不要背?”这使我感到一种无奈和凄凉。我决意和学生一起找回诗词的本来面目,找回本属于它的美丽。在开设音乐鉴赏课的同时,我开设了第二门课:学生主讲诗词鉴赏课。我利用每节课开始的5到10分钟,让学生事先选择诗词进行阅读分析,然后抄写到黑板上讲给大家,之后我进行点评,并对学生抄写、分析诗词时出现的错误进行纠正,以免以讹传讹。这对教师人文素养的要求是极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