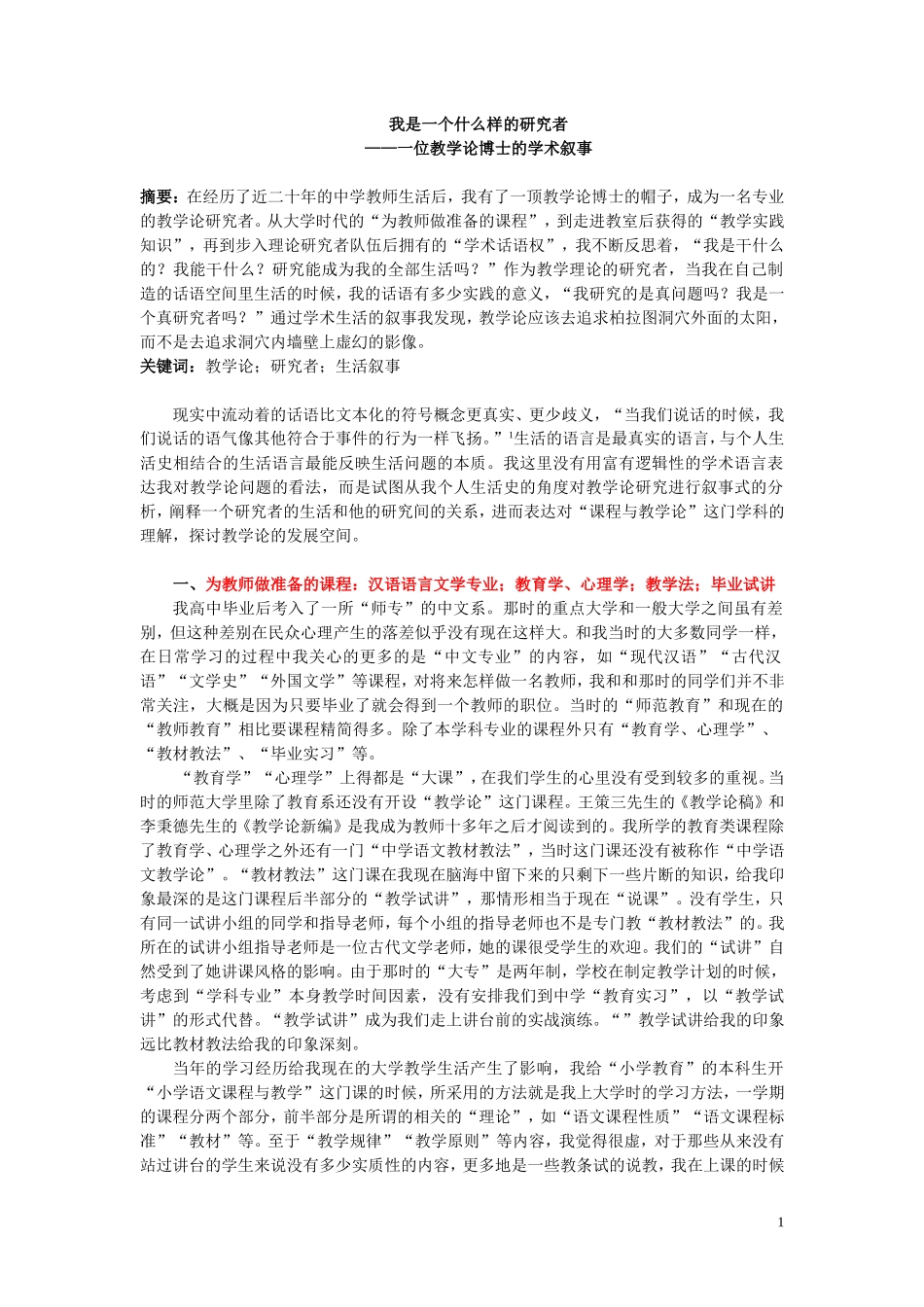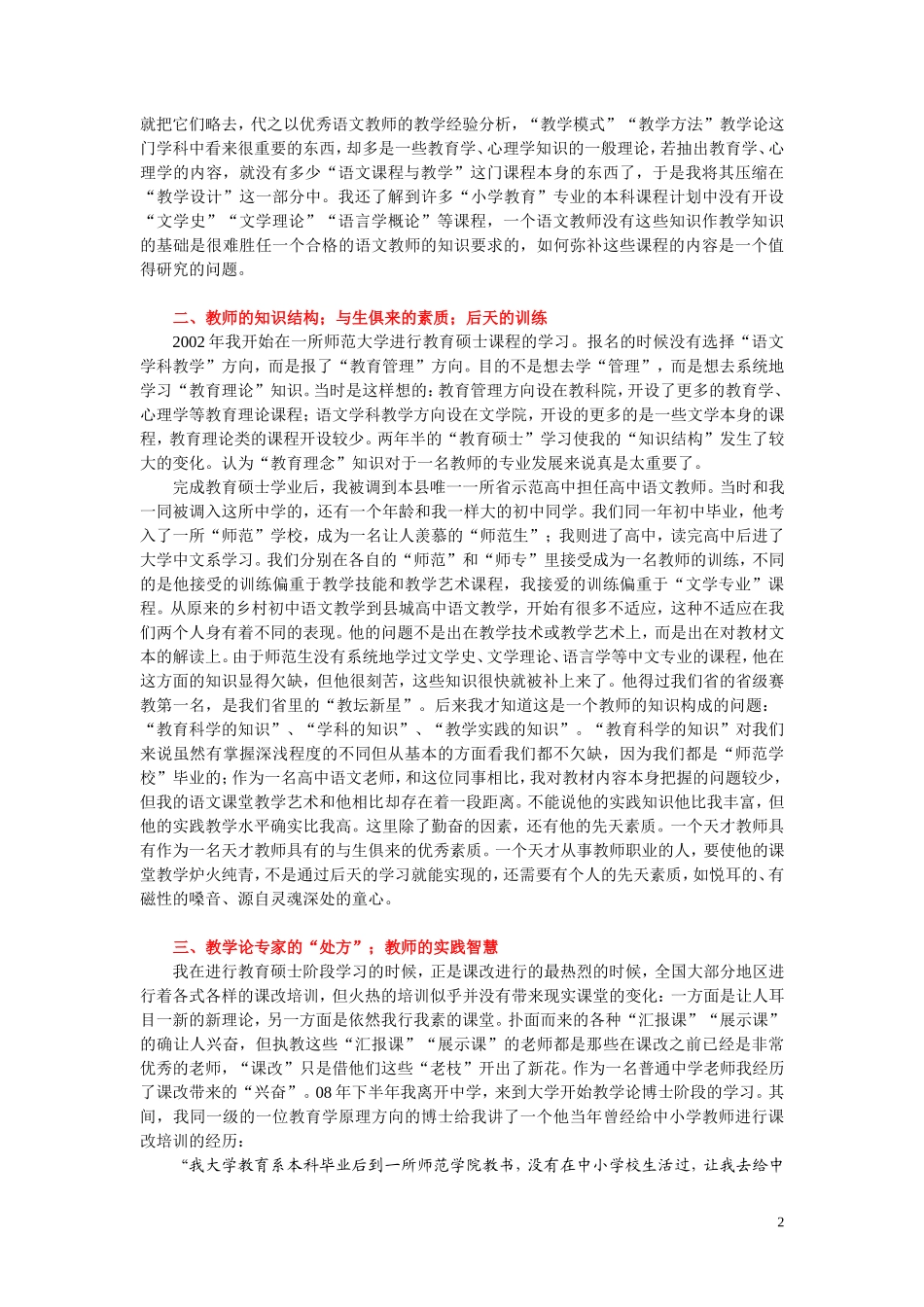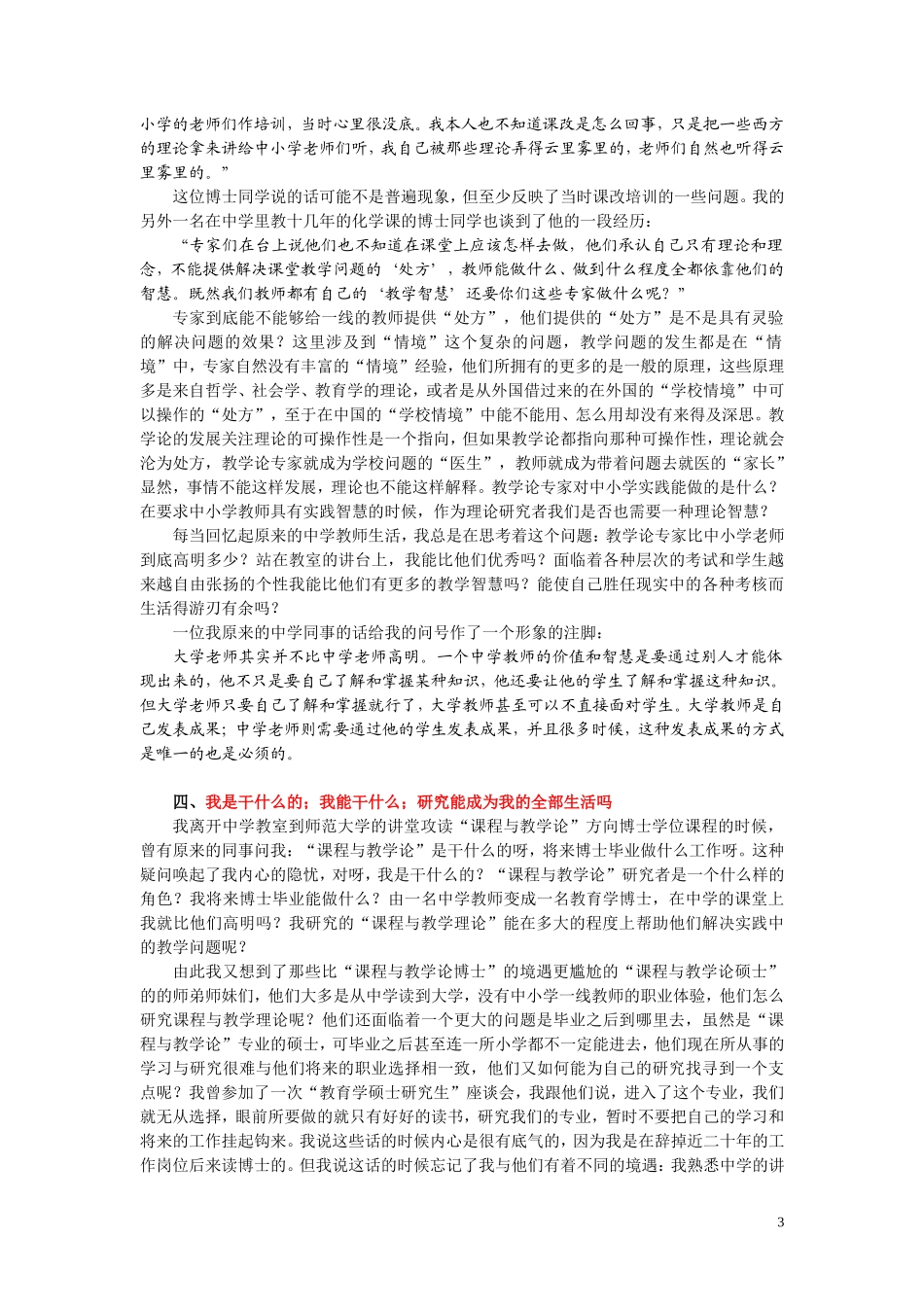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者——一位教学论博士的学术叙事摘要: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后,我有了一顶教学论博士的帽子,成为一名专业的教学论研究者。从大学时代的“为教师做准备的课程”,到走进教室后获得的“教学实践知识”,再到步入理论研究者队伍后拥有的“学术话语权”,我不断反思着,“我是干什么的?我能干什么?研究能成为我的全部生活吗?”作为教学理论的研究者,当我在自己制造的话语空间里生活的时候,我的话语有多少实践的意义,“我研究的是真问题吗?我是一个真研究者吗?”通过学术生活的叙事我发现,教学论应该去追求柏拉图洞穴外面的太阳,而不是去追求洞穴内墙壁上虚幻的影像。关键词:教学论;研究者;生活叙事现实中流动着的话语比文本化的符号概念更真实、更少歧义,“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话的语气像其他符合于事件的行为一样飞扬。”1生活的语言是最真实的语言,与个人生活史相结合的生活语言最能反映生活问题的本质。我这里没有用富有逻辑性的学术语言表达我对教学论问题的看法,而是试图从我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对教学论研究进行叙事式的分析,阐释一个研究者的生活和他的研究间的关系,进而表达对“课程与教学论”这门学科的理解,探讨教学论的发展空间。一、为教师做准备的课程: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毕业试讲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一所“师专”的中文系。那时的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之间虽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在民众心理产生的落差似乎没有现在这样大。和我当时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我关心的更多的是“中文专业”的内容,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史”“外国文学”等课程,对将来怎样做一名教师,我和和那时的同学们并不非常关注,大概是因为只要毕业了就会得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当时的“师范教育”和现在的“教师教育”相比要课程精简得多。除了本学科专业的课程外只有“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毕业实习”等。“教育学”“心理学”上得都是“大课”,在我们学生的心里没有受到较多的重视。当时的师范大学里除了教育系还没有开设“教学论”这门课程。王策三先生的《教学论稿》和李秉德先生的《教学论新编》是我成为教师十多年之后才阅读到的。我所学的教育类课程除了教育学、心理学之外还有一门“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当时这门课还没有被称作“中学语文教学论”。“教材教法”这门课在我现在脑海中留下来的只剩下一些片断的知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门课程后半部分的“教学试讲”,那情形相当于现在“说课”。没有学生,只有同一试讲小组的同学和指导老师,每个小组的指导老师也不是专门教“教材教法”的。我所在的试讲小组指导老师是一位古代文学老师,她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们的“试讲”自然受到了她讲课风格的影响。由于那时的“大专”是两年制,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考虑到“学科专业”本身教学时间因素,没有安排我们到中学“教育实习”,以“教学试讲”的形式代替。“教学试讲”成为我们走上讲台前的实战演练。“”教学试讲给我的印象远比教材教法给我的印象深刻。当年的学习经历给我现在的大学教学生活产生了影响,我给“小学教育”的本科生开“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这门课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我上大学时的学习方法,一学期的课程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所谓的相关的“理论”,如“语文课程性质”“语文课程标准”“教材”等。至于“教学规律”“教学原则”等内容,我觉得很虚,对于那些从来没有站过讲台的学生来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更多地是一些教条试的说教,我在上课的时候1就把它们略去,代之以优秀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分析,“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论这门学科中看来很重要的东西,却多是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一般理论,若抽出教育学、心理学的内容,就没有多少“语文课程与教学”这门课程本身的东西了,于是我将其压缩在“教学设计”这一部分中。我还了解到许多“小学教育”专业的本科课程计划中没有开设“文学史”“文学理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一个语文教师没有这些知识作教学知识的基础是很难胜任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的知识要求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