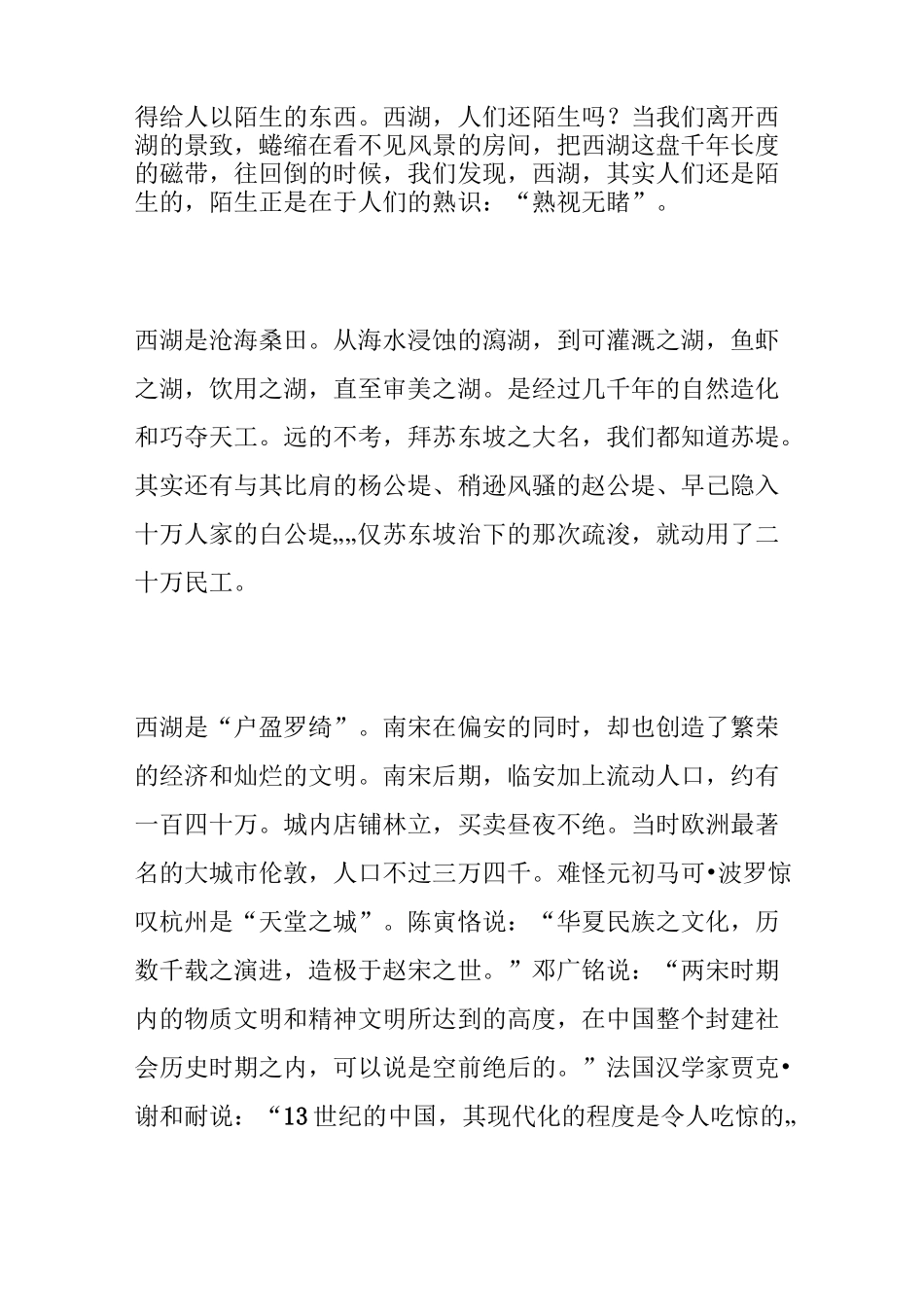(2)十集电视纪录片《西湖》解说词西湖不是纯自然的美景。她不像黄山、九寨沟,西湖是千百年来人类治理疏浚、依势造景的山水之湖泊;她不像漓江、张家界,西湖是千百年来人们感怀世事、寄托情绪的精神之湖泊。因此说,西湖的美是天造人设的,《西湖》纪录片亦复如此。许多第一次来到西湖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西湖之于中国人,太熟识了。因为熟识,后来便不大有人愿意说西湖,也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怎么也说不好西湖。近代以来,西湖没有足以背诵的文,没有足以传唱的歌,没有足以传世的画,当然也没有足以把玩的影像作品。影像作品,有出息的影像作品,是挑战观众的视觉经验,你得给人以陌生的东西。西湖,人们还陌生吗?当我们离开西湖的景致,蜷缩在看不见风景的房间,把西湖这盘千年长度的磁带,往回倒的时候,我们发现,西湖,其实人们还是陌生的,陌生正是在于人们的熟识:“熟视无睹”。西湖是沧海桑田。从海水浸蚀的瀉湖,到可灌溉之湖,鱼虾之湖,饮用之湖,直至审美之湖。是经过几千年的自然造化和巧夺天工。远的不考,拜苏东坡之大名,我们都知道苏堤。其实还有与其比肩的杨公堤、稍逊风骚的赵公堤、早己隐入十万人家的白公堤„„仅苏东坡治下的那次疏浚,就动用了二十万民工。西湖是“户盈罗绮”。南宋在偏安的同时,却也创造了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明。南宋后期,临安加上流动人口,约有一百四十万。城内店铺林立,买卖昼夜不绝。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大城市伦敦,人口不过三万四千。难怪元初马可•波罗惊叹杭州是“天堂之城”。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贾克•谢和耐说:“13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这个“现代化”还包括精神文明的程度,因此,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西湖是东南佛国。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除了庙宇林立、高僧大德云集之外,更重要的是,佛家义理通过日常生活渗入杭州人的饮食起居,一年一度,历时三个月的声势浩大的“香市”便是足证。不仅东南大地,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皆“认祖归宗”。道家在西湖有著名的“葛洪炼丹处”等十多处道观。马可•波罗之后,传教士们先后来到杭州,于是杭州有了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二十多座。伊斯兰教在杭州也有相当的传播,建有约五座清真寺。西湖是唐诗宋词。许多人初来乍到却似曾相识,是因为他们早就熟悉了文学的西湖:宋之问“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柳永“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文传千古的还有:李清照、林和靖、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陈亮、姜夔、梅尧臣、范成大、朱熹、岳飞、文天祥、吴文英元明清时的马可•波罗、于谦、袁宏道、张岱、袁枚、郑板桥、康有为、陈曾寿„„近当代的名人孙中山、张静江、蒋介石、司徒雷登、鲁迅、周作人、戴望舒、郁达夫、李叔同、夏衍、毛泽东、周恩来„„西湖是“勾栏瓦舍”中国的戏曲艺术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样式,肇始于南宋时期的杭州,戏和文自此合璧,南方人谓之“戏文”。汤显祖、关汉卿、李笠翁、洪异等都在西湖这个舞台上有过充分的表演。中国有四大民间故事,其中两个故事的发生地传说在西湖:《白蛇传》和《梁祝》。《白蛇传》被中国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所演绎,《梁祝》更借以西湖的音乐——越剧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誉满世界。西湖还有《红梅记》(李慧娘)和《杨乃武与小白菜》,这都成了戏。西湖是“壮怀激烈”西湖不乏秀美,西湖也有壮美,悲壮之美。旷日持久的宋金、宋元战争中,产生了一代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宗泽、刘铸、吴价、吴磷、岳飞、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