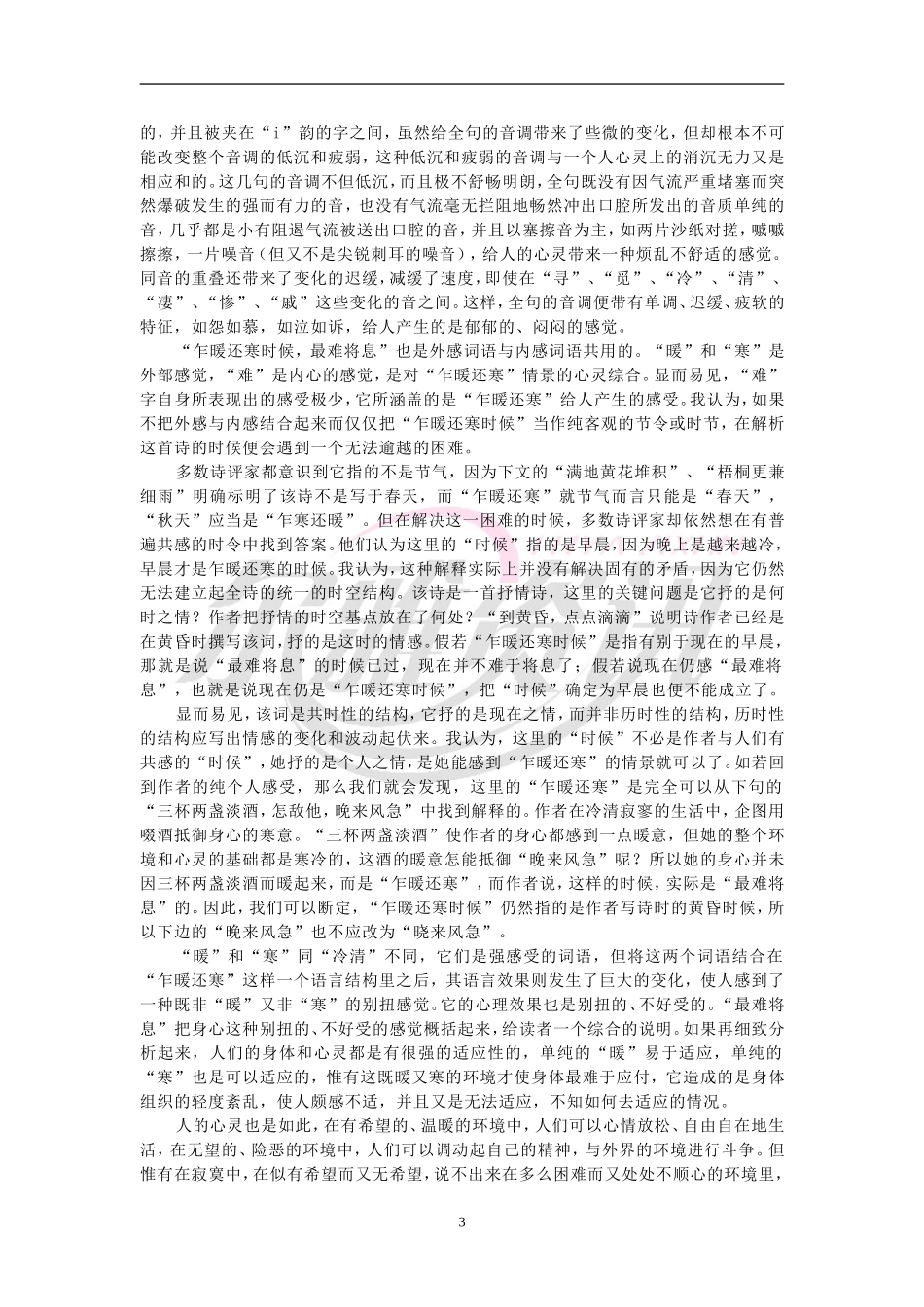内感与外感情绪与结构——李清照词《声声慢》(寻寻觅觅)赏析王富仁(选自《名作欣赏》1992年第5期。王富仁,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汕头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教授是少数能将学问做得极精细的学者之一,他常常能把最玄奥的道理用最明白晓畅的话表达出来。从1992年开始,王教授在《名作欣赏》上发表了一系列重新解读古典诗词的文章,其见解之独到、观点之深刻,给人以耳目一新、醍醐灌顶之感。)我认为,从诗学研究的角度,我们有必要把各民族语言中的词语分为三类:一、由人的外部感觉产生的词语;二、由人的自我心灵感受产生的词语;三、由语言自身的功能和要求产生的词语。第一类词语如“和”、“并且”、“虽然……,但是……”、“然而”、“既然”等等,它们既非人们在感触外部客观事物中产生的,也不是人们在感受自我心灵状态及其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除了它们有一定的声音和形状外,它们几乎没有实际的可感性,严格说来,这类词语不具有诗的语言的主要特征,即使有时出现在诗歌中,也只能作为另两类词的附属品在诗歌中占有一定的空间,以自己的声音参与诗的整体结构,而不具有更大的独立性。用得略多,它们就会对诗的审美效果起严重的破坏作用。第二类词语如悲哀、愁苦、烦闷、喜悦、愉快、欢乐等等,它们是人们对自我心灵的某种感情、情绪、精神状态进行感受的结果,是对它们的语言称谓和概括。表面看来,它们最像诗的语言,因为诗常常是用来表达人类的这种种情感和情绪的。但必须看到,这类词语的诗的品格是极为低下的,因为它们仅有很薄弱的表现性。它们是说明性的,而非表现性的,它们使我们“知”的功能大大超过使我们“感”的功能。当一个人说“我很痛苦”或“我很高兴”的时候,尽管我们高度信赖他的真诚性,但我们依然只是在理智上知道他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灵状态,却不能像他本人一样感到痛苦或高兴。在诗歌中,这类词语起到的主要是提示作用,而不是表现性的作用。缺乏一定的表现基础,这类词语是无法发挥自己的提示作用的。这使我们想起了辛弃疾的一首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实际是说“愁”字本身对人的悲情愁绪实际并没有多显著的表现性,倒是“欲说还休”的外部表现和“天凉好个秋”这样的人物语言更能传达他的内心愁绪。第三类词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可感的对象及其特征,一种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直接而又明确感到的事物及其特征,如宇宙、国家、人民、政党、哲学、制度、原子、细菌、维生素等等,这些词语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具有有限的表现性能,如法西斯、白色恐怖,其自身便能给人产生一种恐怖、憎恨、反感的心灵感觉,但即使这样,也不如希特勒、绞刑架等具体可感的形象具有诗的语言的特征。诗的语言更多地集中在第一种用视、听、嗅、味、触诸多外感器官(视觉中的感觉更丰富、更有强烈的表现性)直接感觉到的对象及其特征的语词。这类直感中的词语之所以具有最强的表现性,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具象的(其中如寒、暖、香、涩等并不具有特定形象),更因为它们与人的心灵状态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人类语言的称谓内心感受的词语中,有很多便直接借自外感的词语,如心寒的寒,(心灵)痛苦的痛和苦。上面我们说的是词语自身的表现性,但它们自身还不是诗,“花红”“柳绿”是常1常出现的词语,但它们各自分离开来,却不是诗的本身。诗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结构,这种语言结构与人的内心情感、情绪、精神状态的结构有一种对应关系。只有如此,它才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构成了一个语言中介,使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和情绪的交流成为可能。从语言的角度讲,人类的内心感受不能由表达内心感受的词语直接进行传达,它必须由以外感产生的词语为主体组成的特殊语言结构来承担,因而人类需要文学,需要诗,我认为,从这里我们才可能感到文学和诗的本质所在。下面我们具体欣赏和分析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关于开首这几句,人们说的已经够多,但我认为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