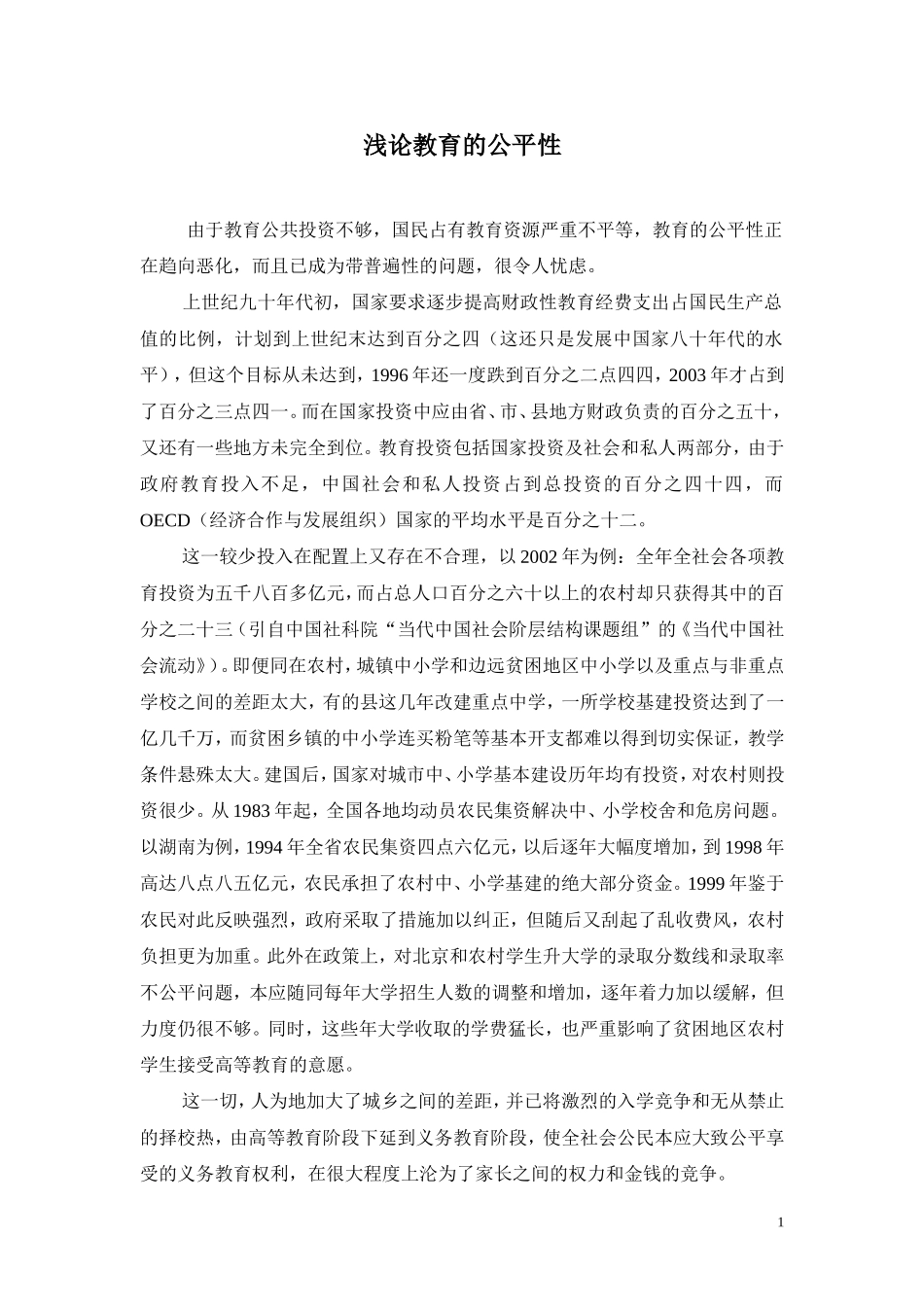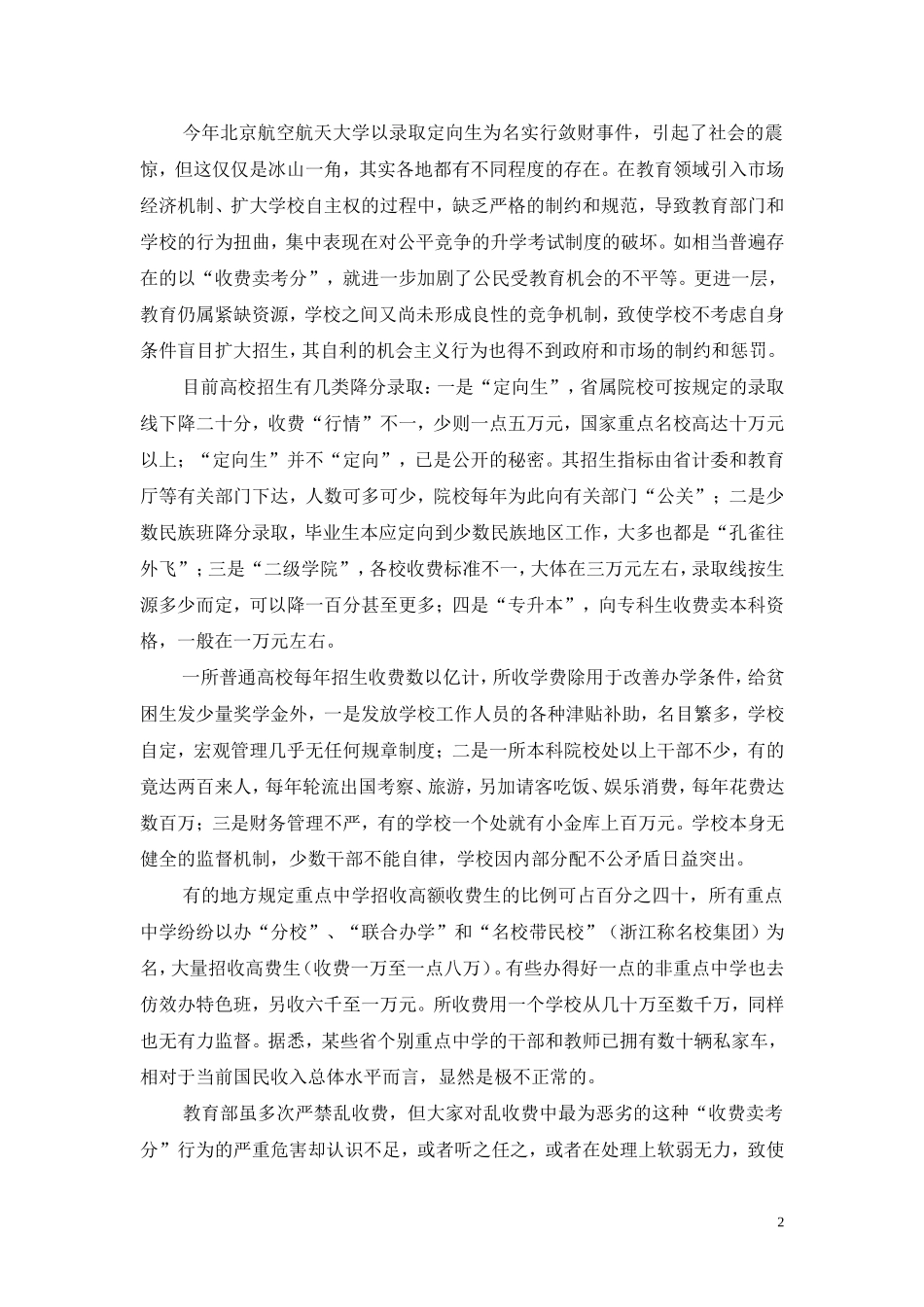浅论教育的公平性由于教育公共投资不够,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教育的公平性正在趋向恶化,而且已成为带普遍性的问题,很令人忧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计划到上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这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的水平),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百分之二点四四,2003年才占到了百分之三点四一。而在国家投资中应由省、市、县地方财政负责的百分之五十,又还有一些地方未完全到位。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四,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是百分之十二。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五千八百多亿元,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太大,有的县这几年改建重点中学,一所学校基建投资达到了一亿几千万,而贫困乡镇的中小学连买粉笔等基本开支都难以得到切实保证,教学条件悬殊太大。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以湖南为例,1994年全省农民集资四点六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高达八点八五亿元,农民承担了农村中、小学基建的绝大部分资金。1999年鉴于农民对此反映强烈,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以纠正,但随后又刮起了乱收费风,农村负担更为加重。此外在政策上,对北京和农村学生升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和录取率不公平问题,本应随同每年大学招生人数的调整和增加,逐年着力加以缓解,但力度仍很不够。同时,这些年大学收取的学费猛长,也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这一切,人为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已将激烈的入学竞争和无从禁止的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家长之间的权力和金钱的竞争。1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录取定向生为名实行敛财事件,引起了社会的震惊,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其实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缺乏严格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为扭曲,集中表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破坏。如相当普遍存在的以“收费卖考分”,就进一步加剧了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更进一层,教育仍属紧缺资源,学校之间又尚未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致使学校不考虑自身条件盲目扩大招生,其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得不到政府和市场的制约和惩罚。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二十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一点五万元,国家重点名校高达十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其招生指标由省计委和教育厅等有关部门下达,人数可多可少,院校每年为此向有关部门“公关”;二是少数民族班降分录取,毕业生本应定向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大多也都是“孔雀往外飞”;三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在三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一百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一万元左右。一所普通高校每年招生收费数以亿计,所收学费除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给贫困生发少量奖学金外,一是发放学校工作人员的各种津贴补助,名目繁多,学校自定,宏观管理几乎无任何规章制度;二是一所本科院校处以上干部不少,有的竟达两百来人,每年轮流出国考察、旅游,另加请客吃饭、娱乐消费,每年花费达数百万;三是财务管理不严,有的学校一个处就有小金库上百万元。学校本身无健全的监督机制,少数干部不能自律,学校因内部分配不公矛盾日益突出。有的地方规定重点中学招收高额收费生的比例可占百分之四十,所有重点中学纷纷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和“名校带民校”(浙江称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