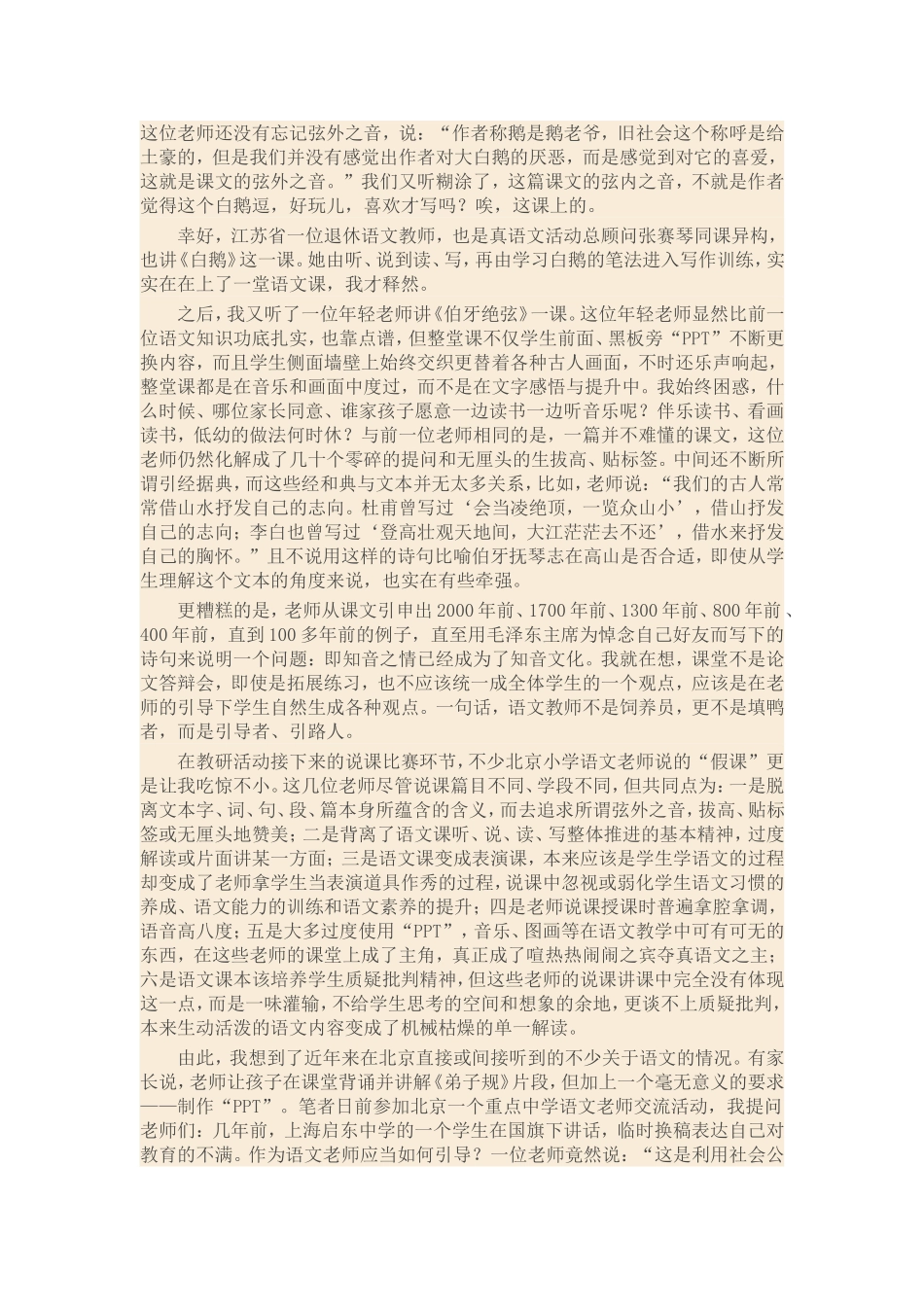北京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王旭明当下学校语文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大家都不满意,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检测质量报告》表明,在语文、数学、科学和思品四门学科中,语文的合格率最低,其中有近30%学生的语文成绩处于基本合格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下语文课时数是1963年的一半,效果与1963年相比,却没有明显不同。这就说明语文课多上、少上甚至不上,与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并没有多大关系。还有一项调查说,在某地中学生17门课程抽样调查中,学生最不喜欢上的是语文课——我的天啊!教师配备最多、学生用时最多、国家最重视的母语学科,落实在课堂教学上竟是如此结果,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最近,我在北京的一个教学研讨活动上听了课,参与者多是来自北京所谓重点小学的语文老师,他们所上的语文课竟与语文相去甚远充斥了许多非语文的东西。联想到近期不断有家长跟我反映其子女在小学、中学及高中语文课上所学、所知、所感;再联想到两年前真语文北京启动仪式上,听到的许多充满假语文元素的语文课,我因此愈发担忧,也印证了这样的判断:北京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先说、也重点说说北京的小学语文课堂吧。我始终认为中国汉语水平的真正提高在未来,在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因此我尤其关注小学语文教育和语文老师我听了一位年轻女语文老师讲丰子恺先生的《白鹅》。这是一篇生活散文,层次分明、语言生动、感情真挚,如果老师按照语文教学规律,紧紧抓住字、词、句、段,听、说、读、写整体推进,该多好啊。可是,这位老师一上课就用丰子恺的若干幅漫画引入,而漫画内容既和课文内容无关,又与白鹅无关,一边看漫画还一边问孩子:“感动了没有?为什么感动?”不要说学生,就是成人见到她展示的漫画也只是会心一笑而已,哪来的感动?原来老师要引入她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个小孩用他自己柔软的善心,感到桌子的感觉,看来,所有的生命都是需要呵护的。”我的生命已经老矣,第一次听说桌子也是有生命的!老师还不过瘾,一定要引入她对丰子恺的理解,说“透过小事、小画面之后,我们得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丰子恺说最喜欢弦外有余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篇散文的弦外之音”。一篇小短文,老师就是这样硬生生地拔高、贴标签,要引出弦外之音。恕我直言,我从小读《白鹅》,没有悟出弦外有什么音,也许我从小没有学好语文吧?!这样五六分钟过去之后,老师把一篇完整的文章化成了几十个零碎的小问题,无休止地问学生,既没有抓住词语重点,许多内容也离开文本本身,中间虽然有字词的校正和朗读,但完全是应景的,是为老师表演服务的。最糟糕的是,这位老师自己范读了一段课文,不仅让学生给自己掌声,还要问学生“老师读得怎么样,能不能把鹅和狗吃饭时的不同读出来”。四五个学生当然都说老师读得好,最后一位说:“我觉得老师读得特别好,因为,您用讲故事的方式读出来了。”老师当堂高度评价这位学生:“同学们再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他不仅把真诚的赞美献给老师,还告诉同学们读书的时候要像讲故事一样。”问题是,我整堂课听下来,从老师的讲课语言到她读范文的语言,毫无讲故事的感觉,都是用高八度的矫情做作腔调,自始至终像是一位二流演员在表演。退一步说,就是真像讲故事,也不要这样引导学生当面赞美老师啊!讲课结尾,这位老师还没有忘记弦外之音,说:“作者称鹅是鹅老爷,旧社会这个称呼是给土豪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出作者对大白鹅的厌恶,而是感觉到对它的喜爱,这就是课文的弦外之音。”我们又听糊涂了,这篇课文的弦内之音,不就是作者觉得这个白鹅逗,好玩儿,喜欢才写吗?唉,这课上的。幸好,江苏省一位退休语文教师,也是真语文活动总顾问张赛琴同课异构,也讲《白鹅》这一课。她由听、说到读、写,再由学习白鹅的笔法进入写作训练,实实在在上了一堂语文课,我才释然。之后,我又听了一位年轻老师讲《伯牙绝弦》一课。这位年轻老师显然比前一位语文知识功底扎实,也靠点谱,但整堂课不仅学生前面、黑板旁“PPT”不断更换内容,而且学生侧面墙壁上始终交织更替着各种古人画面,不时还乐声响起,整堂课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