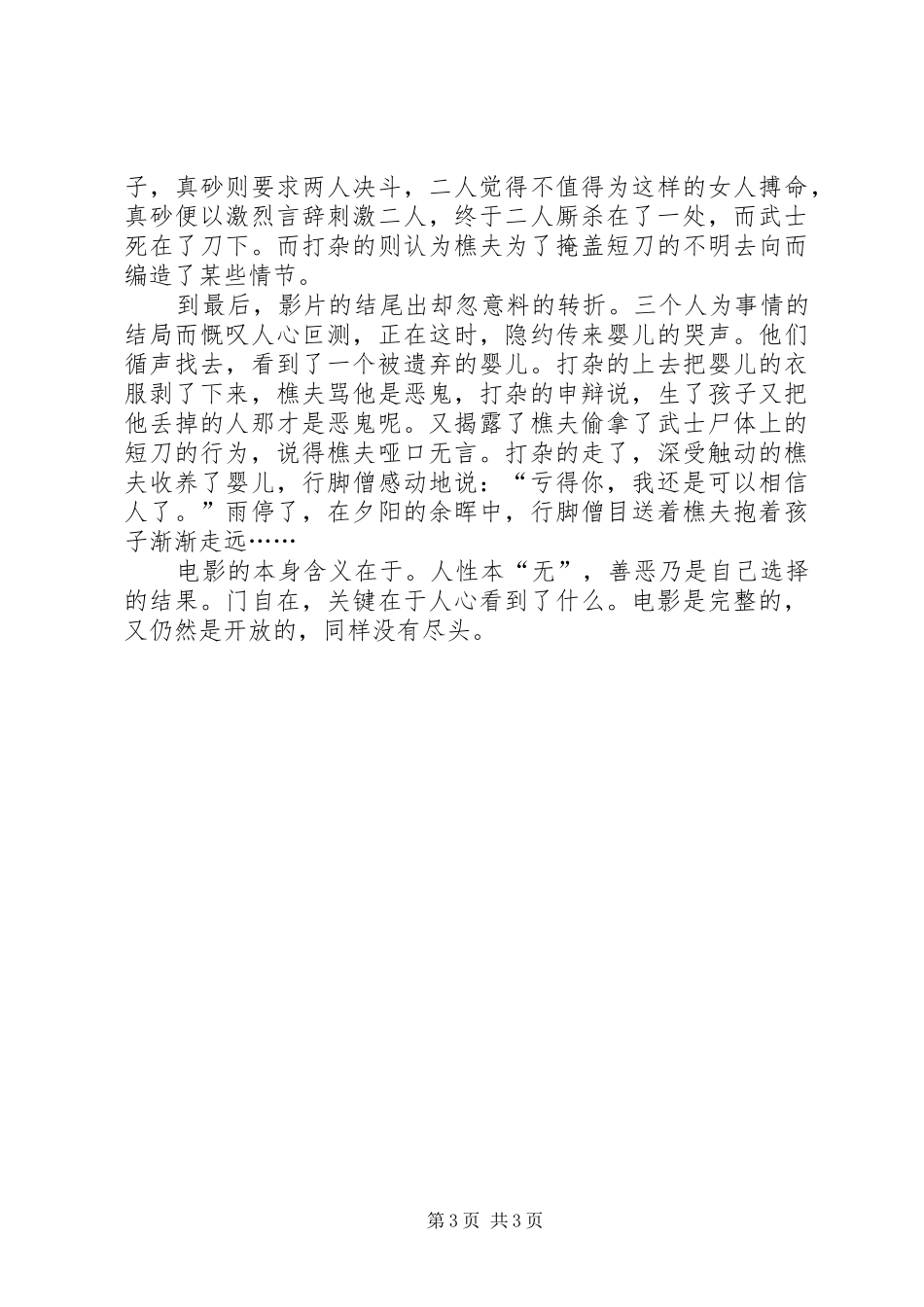观《生门》有感5篇以自在门观七十二变—观《罗生门》有感东方电影界的大师—黑泽明的电影是不可磨灭的经典。《菊与刀》是代表,而《罗生门》更是在特殊的叙事模式中将故事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叙事艺术高度。叙事是通过外部事件的描绘来把握社会现实本身,是用话语来虚构世界。这个用话语重构的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虽然不等于现实本身,但却比现实本身更可能在本质的层次上揭示社会现实的内在意义。影片借风雨交加的“罗生门”为场景,让三个在这里避雨的人谈论“竹丛中”的杀人案,从强盗、武士之妻、武士、樵夫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个凶杀事件。在这个过程中,观者的视角和人物是平行的,没有走上帝视角,而是通过人物本身各自的叙述来道出故事的发生过程。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众多人性。这就是《罗生门》最为引人入胜的第三人称视点。第三人称视点即叙述者是用他者的口吻叙述故事的,接受者只知道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事,内心的活动在影片中不被叙述。这种变化视点出发者的做法也许是跟现实最近的一种叙述方式,因为世界事实上是由一个“我”和无数“他”构成的。让人忍不住探究:”真相究竟如何。“多重叙事中哪个才是真实的发生了。导演把太阳光线当做电影语言运用,既有流动跳跃之美,又透视心理活动,还传递纵欲快感。一开始,罗生门前暴雨倾盆,阴云密布,影多光少,形成罪恶感和压抑感。而审问中,法庭供述曝光过度,光多影少,明显夸饰失真。每个人喃喃自语。而关于事件的叙述时,林中案发现场光影斑驳,幽暗神秘,镜头摇移。强盗的说他很英勇的和武士比剑,赢得美人归,武士的妻子把自己形容成贞女烈妇,用自己的护身匕首刺死了丈夫。武士则通过灵媒自称壮烈的切腹。强盗骑着武士的马,带着武士的弓箭和腰刀,在逃逸的路上突然腹痛倒地,因此被捕手擒获,他当然是嫌犯;武士的妻子也在附近的庙里找到,两人被带到巡捕官署。可我们唯一知道已经发生的事件是:武士和他的新婚妻子真砂骑马乘穿过森林时,遭到强盗多襄丸的袭第1页共3页击,冲突的结果是武士丧命,他的妻子被奸污。而其中的细节却各有说词。强盗起歹心在先,得手之后,以为自己已经得到女人了。而让女人记忆最深的却是丈夫的眼神让她绝望。那眼神既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而是充满着鄙视,冷酷无比,令她战栗。宁愿他杀了自己,丈夫仍旧不言不动,眼光如剑。她绝望之下想与丈夫同归于尽,便以匕尖对准了丈夫,自己昏过去了;醒来后看到丈夫胸口插着那把短刀。武士只觉得妻子的“背叛”和“狠毒”,使他痛不欲生,拾起短刀,毅然自尽。每个人有自己的内心动机。武士憎恨妻子,是因为受到强盗强暴其妻子的强烈刺激,从而把内心痛苦投射为无辜女人的“罪恶”,这是怯懦胆小而又妄自尊大、男尊女卑思想顽固的男人常会有的心理指向方式。武士说是自杀,其实想怪罪女人杀了他,女人割断绳子,要他与强盗决斗,确是他的间接死因。同时,他不肯承认输给强盗,说为自杀,也出于这种心理需要。因心理需要而下意识地编谎说事,分析起来,故事里总会有一两个事实的基点。武士说他死在匕首下,应该是事实,因为他临死知道刺进胸口的是匕首,心理并不需要在这种地方说谎。女人其实未逃走,而是极度恐惧地旁观战斗。她看到匕尖对准丈夫时吓得昏死过去,醒来又看到丈夫胸前插的是匕首,而这场战斗正是她用匕首割断绳子挑起的,所以她自责自罪,认为是自己刺死了丈夫。她的心理需要是强调自己的行为另有原因,即丈夫那冷酷鄙视的眼光,以稍稍减轻一点自己并没有的罪责。这女人的心理需要实在很可怜。一切文学表象都执着于主观真实而非客观真实。那阵凉爽的风,不仅吹开了美女的面纱,更吹开了邪念和万劫不复的罗生门。人心的根本缺陷,在于这缺陷几乎不可克服。那途中突然出现的神秘的风,撩动着人心,心口不一怕是通病吧,一旦学会,再难戒掉。所以审问中现出众生百态,就算讲述者本身也逃不了,一个谎言往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弥补。在罗生门下,樵夫向行脚僧和打杂的承认自己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者,在他的描述中,强盗奸污真砂后要真砂做自己的妻第2页共3页子,真砂则要求两人决斗,二人觉得不值得为这样的女人搏命,真砂便以激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