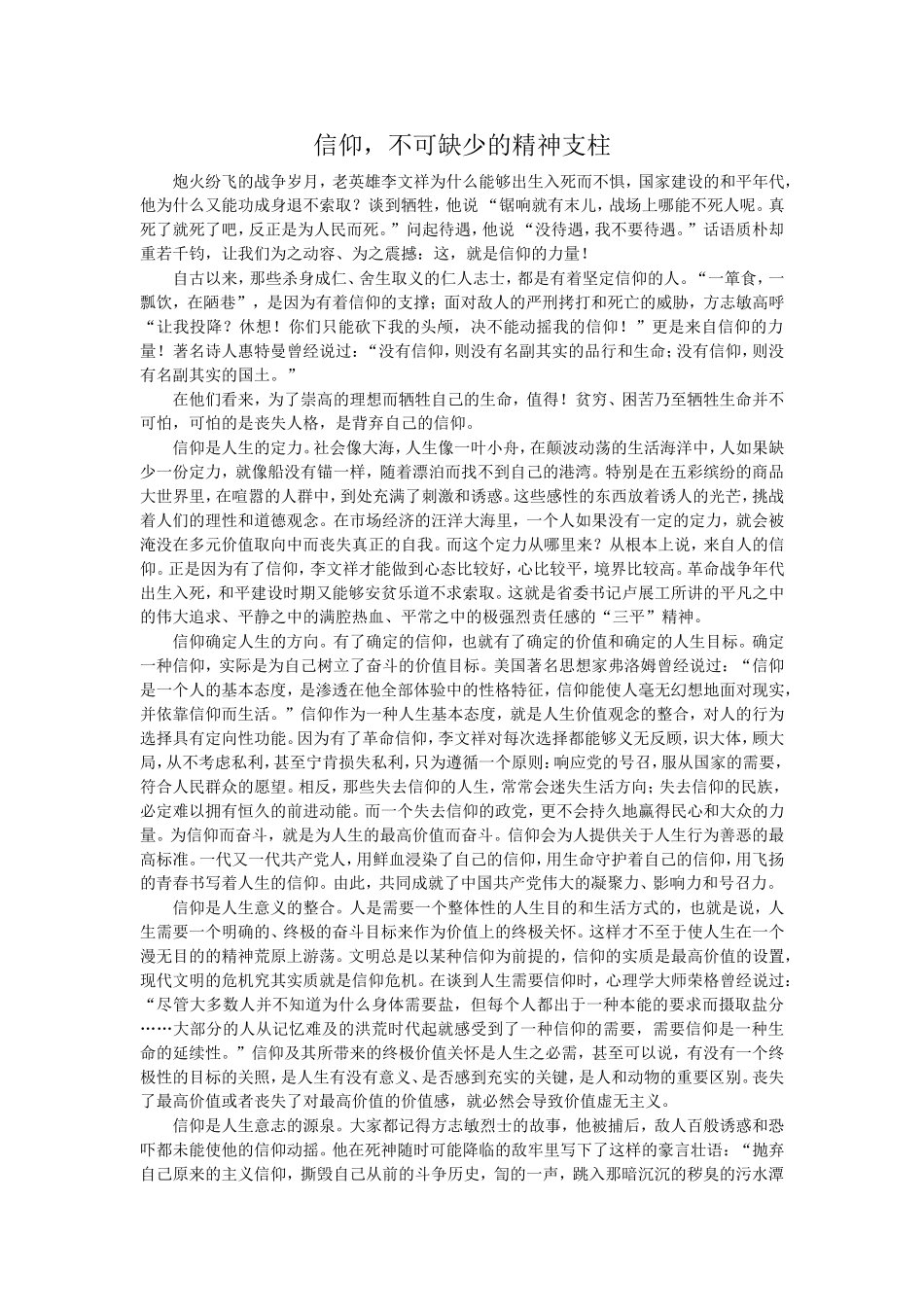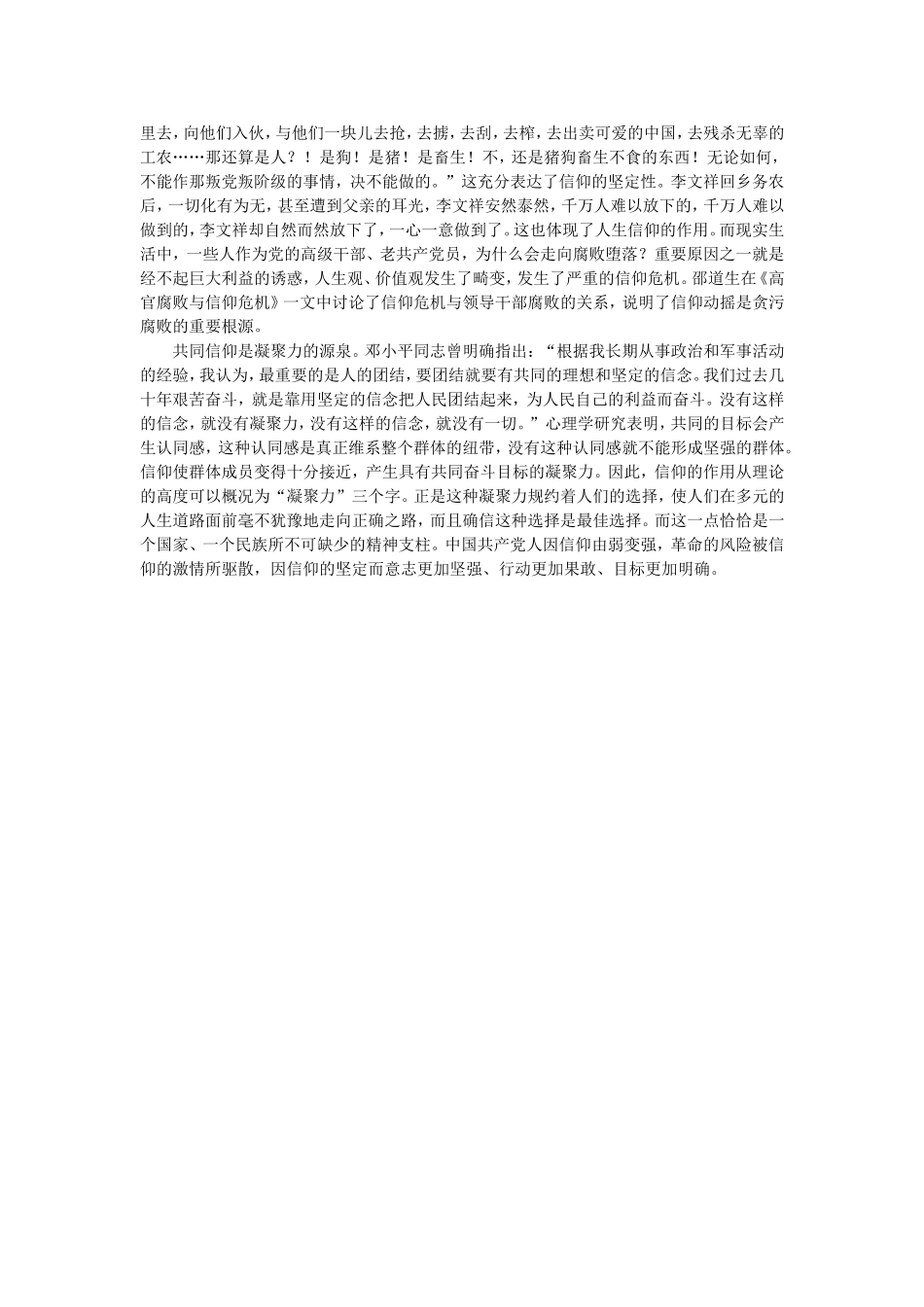信仰,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炮火纷飞的战争岁月,老英雄李文祥为什么能够出生入死而不惧,国家建设的和平年代,他为什么又能功成身退不索取?谈到牺牲,他说“锯响就有末儿,战场上哪能不死人呢。真死了就死了吧,反正是为人民而死。”问起待遇,他说“没待遇,我不要待遇。”话语质朴却重若千钧,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震撼: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自古以来,那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都是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是因为有着信仰的支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的威胁,方志敏高呼“让我投降?休想!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更是来自信仰的力量!著名诗人惠特曼曾经说过:“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在他们看来,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值得!贫穷、困苦乃至牺牲生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人格,是背弃自己的信仰。信仰是人生的定力。社会像大海,人生像一叶小舟,在颠波动荡的生活海洋中,人如果缺少一份定力,就像船没有锚一样,随着漂泊而找不到自己的港湾。特别是在五彩缤纷的商品大世界里,在喧嚣的人群中,到处充满了刺激和诱惑。这些感性的东西放着诱人的光芒,挑战着人们的理性和道德观念。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定力,就会被淹没在多元价值取向中而丧失真正的自我。而这个定力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来自人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信仰,李文祥才能做到心态比较好,心比较平,境界比较高。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和平建设时期又能够安贫乐道不求索取。这就是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讲的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的“三平”精神。信仰确定人生的方向。有了确定的信仰,也就有了确定的价值和确定的人生目标。确定一种信仰,实际是为自己树立了奋斗的价值目标。美国著名思想家弗洛姆曾经说过:“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征,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信仰作为一种人生基本态度,就是人生价值观念的整合,对人的行为选择具有定向性功能。因为有了革命信仰,李文祥对每次选择都能够义无反顾,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考虑私利,甚至宁肯损失私利,只为遵循一个原则: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相反,那些失去信仰的人生,常常会迷失生活方向;失去信仰的民族,必定难以拥有恒久的前进动能。而一个失去信仰的政党,更不会持久地赢得民心和大众的力量。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而奋斗。信仰会为人提供关于人生行为善恶的最高标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用鲜血浸染了自己的信仰,用生命守护着自己的信仰,用飞扬的青春书写着人生的信仰。由此,共同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信仰是人生意义的整合。人是需要一个整体性的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的,也就是说,人生需要一个明确的、终极的奋斗目标来作为价值上的终极关怀。这样才不至于使人生在一个漫无目的的精神荒原上游荡。文明总是以某种信仰为前提的,信仰的实质是最高价值的设置,现代文明的危机究其实质就是信仰危机。在谈到人生需要信仰时,心理学大师荣格曾经说过:“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身体需要盐,但每个人都出于一种本能的要求而摄取盐分……大部分的人从记忆难及的洪荒时代起就感受到了一种信仰的需要,需要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性。”信仰及其所带来的终极价值关怀是人生之必需,甚至可以说,有没有一个终极性的目标的关照,是人生有没有意义、是否感到充实的关键,是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丧失了最高价值或者丧失了对最高价值的价值感,就必然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信仰是人生意志的源泉。大家都记得方志敏烈士的故事,他被捕后,敌人百般诱惑和恐吓都未能使他的信仰动摇。他在死神随时可能降临的敌牢里写下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訇的一声,跳入那暗沉沉的秽臭的污水潭里去,向他们入伙,与他们一块儿去抢,去掳,去刮,去榨,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