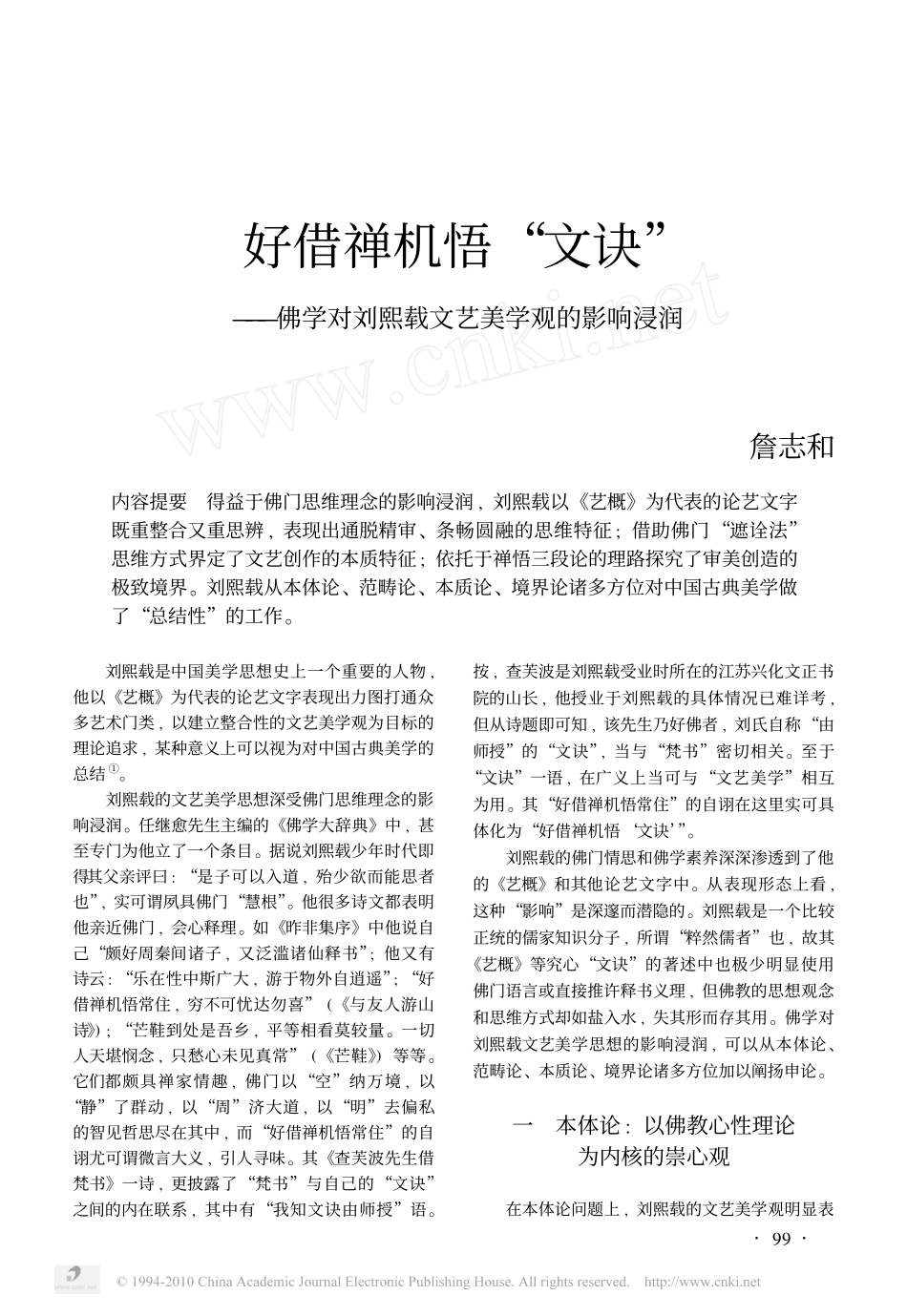好借禅机悟“文诀”———佛学对刘熙载文艺美学观的影响浸润詹志和内容提要得益于佛门思维理念的影响浸润,刘熙载以《艺概》为代表的论艺文字既重整合又重思辨,表现出通脱精审、条畅圆融的思维特征;借助佛门“遮诠法”思维方式界定了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依托于禅悟三段论的理路探究了审美创造的极致境界。刘熙载从本体论、范畴论、本质论、境界论诸多方位对中国古典美学做了“总结性”的工作。刘熙载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以《艺概》为代表的论艺文字表现出力图打通众多艺术门类,以建立整合性的文艺美学观为目标的理论追求,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①。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深受佛门思维理念的影响浸润。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佛学大辞典》中,甚至专门为他立了一个条目。据说刘熙载少年时代即得其父亲评曰:“是子可以入道,殆少欲而能思者也”,实可谓夙具佛门“慧根”。他很多诗文都表明他亲近佛门,会心释理。如《昨非集序》中他说自己“颇好周秦间诸子,又泛滥诸仙释书”;他又有诗云:“乐在性中斯广大,游于物外自逍遥”;“好借禅机悟常住,穷不可忧达勿喜”(《与友人游山诗》);“芒鞋到处是吾乡,平等相看莫较量。一切人天堪悯念,只愁心未见真常”(《芒鞋》)等等。它们都颇具禅家情趣,佛门以“空”纳万境,以“静”了群动,以“周”济大道,以“明”去偏私的智见哲思尽在其中,而“好借禅机悟常住”的自诩尤可谓微言大义,引人寻味。其《查芙波先生借梵书》一诗,更披露了“梵书”与自己的“文诀”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有“我知文诀由师授”语。按,查芙波是刘熙载受业时所在的江苏兴化文正书院的山长,他授业于刘熙载的具体情况已难详考,但从诗题即可知,该先生乃好佛者,刘氏自称“由师授”的“文诀”,当与“梵书”密切相关。至于“文诀”一语,在广义上当可与“文艺美学”相互为用。其“好借禅机悟常住”的自诩在这里实可具体化为“好借禅机悟‘文诀’”。刘熙载的佛门情思和佛学素养深深渗透到了他的《艺概》和其他论艺文字中。从表现形态上看,这种“影响”是深邃而潜隐的。刘熙载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谓“粹然儒者”也,故其《艺概》等究心“文诀”的著述中也极少明显使用佛门语言或直接推许释书义理,但佛教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却如盐入水,失其形而存其用。佛学对刘熙载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浸润,可以从本体论、范畴论、本质论、境界论诸多方位加以阐扬申论。一本体论:以佛教心性理论为内核的崇心观在本体论问题上,刘熙载的文艺美学观明显表·99·现出“崇心”的倾向,是以佛教心性理论为内核的。当然,由于“审美之源不属于本质主义一元论的范畴,而呈现出‘灵/肉’二维性”②,故而在作品生成论的意义上,刘熙载也讲“心”与“物”的缘会相生,但“心”“物”二者何者起主导作用呢?他更强调的是“心”,认为实现主客观完美统一的关键在主观方面。其《艺概·赋概》中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则物色只成闲事”,所以“赋必有关着自己痛痒处”。这里虽然肯定了“赋”的生成,也即艺术品的生成、“美”的生成,须有外在的“物色”与自家的“生意”相摩相荡,但是又强调了“物色”必须投合“自家生意”、“关着自己痛痒”,否则“只成闲事”。这显然是强调了“心”的主导作用和本体意义。特别是考虑到在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类中,“赋”历来被认为是以“铺陈实事”也即以“物色”见长,而刘熙载却强调它其实也是由“自家生意”牵率,那么刘氏文艺美学本体论的崇心倾向就更容易见出了。刘氏这种本体观追根溯源是由佛教心性理论和汲取佛教心性理论而在儒门别立新宗的陆王心学发脉而来。这个“学统”关系,《清史稿·儒林传》将其与倭仁并提时作过辨析:“(熙载)咸丰三年命值上书房,与大学士倭仁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倭仁宗程、朱,熙载则兼取陆、王。”另有论者认为:“从宋明的理学发展的线索看,由讲理而讲心性,由讲心性而讲情,由讲情而讲到欲,刘熙载承接了这个余波。”③此说在命理心性之学的发展走势这个大背景下为刘熙载的“学统”作了寻根定位,也指涉了陆王心学。而陆王学派之“崇心”,众所周知,实乃受熏于佛门。印度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