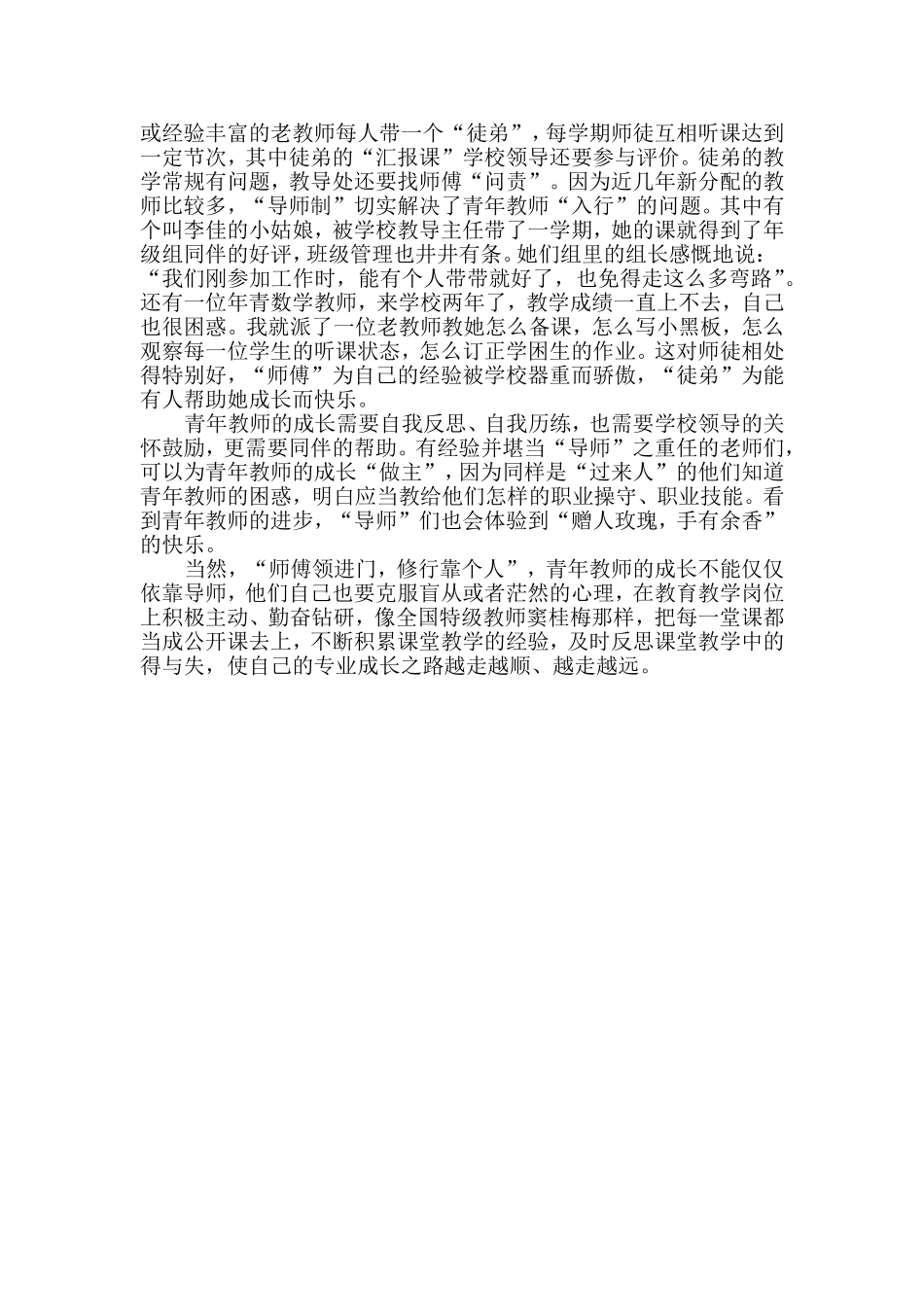我的成长谁“做主”——试论小学建立“导师制”的必要性银川市金凤区第一回民小学魏茜2008年,笔者有幸赴上海市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挂职培训两个月,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听课和参加教研活动。这所学校在区域内很有名,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业内人士,但是这些参观者却没有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因为教学楼里每一间教室都是开放的,每位老师的教学都是规范而常态的。我所听的每一节随堂课都不是教务处特意安排的,他们只是为我提供了一张课程表。但是每走进一间教室,观察这些年仅二十几岁的年青教师的课堂,都会收获一份惊喜,一份羡慕。他们基本功扎实,教学目标明确,组织调控课堂的能力成熟老练,教学任务完成得很好,完全不像“新手”。我深感叹服并心存疑问,便向徐校长请教她在教师培养方面的“高招”。徐校长告诉我,她的学校之所以有这样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除了严把“入口关”(仅在上海师范大学招聘教师),还延续了这所学校的老传统“师带徒”制度:就是给每一位新入行的教师指认一位“师傅”,手把手地教他们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教他们教育教学的策略与技巧,并规定新教师“一年入行,三年胜任,五年成长为骨干”。对于有培养前途的教师,学校还出资返聘退休的优秀教师为他们“磨课”,特殊“施教”。徐校长的一番话让我幡然警醒:工人生产需要技术,工厂新招聘的员工都要“跟师傅”,由师傅教他们学习生产和操作技术,这样才能保证安全生产,保证制造出优质合格的产品。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教师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有很高的专业技能要求。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把每一位孩子都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新教师当然也更应当“跟师傅”了。笔者已有20年教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曾走了5所学校,似乎没有哪所学校像模像样地推行过“导师制”。只有一所学校举行过“拜师结对”仪式,我还给“师傅”献上了学校购买的红花,可是到底该怎样向师傅学习,师傅应当怎样“施教”,却没有了下文。以至于时隔几年,连当时学校为自己指派的师傅是哪位都记不清了。我的课堂教学,全凭自己摸索,主任偶尔来听一次课,也没起到多大作用。特别是担任新课程实验教师的那几年,我还不会制作和使用课件,周围也没有几个会的人。而教育局教研员却时常来校调研,并经常光顾我的课堂,指出这里那里不符合课改理念,常常弄得我无所适从,痛苦至极。那段时间,走的弯路很多,付出的努力也很多。假如有一位“导师”帮助自己,该是多么好啊!近两年,我在自己的学校推行了“导师制”,要求每位骨干教师或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每人带一个“徒弟”,每学期师徒互相听课达到一定节次,其中徒弟的“汇报课”学校领导还要参与评价。徒弟的教学常规有问题,教导处还要找师傅“问责”。因为近几年新分配的教师比较多,“导师制”切实解决了青年教师“入行”的问题。其中有个叫李佳的小姑娘,被学校教导主任带了一学期,她的课就得到了年级组同伴的好评,班级管理也井井有条。她们组里的组长感慨地说:“我们刚参加工作时,能有个人带带就好了,也免得走这么多弯路”。还有一位年青数学教师,来学校两年了,教学成绩一直上不去,自己也很困惑。我就派了一位老教师教她怎么备课,怎么写小黑板,怎么观察每一位学生的听课状态,怎么订正学困生的作业。这对师徒相处得特别好,“师傅”为自己的经验被学校器重而骄傲,“徒弟”为能有人帮助她成长而快乐。青年教师的成长需要自我反思、自我历练,也需要学校领导的关怀鼓励,更需要同伴的帮助。有经验并堪当“导师”之重任的老师们,可以为青年教师的成长“做主”,因为同样是“过来人”的他们知道青年教师的困惑,明白应当教给他们怎样的职业操守、职业技能。看到青年教师的进步,“导师”们也会体验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乐。当然,“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青年教师的成长不能仅仅依靠导师,他们自己也要克服盲从或者茫然的心理,在教育教学岗位上积极主动、勤奋钻研,像全国特级教师窦桂梅那样,把每一堂课都当成公开课去上,不断积累课堂教学的经验,及时反思课堂教学中的得与失,使自己的专业成长之路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