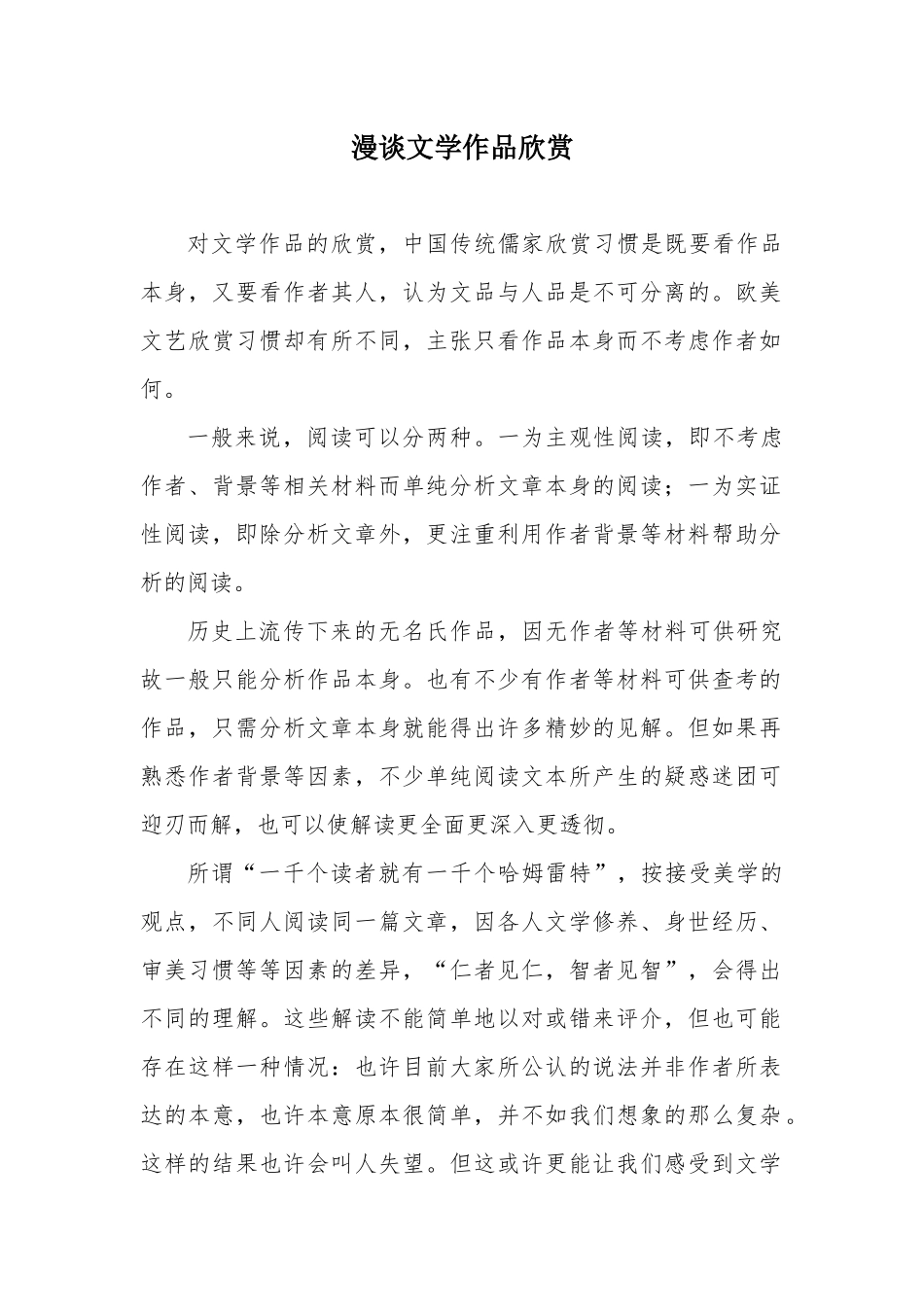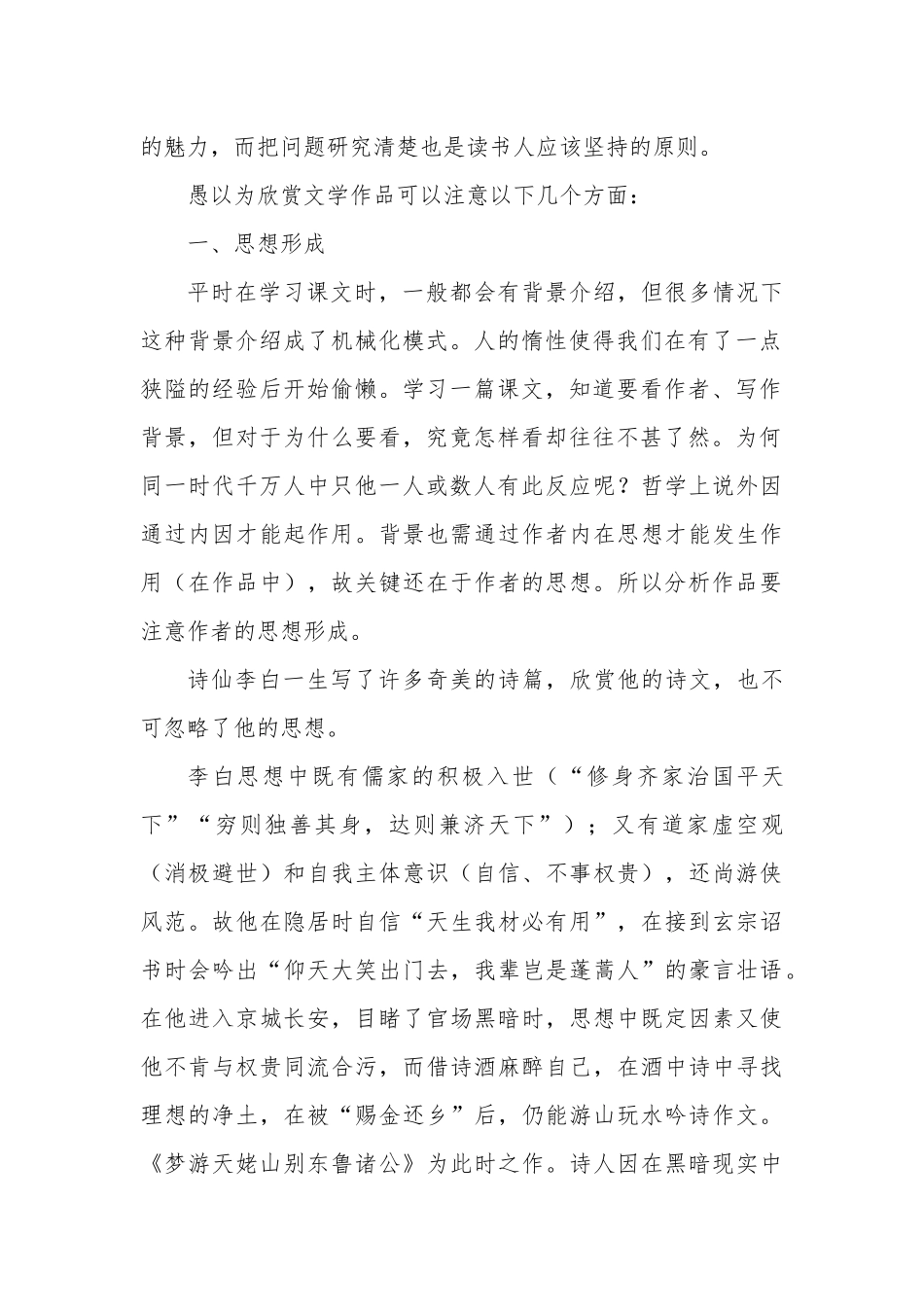漫谈文学作品欣赏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国传统儒家欣赏习惯是既要看作品本身,又要看作者其人,认为文品与人品是不可分离的。欧美文艺欣赏习惯却有所不同,主张只看作品本身而不考虑作者如何。一般来说,阅读可以分两种。一为主观性阅读,即不考虑作者、背景等相关材料而单纯分析文章本身的阅读;一为实证性阅读,即除分析文章外,更注重利用作者背景等材料帮助分析的阅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无名氏作品,因无作者等材料可供研究故一般只能分析作品本身。也有不少有作者等材料可供查考的作品,只需分析文章本身就能得出许多精妙的见解。但如果再熟悉作者背景等因素,不少单纯阅读文本所产生的疑惑迷团可迎刃而解,也可以使解读更全面更深入更透彻。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不同人阅读同一篇文章,因各人文学修养、身世经历、审美习惯等等因素的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得出不同的理解。这些解读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来评介,但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也许目前大家所公认的说法并非作者所表达的本意,也许本意原本很简单,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这样的结果也许会叫人失望。但这或许更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而把问题研究清楚也是读书人应该坚持的原则。愚以为欣赏文学作品可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思想形成平时在学习课文时,一般都会有背景介绍,但很多情况下这种背景介绍成了机械化模式。人的惰性使得我们在有了一点狭隘的经验后开始偷懒。学习一篇课文,知道要看作者、写作背景,但对于为什么要看,究竟怎样看却往往不甚了然。为何同一时代千万人中只他一人或数人有此反应呢?哲学上说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背景也需通过作者内在思想才能发生作用(在作品中),故关键还在于作者的思想。所以分析作品要注意作者的思想形成。诗仙李白一生写了许多奇美的诗篇,欣赏他的诗文,也不可忽略了他的思想。李白思想中既有儒家的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又有道家虚空观(消极避世)和自我主体意识(自信、不事权贵),还尚游侠风范。故他在隐居时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在接到玄宗诏书时会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言壮语。在他进入京城长安,目睹了官场黑暗时,思想中既定因素又使他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而借诗酒麻醉自己,在酒中诗中寻找理想的净土,在被“赐金还乡”后,仍能游山玩水吟诗作文。《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为此时之作。诗人因在黑暗现实中无法实现理想,而借助梦境仙境抒发对理想的追求,而文中“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则或多或少流露了遭挫后的消极情绪,然消极不等于消沉,作者的道侠思想在此时又使他吟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等傲视权贵的不羁之语。故其诗能显神奇瑰丽洒脱豪放。与李白思想相类,苏轼思想中主要有三重因素:儒释道。儒家的积极入世使他充满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佛家道家的虚空观逍遥观又使他在仕途失意时有消极情绪却又能极快从委顿中摆脱出来,表现得豁达洒脱与达观。苏轼在贬官黄州游赤壁时写了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既借周郎年少英雄抒发自己年老功业无成的慨叹,又有“人生如梦”的消极之语,但思想中逍遥达观因素又使他能迅速从悲观中摆脱出来,潇洒地倒一杯酒祭洒江月,表现得极其洒脱。李白的道侠思想,苏轼的释道思想,使得他们两人性格豪放洒脱,创作的作品也充溢着豪放与浪漫的味道。杜甫思想中缺少这些东西,所以只能做一位现实主义大师;白居易也做不到如此洒脱豪放,贬官九江时听到琵琶声竟至痛哭流涕。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后叶,发展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对我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虚无荒诞的,孤独个体在存在中会感到恐怖、厌烦、忧郁和绝望,人被抛到世界上,无能为力,必然走向死亡,归于虚无。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灭亡的最终归途,但又并不主张放弃努力,强调应自己把握自己,对自己人生负责。鲁迅在1902—1909年留学日本期间深受此思潮影响。鲁迅曾坦言自己思想太黑暗,而这黑暗思想是他长期以来孤独、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