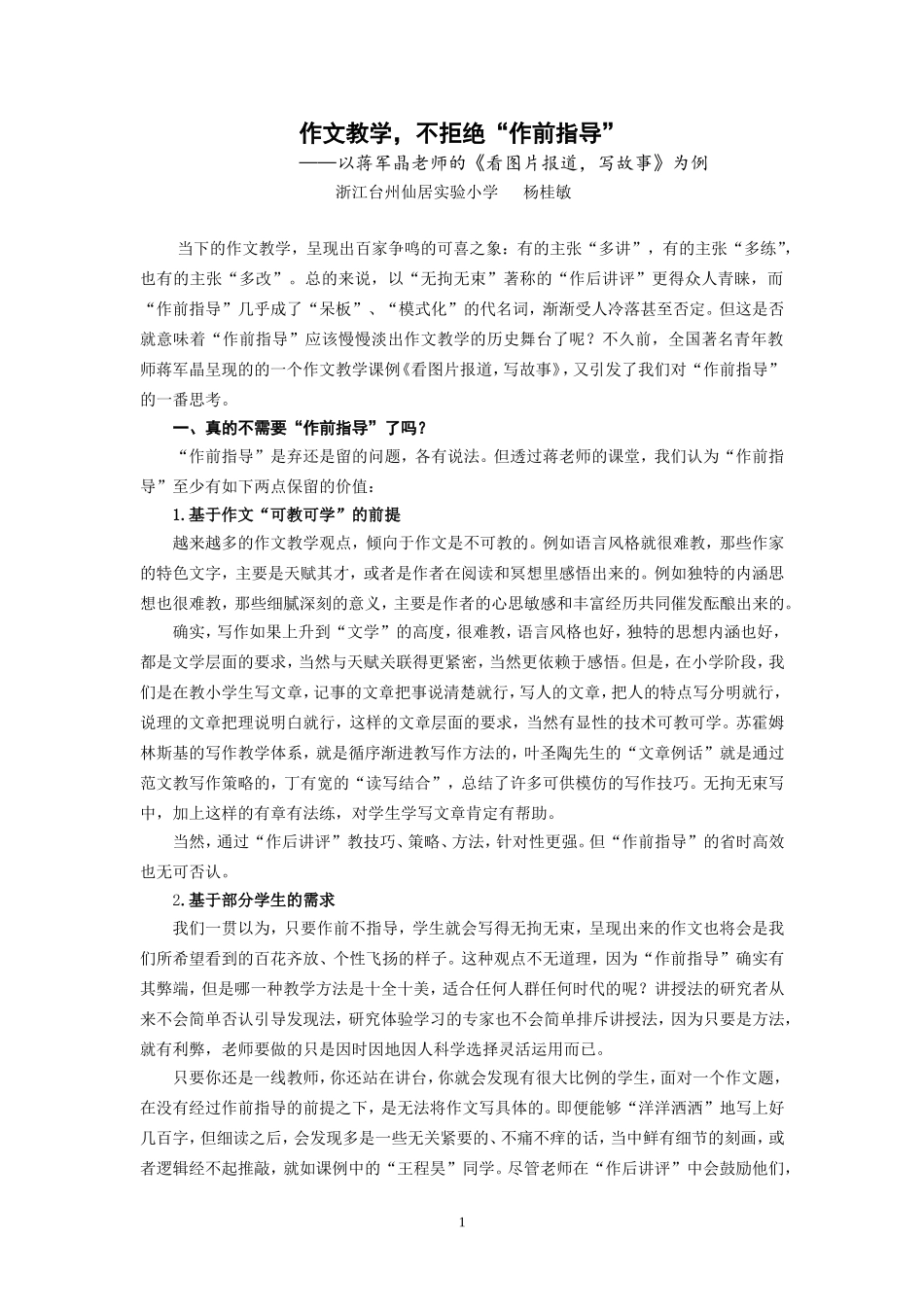作文教学,不拒绝“作前指导”——以蒋军晶老师的《看图片报道,写故事》为例浙江台州仙居实验小学杨桂敏当下的作文教学,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可喜之象:有的主张“多讲”,有的主张“多练”,也有的主张“多改”。总的来说,以“无拘无束”著称的“作后讲评”更得众人青睐,而“作前指导”几乎成了“呆板”、“模式化”的代名词,渐渐受人冷落甚至否定。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作前指导”应该慢慢淡出作文教学的历史舞台了呢?不久前,全国著名青年教师蒋军晶呈现的的一个作文教学课例《看图片报道,写故事》,又引发了我们对“作前指导”的一番思考。一、真的不需要“作前指导”了吗?“作前指导”是弃还是留的问题,各有说法。但透过蒋老师的课堂,我们认为“作前指导”至少有如下两点保留的价值:1.基于作文“可教可学”的前提越来越多的作文教学观点,倾向于作文是不可教的。例如语言风格就很难教,那些作家的特色文字,主要是天赋其才,或者是作者在阅读和冥想里感悟出来的。例如独特的内涵思想也很难教,那些细腻深刻的意义,主要是作者的心思敏感和丰富经历共同催发酝酿出来的。确实,写作如果上升到“文学”的高度,很难教,语言风格也好,独特的思想内涵也好,都是文学层面的要求,当然与天赋关联得更紧密,当然更依赖于感悟。但是,在小学阶段,我们是在教小学生写文章,记事的文章把事说清楚就行,写人的文章,把人的特点写分明就行,说理的文章把理说明白就行,这样的文章层面的要求,当然有显性的技术可教可学。苏霍姆林斯基的写作教学体系,就是循序渐进教写作方法的,叶圣陶先生的“文章例话”就是通过范文教写作策略的,丁有宽的“读写结合”,总结了许多可供模仿的写作技巧。无拘无束写中,加上这样的有章有法练,对学生学写文章肯定有帮助。当然,通过“作后讲评”教技巧、策略、方法,针对性更强。但“作前指导”的省时高效也无可否认。2.基于部分学生的需求我们一贯以为,只要作前不指导,学生就会写得无拘无束,呈现出来的作文也将会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百花齐放、个性飞扬的样子。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因为“作前指导”确实有其弊端,但是哪一种教学方法是十全十美,适合任何人群任何时代的呢?讲授法的研究者从来不会简单否认引导发现法,研究体验学习的专家也不会简单排斥讲授法,因为只要是方法,就有利弊,老师要做的只是因时因地因人科学选择灵活运用而已。只要你还是一线教师,你还站在讲台,你就会发现有很大比例的学生,面对一个作文题,在没有经过作前指导的前提之下,是无法将作文写具体的。即便能够“洋洋洒洒”地写上好几百字,但细读之后,会发现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痛不痒的话,当中鲜有细节的刻画,或者逻辑经不起推敲,就如课例中的“王程昊”同学。尽管老师在“作后讲评”中会鼓励他们,1努力挖掘他们习作中的“亮点”,但他们在这样的尝试和横向比较中,已经受挫,信心下降。蒋老师这堂“作前指导”课,其用意正是在50人左右的大班情境中,切实帮助像“王程昊”那样的同学,让这部分同学在写之前了解写作技巧,明了写作方向,努力缩小与其他同学的差距,提升他们的信心,应当说,这样的“作前指导”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样的“作前指导”,再加上适量的时间上允许的“个别辅导”,一定能事半功倍。二、我们需要怎样的“作前指导”?那么,怎样的“作前指导”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呢?以上课例也给了我们这样两点启示:1.基于学情的“作前指导”这一“作前指导”并非隔空架构,而是基于学生学情的。对于学情的把握,大部分老师依靠的是自己多年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判断,但是蒋老师经常在预测的同时去“实地调研”。上课之前,蒋老师让一些学生在没有经过任何指导的前提下进行习作,写完之后比较,比较之后就发现了两类写作方式:一类用了“动物直接说话”的方式,即类似于童话的写法;一类加上了“好像在说”,接近动物纪实故事的写法。显然,作为通讯报道这样的特殊文体,用上“王程昊”同学的那种童话式写法并不适合。但经过进一步分析获知,在没有经过任何“作前指导”的前提下,十有八九的写作上有困难的学生都很自然地采用这样的写法。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