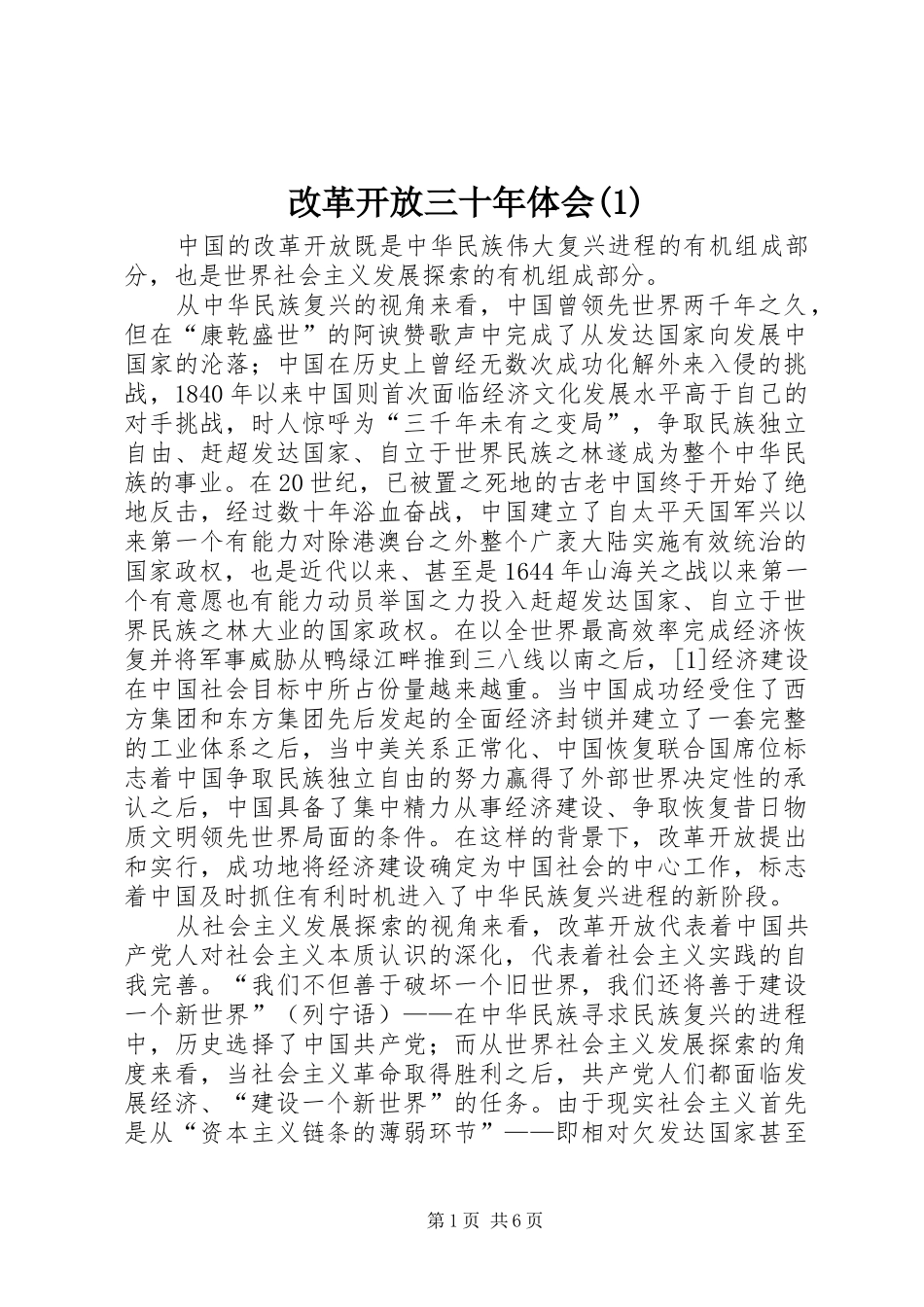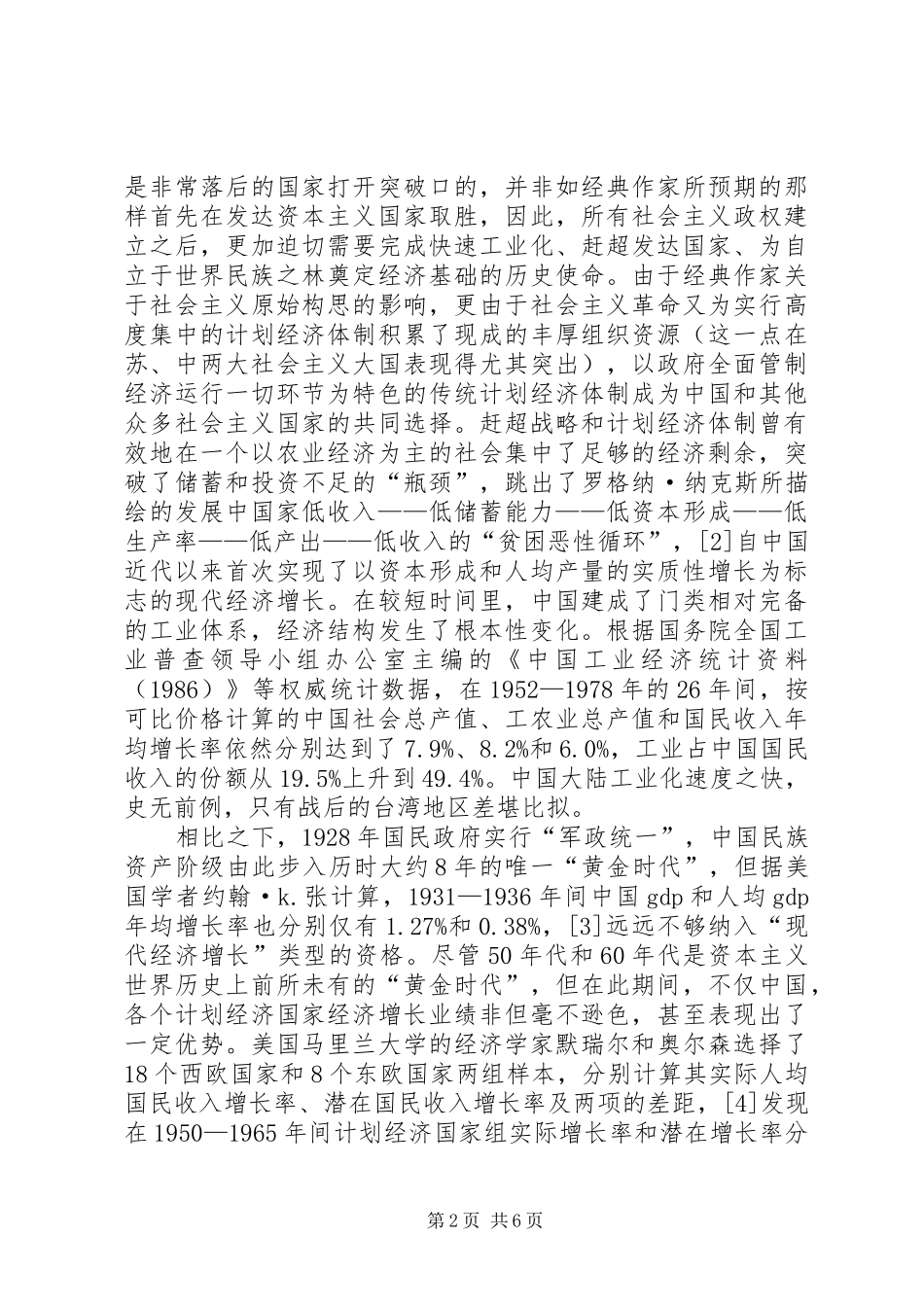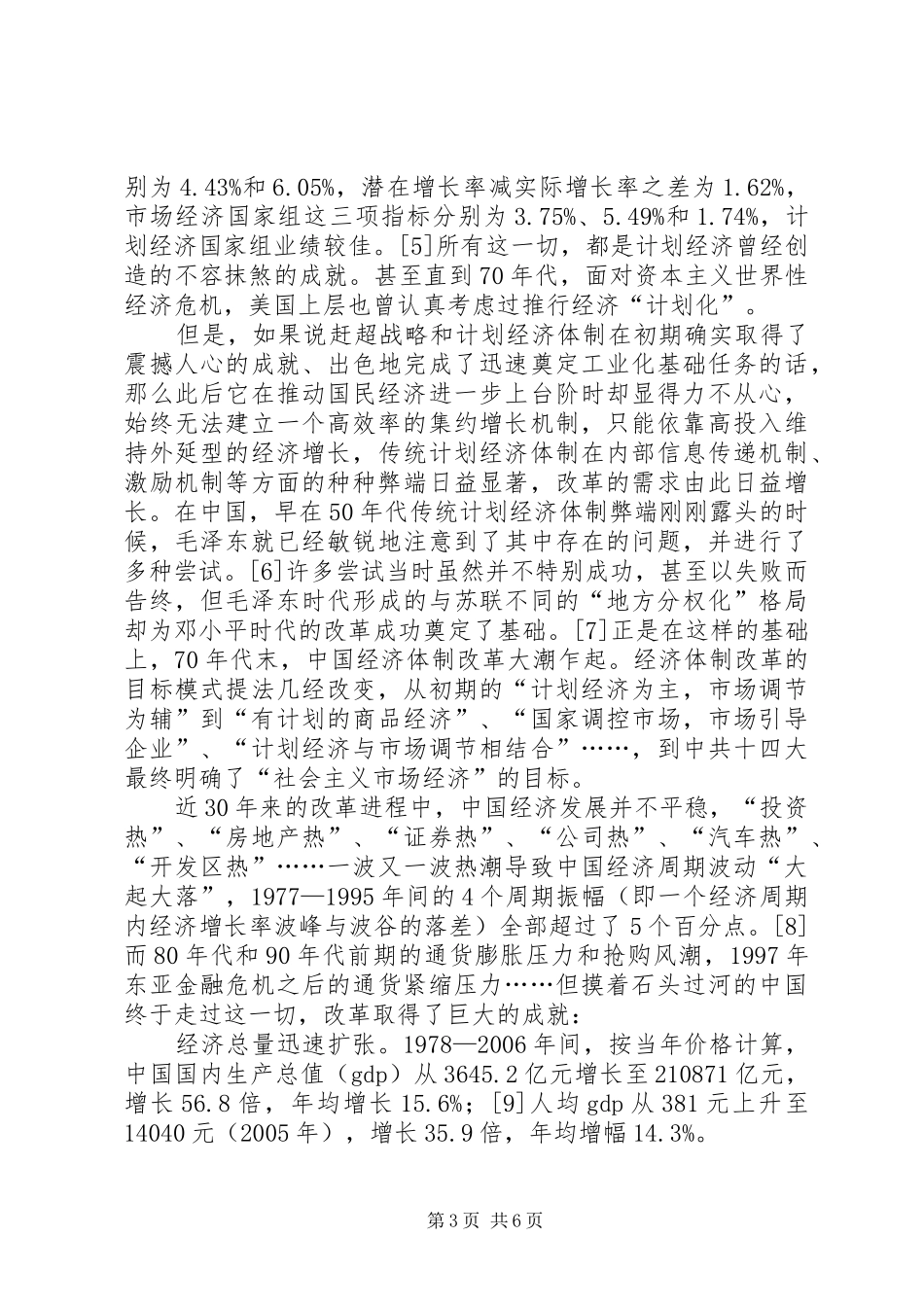改革开放三十年体会(1)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看,中国曾领先世界两千年之久,但在“康乾盛世”的阿谀赞歌声中完成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沦落;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无数次成功化解外来入侵的挑战,1840年以来中国则首次面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自己的对手挑战,时人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赶超发达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在20世纪,已被置之死地的古老中国终于开始了绝地反击,经过数十年浴血奋战,中国建立了自太平天国军兴以来第一个有能力对除港澳台之外整个广袤大陆实施有效统治的国家政权,也是近代以来、甚至是1644年山海关之战以来第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动员举国之力投入赶超发达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业的国家政权。在以全世界最高效率完成经济恢复并将军事威胁从鸭绿江畔推到三八线以南之后,[1]经济建设在中国社会目标中所占份量越来越重。当中国成功经受住了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先后发起的全面经济封锁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当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标志着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努力赢得了外部世界决定性的承认之后,中国具备了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争取恢复昔日物质文明领先世界局面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提出和实行,成功地将经济建设确定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工作,标志着中国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进入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新阶段。从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代表着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完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列宁语)——在中华民族寻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角度来看,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共产党人们都面临发展经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任务。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首先是从“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即相对欠发达国家甚至第1页共6页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打开突破口的,并非如经典作家所预期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更加迫切需要完成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经济基础的历史使命。由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原始构思的影响,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又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累了现成的丰厚组织资源(这一点在苏、中两大社会主义大国表现得尤其突出),以政府全面管制经济运行一切环节为特色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和其他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选择。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曾有效地在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集中了足够的经济剩余,突破了储蓄和投资不足的“瓶颈”,跳出了罗格纳·纳克斯所描绘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贫困恶性循环”,[2]自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实现了以资本形成和人均产量的实质性增长为标志的现代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里,中国建成了门类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86)》等权威统计数据,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中国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依然分别达到了7.9%、8.2%和6.0%,工业占中国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5%上升到49.4%。中国大陆工业化速度之快,史无前例,只有战后的台湾地区差堪比拟。相比之下,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军政统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此步入历时大约8年的唯一“黄金时代”,但据美国学者约翰·k.张计算,1931—1936年间中国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也分别仅有1.27%和0.38%,[3]远远不够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类型的资格。尽管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但在此期间,不仅中国,各个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增长业绩非但毫不逊色,甚至表现出了一定优势。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默瑞尔和奥尔森选择了18个西欧国家和8个东欧国家两组样本,分别计算其实际人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