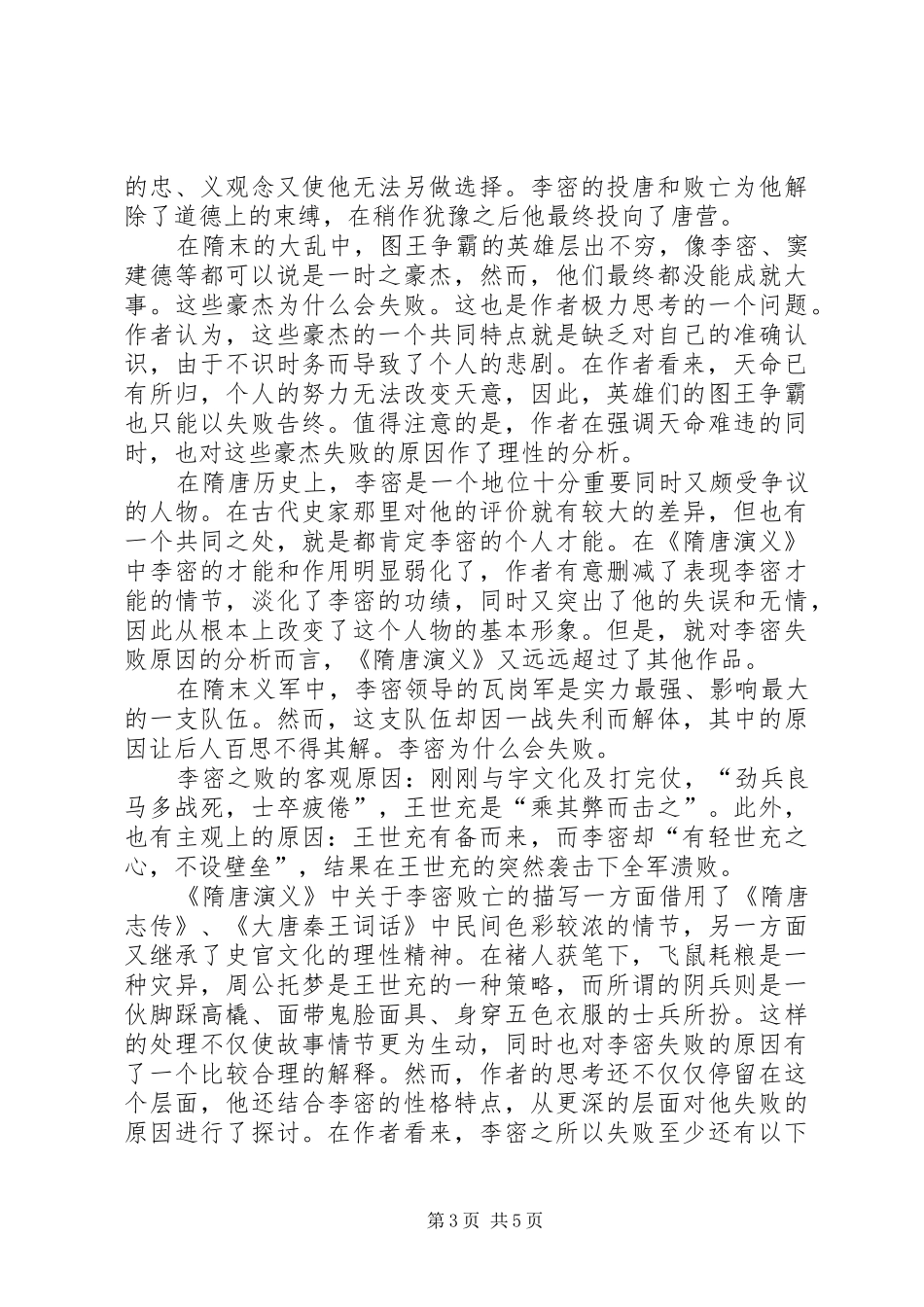读《隋唐演义》有感《隋唐演义》是一部特点鲜明、艺术成就突出的历史演义小说,其带有更为明显的英雄传奇色彩。作者在揭示这些草莽英雄命运时突出了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既描述了他们可歌可泣的传奇式经历,又揭示了他们的悲剧,体现了较新的英雄史观。古代史家在谈到历史发展、变化的时候常常会使用“时”、“势”之类的概念。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就以“势”来论说封建制的产生,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苏东坡则认为:“圣人不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王夫之说:“一动而不可止者,势也。”在他看来,势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动向,因此,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就要“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在这些史家、政治家看来,“时”和“势”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不能制造它,但却可以认识它、利用它,“圣人”的高明之处就是“能不失时”。本传中的李圆通、来护儿、张定和、麦铁杖等都出身贫贱,由于“遇其时”而在隋朝统一的过程中屡建战功,成就了一番事业。“时势造英雄”,这可以说是古代史家比较普遍的一种历史观,同时也是历史小说着力表现的一个主题。隋末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隋唐演义》中所写的李密、窦建德、秦琼、程咬金、徐懋功、单雄信等都可谓是一时之俊杰,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是隋末大动乱的“时势”将他们推上了历史舞台。在作者看来,“人生天地间,有盛必有衰,有聚必有散。处承平之世,人人思安享守业,共乐升平。若处昏淫之世,凡有一材一艺之士,个个思量寻一番事业,讨一番烦恼;或聚在一处,或散于四方,谁肯株守林泉,老死牖下。”隋末正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昏淫之世”,在这样的乱世中,豪杰之士都想有一番作为。单雄信就明确表示:“天生此第1页共5页六尺之躯,自然要轰轰烈烈做他一场,成与不成命也。”徐懋功也“有意结纳英豪,寻访真主”,试图有所作为。隋炀帝的暴政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英雄们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事业成就与否却取决于自己能否认识时势、把握机遇。隋唐英雄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秦琼,在《隋史遗文》和《隋唐演义》中他都是最重要的角色,两个作者都用了大量笔墨细致地描绘了他从市井豪侠到开国功臣的人生历程。秦琼的人生道路给读者留下了三点启示:首先,时势造英雄。小说中的秦琼本来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豪侠,他出身于世代将门之家,朝代更替的巨变使他沦落于下层社会,但他的人生理想仍是“为国家提一枝兵马,斩将搴旗,开疆展土”在小说中他是一个忠、孝、义俱全的英雄,然而,“忠”和“义”的矛盾常常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而与生俱来的侠义性格更注定了他人生道路的坎坷。尽管他一再克制、忍让,但楂树岗救李渊、长安城打死宇文公子等义举却使他与当权者发生了直接冲突。因此,尽管他为大隋屡立战功,最终还是被逼上瓦岗,走上了造**的道路。正是奸臣当道的现实使他为国效力的梦想一再化为泡影,但也正是因此才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并成全了他的英雄事业。其次,“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与那些图王争霸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秦琼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有一大段徐懋功与秦琼的对话,徐懋功首先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判断:“不出四五年,天下定然大乱。”然后对当时的一些豪杰一一作了评判,他认为自己与秦琼都是“一时之杰”,“俱堪为兴朝佐命,永保功名”,但前提是必须“择真主而归之,无为祸首”。在“天命”已有所归的形势下,不为祸首,择主而事,这可以说是秦琼之类的英雄事业成就的关键。第三,要顺应“时势”。秦琼一生最为关键的决断无疑是投唐,但这个决断的作出却是十分艰难的。多年征战的经历使秦琼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知道李世民才是“真命之主”,因此在李世民危难之时就曾出手相救,但传统第2页共5页的忠、义观念又使他无法另做选择。李密的投唐和败亡为他解除了道德上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