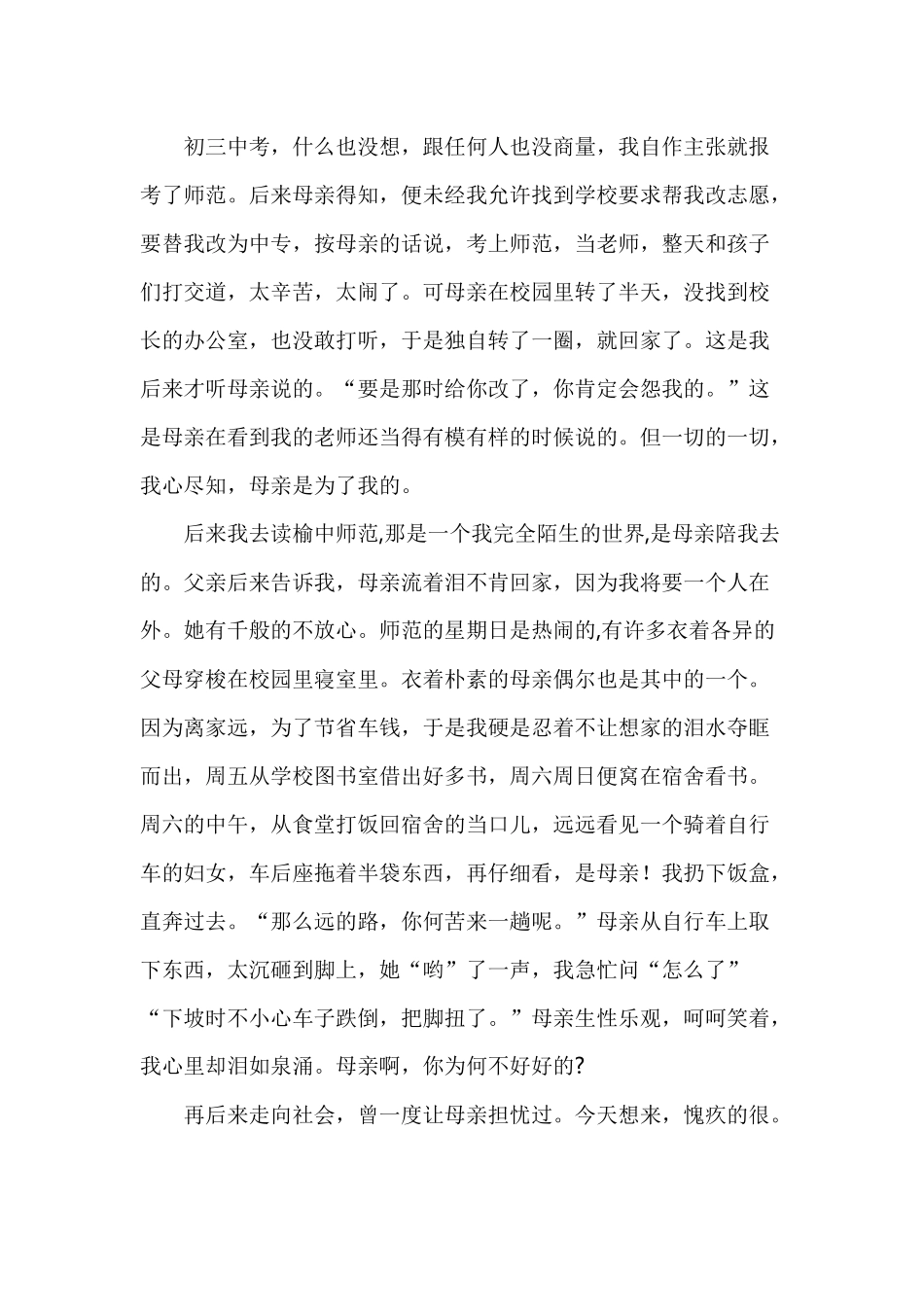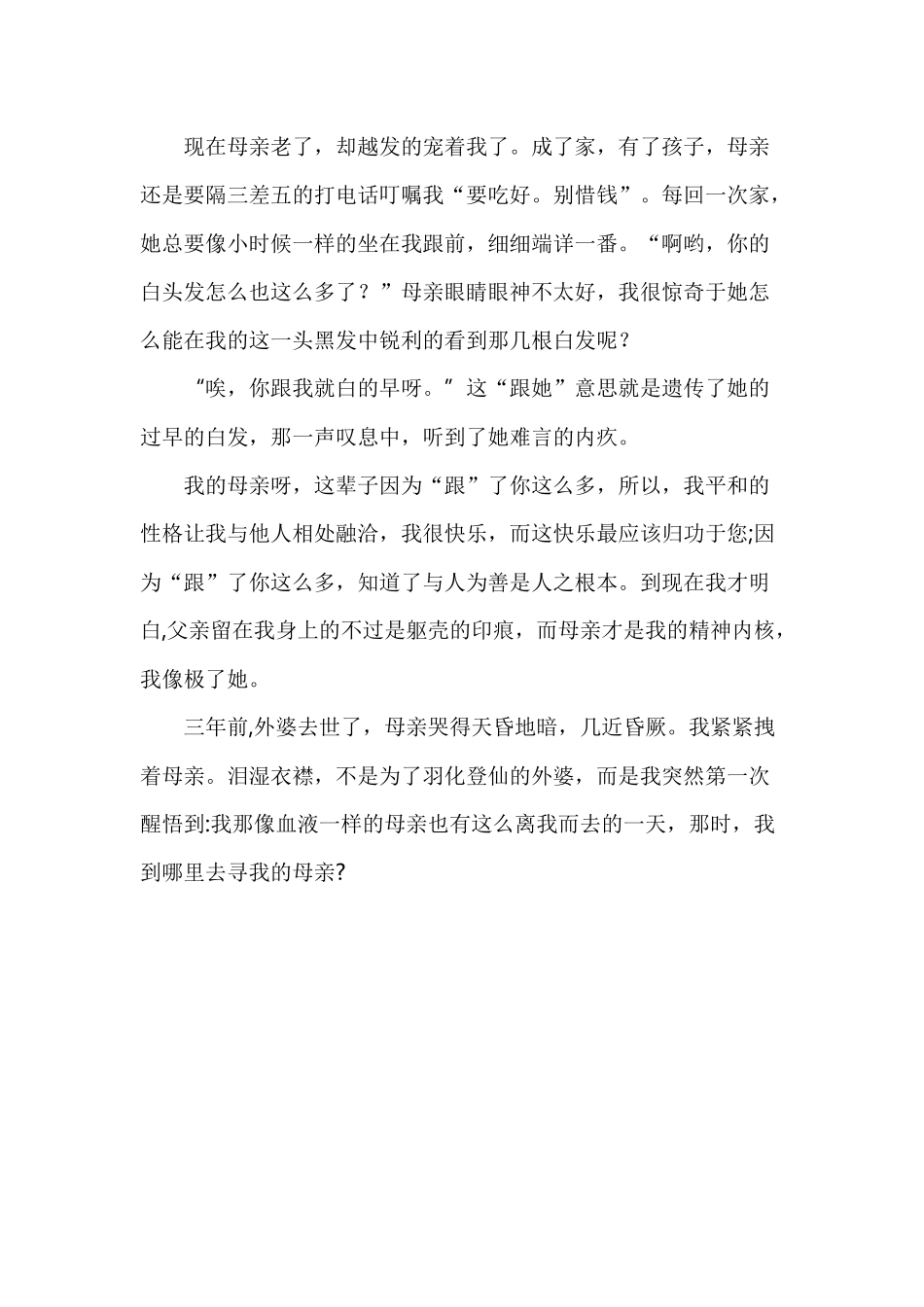母亲从来未曾在文章里将妈妈称呼为母亲,因为总觉得“母亲”这个称呼太庄重,只适合于在名家的笔下,平凡如我的母亲,怎当得起?这一次,例外!小时候,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很少有时间照顾我和弟弟,所以记忆中我从未有过被父亲打抑或斥责的事情,一直到今天。记忆里打我骂我训斥我的都是母亲。有一次我不知做错了什么事。母亲罚我站在大门口。有许多路过的小伙伴看到狼狈的我,再也不离开了,围在旁边嘲笑我。我表面上还在嬉皮笑脸,但当时的无地自容到现在还记得清楚。成年后我有一次和母亲开玩笑说:“你不知道你睁着眼睛,耸着眉毛的样子有多么吓人。”母亲说:“对你的好都不记得了?”那一刻,母亲似有些黯然。而我亦有些后悔,母亲年老,有些话是不能轻易去说的。母亲性格要强。嗓门大,脾气也大。凡事总要做到比别人好一些。于是,我很少犯错误,是出了名的乖孩子。记忆中,母亲便从不骂我了,是在我上到小学六年级时。那时,我的学习已经很能为母亲争光。全乡的统考,我考了第一,从此我也成了母亲心中的骄傲,成了她经意或不经意间和乡邻谈话的中心。后来,进入初中,连续三年,第一名的宝座从未旁落他家。从母亲和邻家婶婶们的聊天中,知晓因为我的争气,她觉得干起活儿来竟然没觉得累。那时,要让母亲高兴,要让母亲满脸笑容的和乡邻四舍以聊我的话题为骄傲,就是我努力地理由。初三中考,什么也没想,跟任何人也没商量,我自作主张就报考了师范。后来母亲得知,便未经我允许找到学校要求帮我改志愿,要替我改为中专,按母亲的话说,考上师范,当老师,整天和孩子们打交道,太辛苦,太闹了。可母亲在校园里转了半天,没找到校长的办公室,也没敢打听,于是独自转了一圈,就回家了。这是我后来才听母亲说的。“要是那时给你改了,你肯定会怨我的。”这是母亲在看到我的老师还当得有模有样的时候说的。但一切的一切,我心尽知,母亲是为了我的。后来我去读榆中师范,那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是母亲陪我去的。父亲后来告诉我,母亲流着泪不肯回家,因为我将要一个人在外。她有千般的不放心。师范的星期日是热闹的,有许多衣着各异的父母穿梭在校园里寝室里。衣着朴素的母亲偶尔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离家远,为了节省车钱,于是我硬是忍着不让想家的泪水夺眶而出,周五从学校图书室借出好多书,周六周日便窝在宿舍看书。周六的中午,从食堂打饭回宿舍的当口儿,远远看见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妇女,车后座拖着半袋东西,再仔细看,是母亲!我扔下饭盒,直奔过去。“那么远的路,你何苦来一趟呢。”母亲从自行车上取下东西,太沉砸到脚上,她“哟”了一声,我急忙问“怎么了”“下坡时不小心车子跌倒,把脚扭了。”母亲生性乐观,呵呵笑着,我心里却泪如泉涌。母亲啊,你为何不好好的?再后来走向社会,曾一度让母亲担忧过。今天想来,愧疚的很。现在母亲老了,却越发的宠着我了。成了家,有了孩子,母亲还是要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叮嘱我“要吃好。别惜钱”。每回一次家,她总要像小时候一样的坐在我跟前,细细端详一番。“啊哟,你的白头发怎么也这么多了?”母亲眼睛眼神不太好,我很惊奇于她怎么能在我的这一头黑发中锐利的看到那几根白发呢?“唉,你跟我就白的早呀。”这“跟她”意思就是遗传了她的过早的白发,那一声叹息中,听到了她难言的内疚。我的母亲呀,这辈子因为“跟”了你这么多,所以,我平和的性格让我与他人相处融洽,我很快乐,而这快乐最应该归功于您;因为“跟”了你这么多,知道了与人为善是人之根本。到现在我才明白,父亲留在我身上的不过是躯壳的印痕,而母亲才是我的精神内核,我像极了她。三年前,外婆去世了,母亲哭得天昏地暗,几近昏厥。我紧紧拽着母亲。泪湿衣襟,不是为了羽化登仙的外婆,而是我突然第一次醒悟到:我那像血液一样的母亲也有这么离我而去的一天,那时,我到哪里去寻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