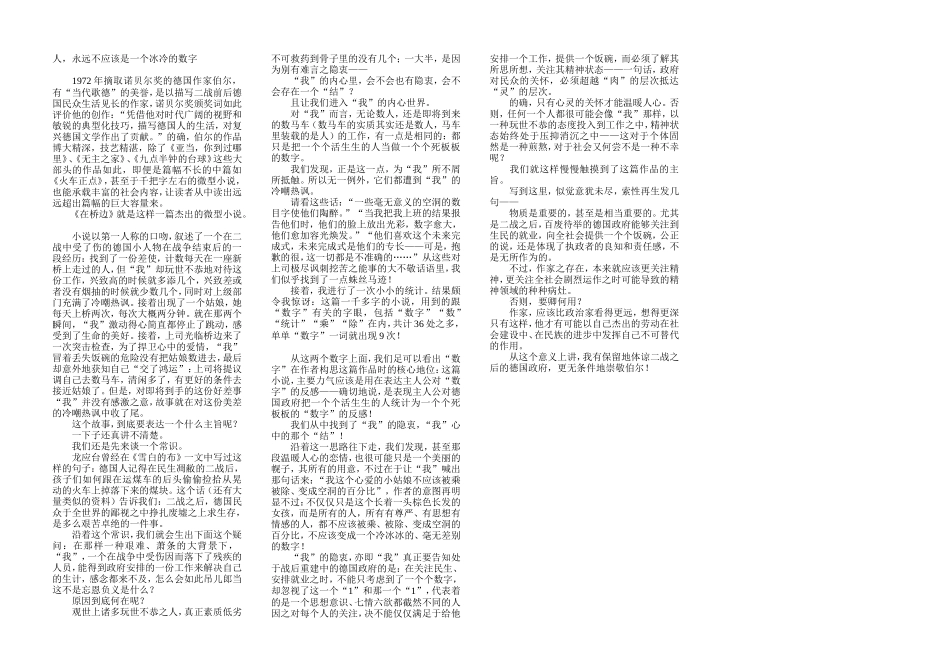人,永远不应该是一个冰冷的数字1972年摘取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伯尔,有“当代歌德”的美誉,是以描写二战前后德国民众生活见长的作家,诺贝尔奖颁奖词如此评价他的创作:“凭借他对时代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典型化技巧,描写德国人的生活,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的确,伯尔的作品博大精深,技艺精湛,除了《亚当,你到过哪里》、《无主之家》、《九点半钟的台球》这些大部头的作品如此,即便是篇幅不长的中篇如《火车正点》,甚至于千把字左右的微型小说,也能承载丰富的社会内容,让读者从中读出远远超出篇幅的巨大容量来。《在桥边》就是这样一篇杰出的微型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在二战中受了伤的德国小人物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经历:找到了一份差使,计数每天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但“我”却玩世不恭地对待这份工作,兴致高的时候就多添几个,兴致差或者没有烟抽的时候就少数几个,同时对上级部门充满了冷嘲热讽。接着出现了一个姑娘,她每天上桥两次,每次大概两分钟。就在那两个瞬间,“我”激动得心简直都停止了跳动,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接着,上司光临桥边来了一次突击检查,为了捍卫心中的爱情,“我”冒着丢失饭碗的危险没有把姑娘数进去,最后却意外地获知自己“交了鸿运”:上司将提议调自己去数马车,清闲多了,有更好的条件去接近姑娘了。但是,对即将到手的这份好差事“我”并没有感激之意,故事就在对这份美差的冷嘲热讽中收了尾。这个故事,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主旨呢?一下子还真讲不清楚。我们还是先来谈一个常识。龙应台曾经在《雪白的布》一文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德国人记得在民生凋敝的二战后,孩子们如何跟在运煤车的后头偷偷捡拾从晃动的火车上掉落下来的煤块。这个话(还有大量类似的资料)告诉我们:二战之后,德国民众于全世界的鄙视之中挣扎废墟之上求生存,是多么艰苦卓绝的一件事。沿着这个常识,我们就会生出下面这个疑问:在那样一种艰难、萧条的大背景下,“我”,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因而落下了残疾的人员,能得到政府安排的一份工作来解决自己的生计,感念都来不及,怎么会如此吊儿郎当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原因到底何在呢?观世上诸多玩世不恭之人,真正素质低劣不可救药到骨子里的没有几个;一大半,是因为别有难言之隐衷——“我”的内心里,会不会也有隐衷,会不会存在一个“结”?且让我们进入“我”的内心世界。对“我”而言,无论数人,还是即将到来的数马车(数马车的实质其实还是数人,马车里装载的是人)的工作,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只是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当做一个个死板板的数字。我们发现,正是这一点,为“我”所不屑所抵触。所以无一例外,它们都遭到“我”的冷嘲热讽。请看这些话:“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的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从这些对上司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大不敬话语里,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接着,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统计。结果颇令我惊讶:这篇一千多字的小说,用到的跟“数字”有关的字眼,包括“数字”“数”“统计”“乘”“除”在内,共计36处之多,单单“数字”一词就出现9次!从这两个数字上面,我们足可以看出“数字”在作者构思这篇作品时的核心地位:这篇小说,主要力气应该是用在表达主人公对“数字”的反感——确切地说,是表现主人公对德国政府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统计为一个个死板板的“数字”的反感!我们从中找到了“我”的隐衷,“我”心中的那个“结”!沿着这一思路往下走,我们发现,甚至那段温暖人心的恋情,也很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幌子,其所有的用意,不过在于让“我”喊出那句话来:“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作者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不仅仅只是这个长着一头棕色长发的女孩,而是所有的人,所有有尊严、有思想有情感的人,都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不应该变成一个冷冰冰的、毫无差别的数字!“我”的隐衷,亦即“我”真正要告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