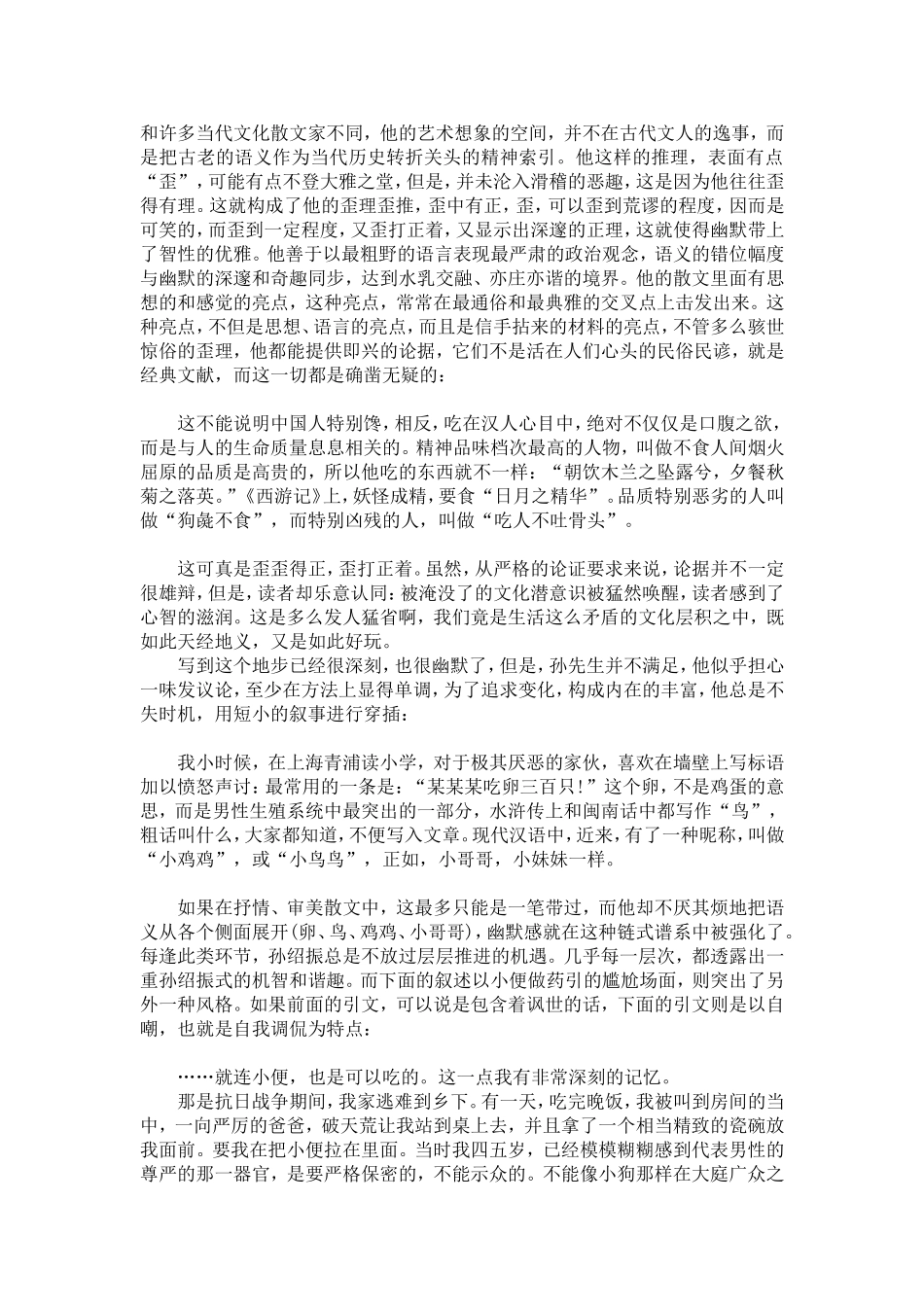从一个“吃”字看到民族无意识中的核心价值孙绍振不满足于把幽默固定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追求是把幽默和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的探索结合起来。他的幽默以歪理歪推见长,但是信手拈来的文献却是经典的。除了中国的历史宝库,还有民俗和普通词汇。这使得他的行文左右逢源,触类旁通,涉笔成趣。他最为在意的往往并不是现象本身,而是其背后深藏着的荒谬和可笑;恰恰是在这些荒谬可笑中,他揭示出汉民族的核心文化价值,并对之加以温和的调侃。孙先生是学者,他的散文远离抒情,似乎不以审美为务。智趣的追求成为风格的一大标志。对于走马灯似的前卫文论,他常有保留,引起他青睐的只是话语学说和文化批评。孙绍振之所以成为孙绍振,就在于他对西方文论并不五体投地地崇拜,他一再提醒自己:站直罗,别趴下,以创作实践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他相信,任何西方文论如果不与汉语实际相结合,只能像无根的圣诞树。对那些把话语学说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人士,他评价不高。他觉得,如果话语学说和文化批评包含着真知灼见,最重要的不是无条件地加以信奉,对于中国当代散文来说,应该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分析和验证,哪怕是手工业式的分析,也应该在所不辞。他没有像流行的当代文化散文那样沉醉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他不屑于从宏大的历史画廊汲取资源,他善于通过最平常最简单的现象,甚至是一个说法,一个字,进行思想的、文化的、艺术的探索。他曾经写过一篇《说不尽的狗》,通篇就讲一个“狗”字在中国人,在德国人、美国人心目中文化价值的巨大差异。由于幽默中蕴含深邃的文化价值,这篇文章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他还写过《谈恋爱的“谈”》,《搞恋爱的“搞”》,《论“阿拉”》,都是把思绪聚焦在一个单位的词语上的。《国人之吃》也是一样,就是以一个“吃”字,来探索汉民族的核心的潜在观念。题目越小,施展的空间就越有限,这等于给自己一个难度,令人想起闻一多先生的著名命题“戴着镣铐跳舞”。舞要跳得好,跳得美,就需要对语言的潜在微妙有高度敏感。本文最初在报纸上发表时,题目是《论中国人的吃饭》,高度语言洁癖使他不能忍受其中些微的生硬,后来成倍地扩大了篇幅,拿到《山花》上去刊载,改成了《国人之吃》,敏感的读者不难从“国人”和“之”中感到原题所没有的典雅和古老的意味。一个“吃”字,做成近九千字的文章,得力于对词语深层那精妙的多元、深层的探索。首先,他对之进行文化价值的还原,把习以为常的词语悬搁起来,暂时排开、去除一切凝固的表层语义,让它回到原生状态,矛盾和怪异就显示出来了。他从“吃”联系到“口”,从词源上追寻其文化心理的原生状态,在“人口”“户口”这种天经地义的说法中,他发现了只有汉语才有的特征:“口”的饮食功能被淡化,人数和家庭的计量单位被强化。经过还原,其中的不合理、不合逻辑,就给文章带来了一种趣味,当然不是抒情的情趣,而是心智得以启迪的智趣。作为理论家的概括力,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广度极大的概括力,不可能从普通人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神仙“不食人间烟火”,红军歌曲“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义和团诗歌“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这些毫无联系的话语之间,发现以吃为纲一脉相承的联系。他曾经提出散文当以非抒情为上,学者散文贵在审智,审智的才能之一,就是在人们看不出联系的地方找到雄辩的联系,在人们发不出疑问的地方提出深邃的问题,在人们感觉麻木的地方发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奥秘。他的智慧聚焦在从熟悉的词语中,发掘出陌生的新意,从而率领着读者从熟知的事物和观念中发现陌生的内涵。他的智慧的感染力的奥秘就在这里。他的这种追求,和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陌生化”有很大的不同。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日常的感觉,常用的语词,读者自动化地认知了,感觉钝化了,习以为常了,就没有生动感了。作家的任务,就是把语词加以陌生化,引起读者感觉的惊异和注意的持久。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西方文学语言中常用的比喻、暗喻,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段都是以超出常规的用法来创造陌生化的感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红杏枝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