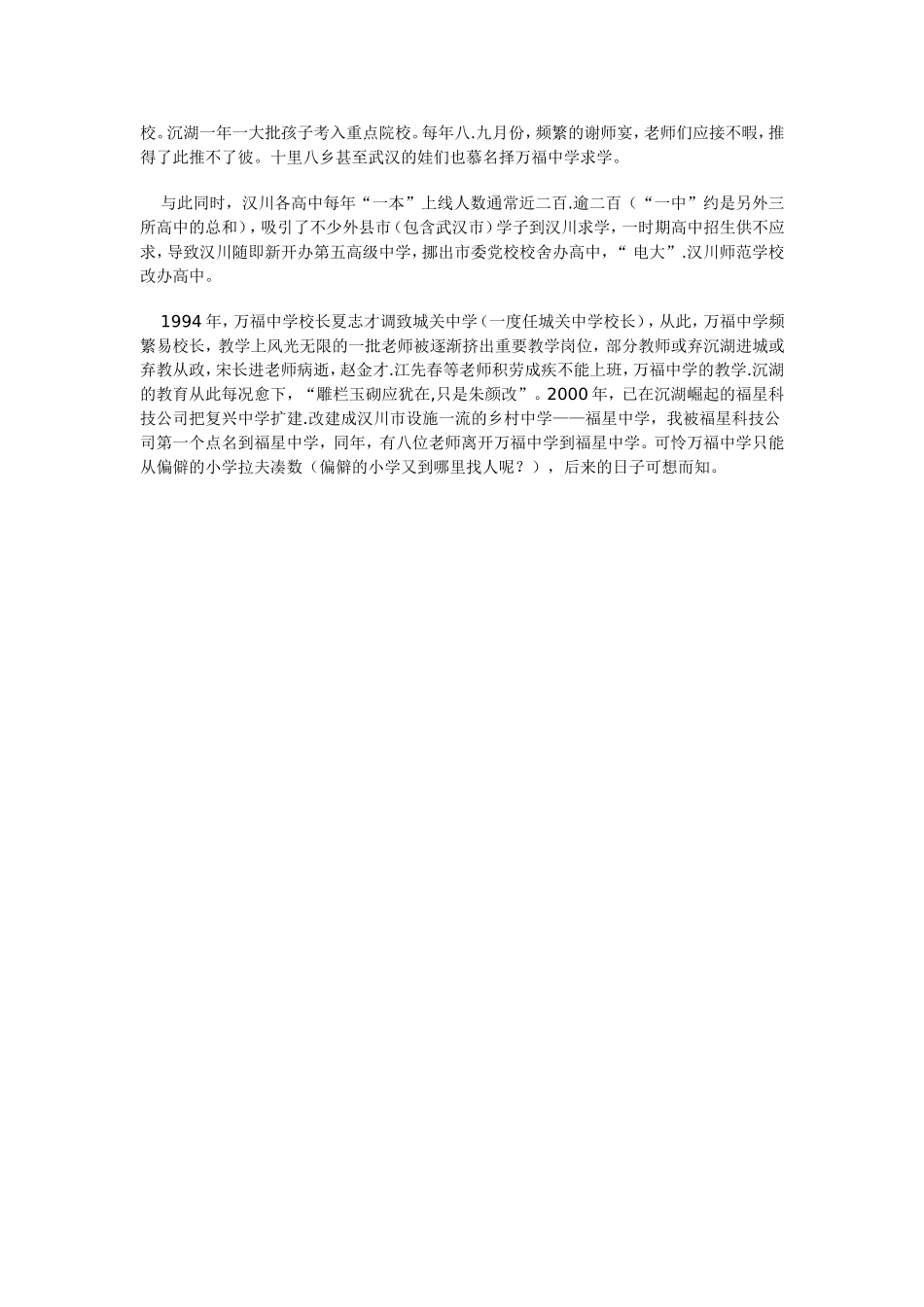来自农村教育一线的报告(一)在一个农业大国,要科技强国.教育兴国,绝对不能小视农村教育。说到教育,在我们农村流传一句话;从师不高,学艺不奥。教育家也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可见老师的学问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城乡差别特别严重的中国,学问权威或者说学问标杆决定着农村教育。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略懂文墨的农民创造了世界上的“民办教师”一词,把教室设在房屋宽敞的农户,挨家挨户地把农民的孩子请到学校,使学校教育在乡村全面铺开。在学问上,这些民办教师的确才高没有八斗,但每个人都是那片小天地中的学问标杆,他的学问和智商在那片小天地中被公认是第一流的,无论你现在的有些人怎样刻薄他们。他们为共和国的乡村学校教育打开了局面。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浩劫的十年“文革”,把大批知识分子驱赶到乡村,这些“牛鬼蛇神”把农村教育推向了一个火红的时代(至少我们汉川沉湖是这样的),每一个大队(村)有一所完整的小学,沉湖镇三个管理区共有五所中学。学校在乡村是最气派的建筑,校内有教师寝室.食堂。每所学校有专门人员做饭.种菜(当然有菜地),有的生产队还为学校无偿提供柴.米.油。我读高中时,我们熟悉和崇拜的老师有:袁宏泽老师,毕业于原华中师范学院;潭艳秋老师,毕业于湖南某大学;李明老师,国民党原中央日报社编辑。他(她)们在我们眼中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在农民的眼中是“文曲星”下凡。1977年,我参加国家恢复的统一“高考”。在我大学求学的几年时间里,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文曲星”陆续返城。待到我毕业返乡时,在沉湖,我是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孤家”“寡人”。我回沉湖做的第一件事是协助赵复录校长完成农民文化扫盲的最后工作。先后任教于三所中学。杜公中学地处天(门)沔(现在称仙桃市)汉(川)三市的交界处。1983年,该校校长与一数学老师卷起铺盖走了人。吴发元临危受命任校长教化学课,点将我教毕业班数学。吴发元与我们在同一口锅里吃饭,在同一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工作量比我们大。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所全汉川最不起眼的乡村中学,学生何成文在地区数学竞赛中获奖,有学生被拔尖考进汉川“一中”,大多数学生进入高中,有的学生后来进入大学。这种效果在沉湖唯一,在汉川所有边缘乡镇唯一,在汉川四大镇才会出现。1985年,吴发元调致县教研室,随后,我调进万福中学。一年多以后,杜公中学在文化教育地图上消失,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的断壁残垣。它让我联想到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一个词:殷墟。教育这种事业,需要一批人的无私奉献。我在万福中学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沉湖的老师蒋楚芳.邱又甫先后倒在讲台上,默默无闻地走了;跟我多年在一个班级的搭档老师宋长进,积劳成疾,撇下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带着遗憾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个人具体做了五件事情:1.培训民师,建设沉湖教师队伍。2.培训教师,提升沉湖教师队伍素质。3.给沉湖驻军开班授课,支援军队文化建设。4.协助沉湖教育组组织教学调查研究,提升沉湖教育教学水准。5.教毕业班数学,万福中学连年“中考”数学成绩均分过百分,成为汉川多年的教学教育热点学校。沉湖一年一大批孩子考入重点院校。每年八.九月份,频繁的谢师宴,老师们应接不暇,推得了此推不了彼。十里八乡甚至武汉的娃们也慕名择万福中学求学。与此同时,汉川各高中每年“一本”上线人数通常近二百.逾二百(“一中”约是另外三所高中的总和),吸引了不少外县市(包含武汉市)学子到汉川求学,一时期高中招生供不应求,导致汉川随即新开办第五高级中学,挪出市委党校校舍办高中,“电大”.汉川师范学校改办高中。1994年,万福中学校长夏志才调致城关中学(一度任城关中学校长),从此,万福中学频繁易校长,教学上风光无限的一批老师被逐渐挤出重要教学岗位,部分教师或弃沉湖进城或弃教从政,宋长进老师病逝,赵金才.江先春等老师积劳成疾不能上班,万福中学的教学.沉湖的教育从此每况愈下,“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2000年,已在沉湖崛起的福星科技公司把复兴中学扩建.改建成汉川市设施一流的乡村中学——福星中学,我被福星科技公司第一个点名到福星中学,同年,有八位老师离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