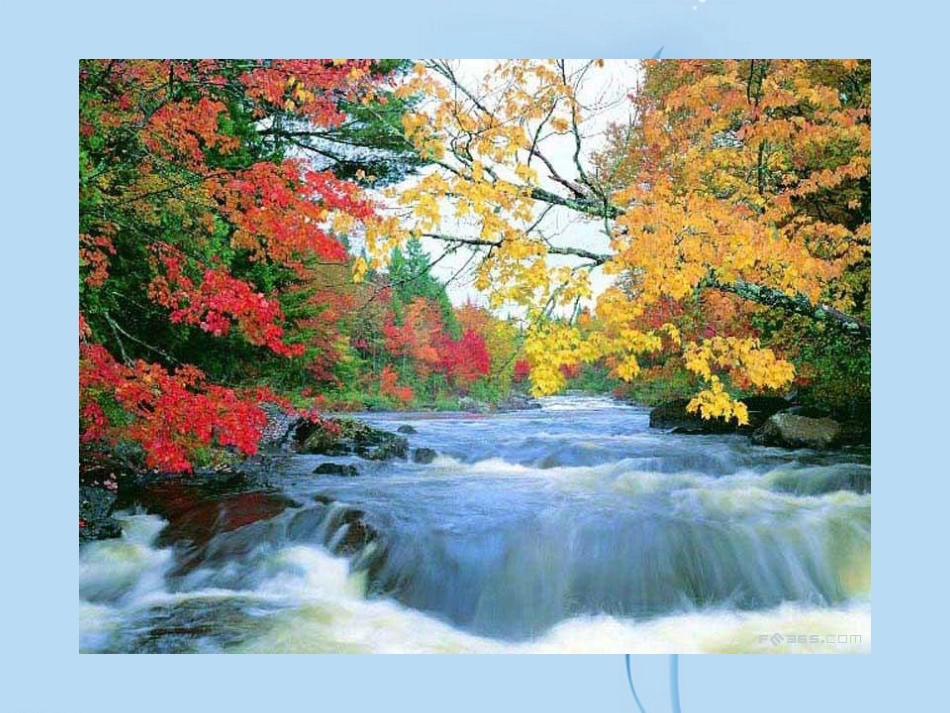秋天何其芳震落了清晨的露珠,伐木声传出幽谷。放下镰刀,用背篓来装竹篱间的瓜果。秋天在农家里。震落了清晨满披着的露珠,伐木声丁丁地飘出幽谷。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秋天栖息在农家里。“满披”形象生动。视觉“飘”字贴切传神。丁丁,听觉伐木声与清晨、露珠等意象构成一幅清净润泽的有声画。“饱食”写丰收之景,拟人。“稻香”使人满口生香。嗅觉“肥硕”也见出丰收之景。最后一句总束,画龙点睛。“栖息”一词,拟物,将虚无的秋天具体化,营造繁忙之后农闲的松弛、闲静的气氛。向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网,“冷雾”烘托出一派朦胧的诗意,又与季节吻合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桕叶的影子。乌桕叶有人说:比喻似拙实妙,耐人寻味。你认为呢?“归泊”“游戏”既写景,又暗示时间,与上文“清晨”呼应。一词虚实相生,体现了秋天的活泼和渔人收获的喜悦。想像一下吧草野在蟋蟀声中更寥阔了。溪水因枯涸见石更清洌了。写景的作用?起兴手法,“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先写秋景,引出少女情思。“梦寐”将秋天拟人化,睡梦朦胧,写出了少女的情感体验,羞涩朦胧,似喜似羞。牛背上的笛声何处去了,那满流着夏夜的香与热的笛孔?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小结:先写繁忙夏天之后的农闲景象,具有清静的氛围;接着写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不见农家些许的艰难苦恨,故具有清远的氛围;最后写少男少女朦胧而纯真的情感,所以具有了清甜的氛围。总起来说,是充满诗意的秋天!何其芳(1912—1977)诗人,文学评论家。四川万县人。北京大学毕业。1938年夏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1944─1947年,两次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散文集《画梦录》等。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关于写诗和读诗》、《文学艺术的春天》等。1977年7月24日在北京逝世。冰心:我同何其芳同志的来往不多,但是从1951年归国后,从作协的朋友口中,我所听到的关于何其芳同志的学问之深、藏书之富、著作之多、待人之诚等等事迹,真是洋洋盈耳。我还记得有一次文藻对我称叹说:“你们文艺界有一位何其芳同志,真是一位很渊博的学者!”比较阅读:读《秋景》,比较与《秋天》在内容、感情、语言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告诉我,欢乐是什么颜色?像白鸽的羽翅?鹦鹉的红嘴?欢乐是什么声音?像一声芦笛?还是从簌簌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是不是可握住的,如温情的手?可看见的,如亮着爱怜的眼光?会不会使心灵微微地颤抖,而且静静地流泪,如同悲伤?欢乐是怎样来的?从什么地方?萤火虫一样飞在朦胧的树阴?香气一样散自蔷薇的花瓣上?它来时脚上响不响着铃声?对于欢乐,我的心是盲人的目,但它是不是可爱的,如我的忧郁?欢乐何其芳巴金:去年七月,我在上海得到其芳逝世的消息,我特别感到难过的是前不久沙汀同志还来信要我也劝告其芳爱惜身体、注意劳逸结合。我来不及写那样的信就听说他住进医院了。十几年中我们只互通过一次信。他在报上看见我的名字(十一年中间的第一次!),写了一封信托报社转来,开头就说:“读到你的文章,很高兴,你又拿起笔来了。”最末一句是“很希望不久还能见到你”。我绝没有想到这是他怀着深厚友谊在向我告别。我多么后悔我为什么不回答他一封长信,详细叙说我十几年的遭遇和今后的打算。连他托我代买的维尔特的诗集我也没有能够办到!我的情况他可能不清楚。但是他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我的耳里:他被揪去批斗,他离开了干校,他回到北京带病工作,他到四川搜集材料准备写小说……还有他几次发病的情况。这其间报刊上也常常出现他的名字,更多的时候是有人用“四人帮”的鞭子抽打这个读者熟悉的名字。那些时候我真替他担心。“四人帮”垮了,枷锁一个接一个地给打碎了。我听说他夜以继日地奋笔写作,看见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