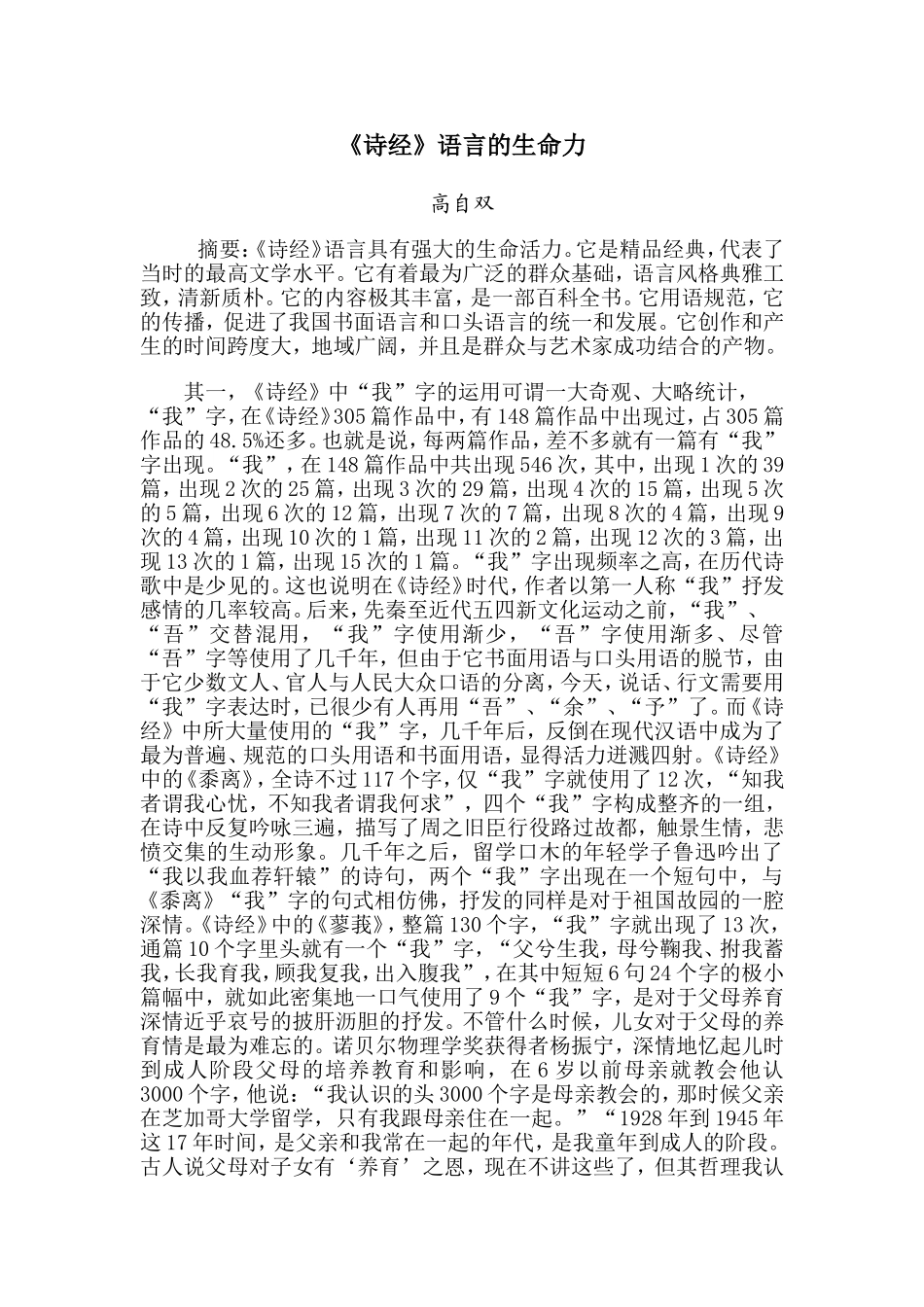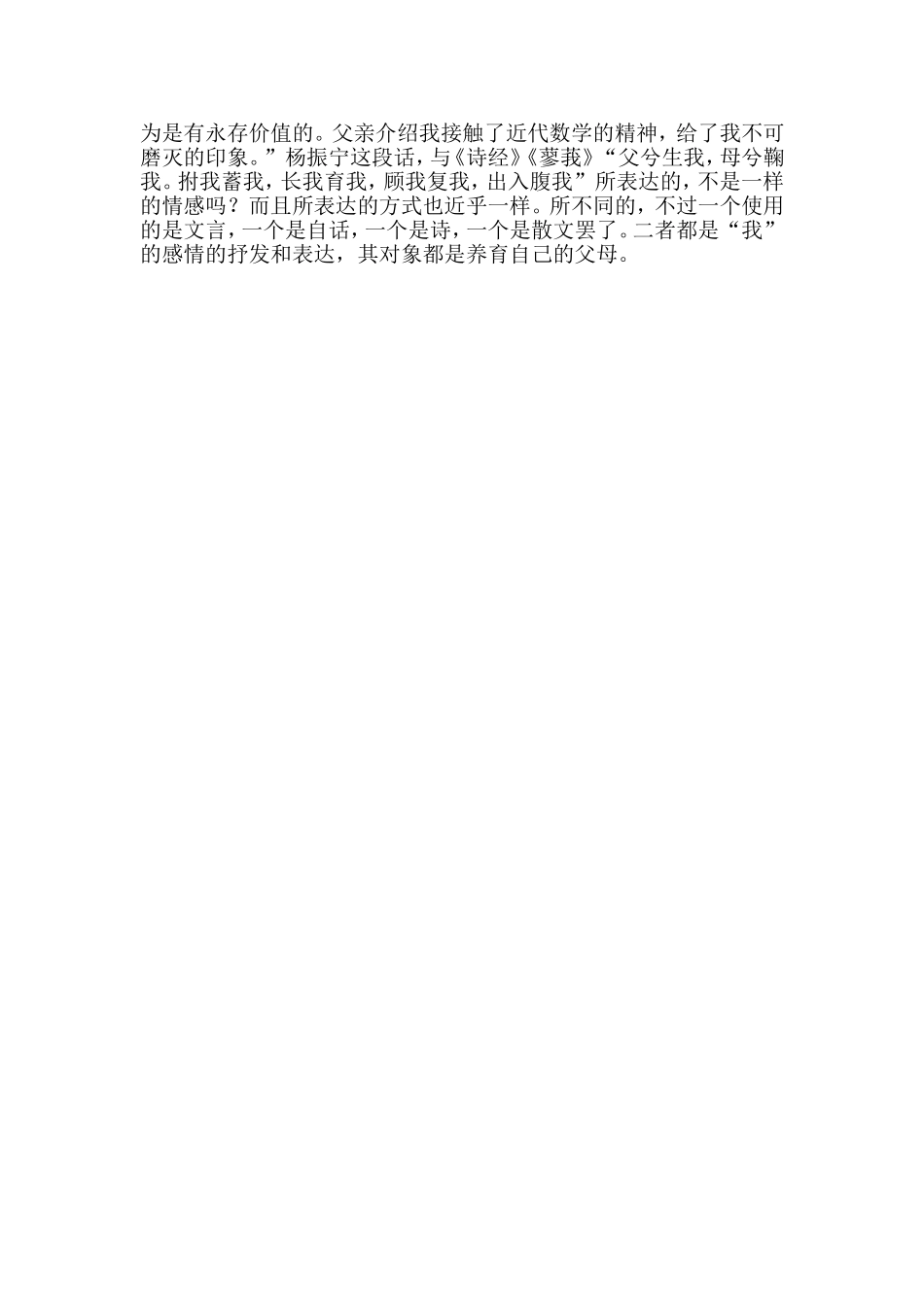《诗经》语言的生命力高自双摘要:《诗经》语言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它是精品经典,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文学水平。它有着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语言风格典雅工致,清新质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是一部百科全书。它用语规范,它的传播,促进了我国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它创作和产生的时间跨度大,地域广阔,并且是群众与艺术家成功结合的产物。其一,《诗经》中“我”字的运用可谓一大奇观、大略统计,“我”字,在《诗经》305篇作品中,有148篇作品中出现过,占305篇作品的48.5%还多。也就是说,每两篇作品,差不多就有一篇有“我”字出现。“我”,在148篇作品中共出现546次,其中,出现1次的39篇,出现2次的25篇,出现3次的29篇,出现4次的15篇,出现5次的5篇,出现6次的12篇,出现7次的7篇,出现8次的4篇,出现9次的4篇,出现10次的1篇,出现11次的2篇,出现12次的3篇,出现13次的1篇,出现15次的1篇。“我”字出现频率之高,在历代诗歌中是少见的。这也说明在《诗经》时代,作者以第一人称“我”抒发感情的几率较高。后来,先秦至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我”、“吾”交替混用,“我”字使用渐少,“吾”字使用渐多、尽管“吾”字等使用了几千年,但由于它书面用语与口头用语的脱节,由于它少数文人、官人与人民大众口语的分离,今天,说话、行文需要用“我”字表达时,已很少有人再用“吾”、“余”、“予”了。而《诗经》中所大量使用的“我”字,几千年后,反倒在现代汉语中成为了最为普遍、规范的口头用语和书面用语,显得活力迸溅四射。《诗经》中的《黍离》,全诗不过117个字,仅“我”字就使用了12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四个“我”字构成整齐的一组,在诗中反复吟咏三遍,描写了周之旧臣行役路过故都,触景生情,悲愤交集的生动形象。几千年之后,留学口木的年轻学子鲁迅吟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两个“我”字出现在一个短句中,与《黍离》“我”字的句式相仿佛,抒发的同样是对于祖国故园的一腔深情。《诗经》中的《蓼莪》,整篇130个字,“我”字就出现了13次,通篇10个字里头就有一个“我”字,“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在其中短短6句24个字的极小篇幅中,就如此密集地一口气使用了9个“我”字,是对于父母养育深情近乎哀号的披肝沥胆的抒发。不管什么时候,儿女对于父母的养育情是最为难忘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深情地忆起儿时到成人阶段父母的培养教育和影响,在6岁以前母亲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他说:“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杨振宁这段话,与《诗经》《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所表达的,不是一样的情感吗?而且所表达的方式也近乎一样。所不同的,不过一个使用的是文言,一个是自话,一个是诗,一个是散文罢了。二者都是“我”的感情的抒发和表达,其对象都是养育自己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