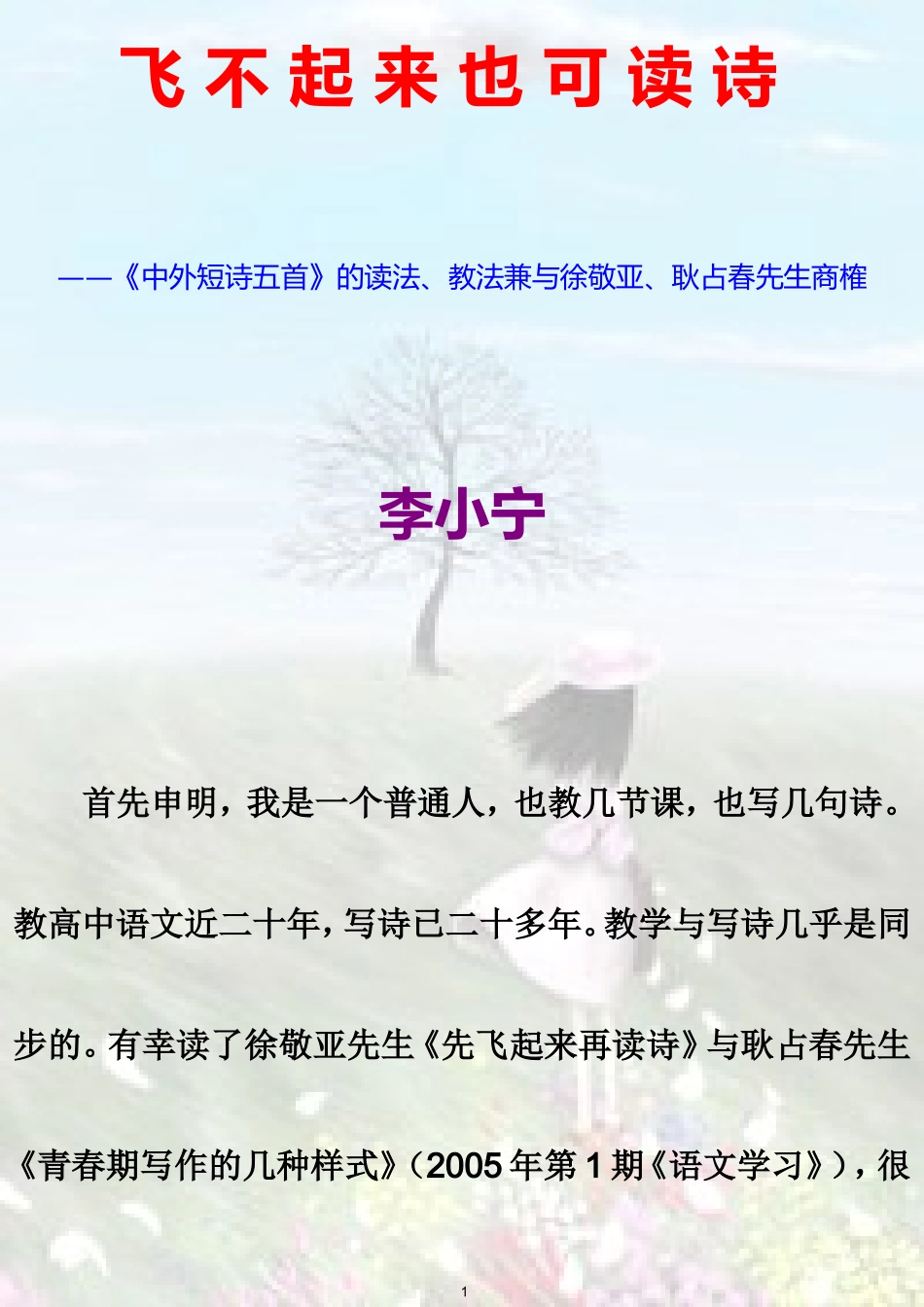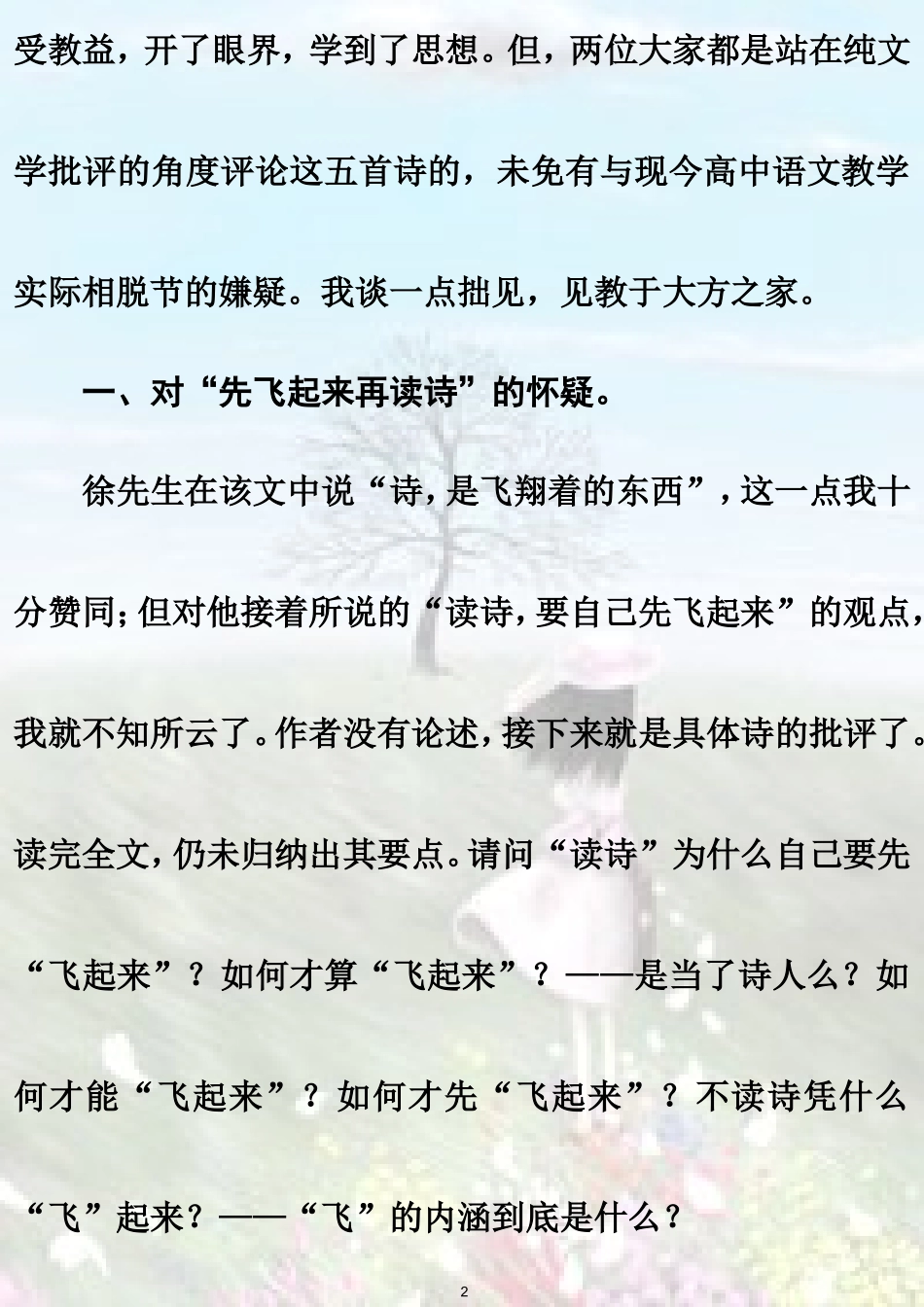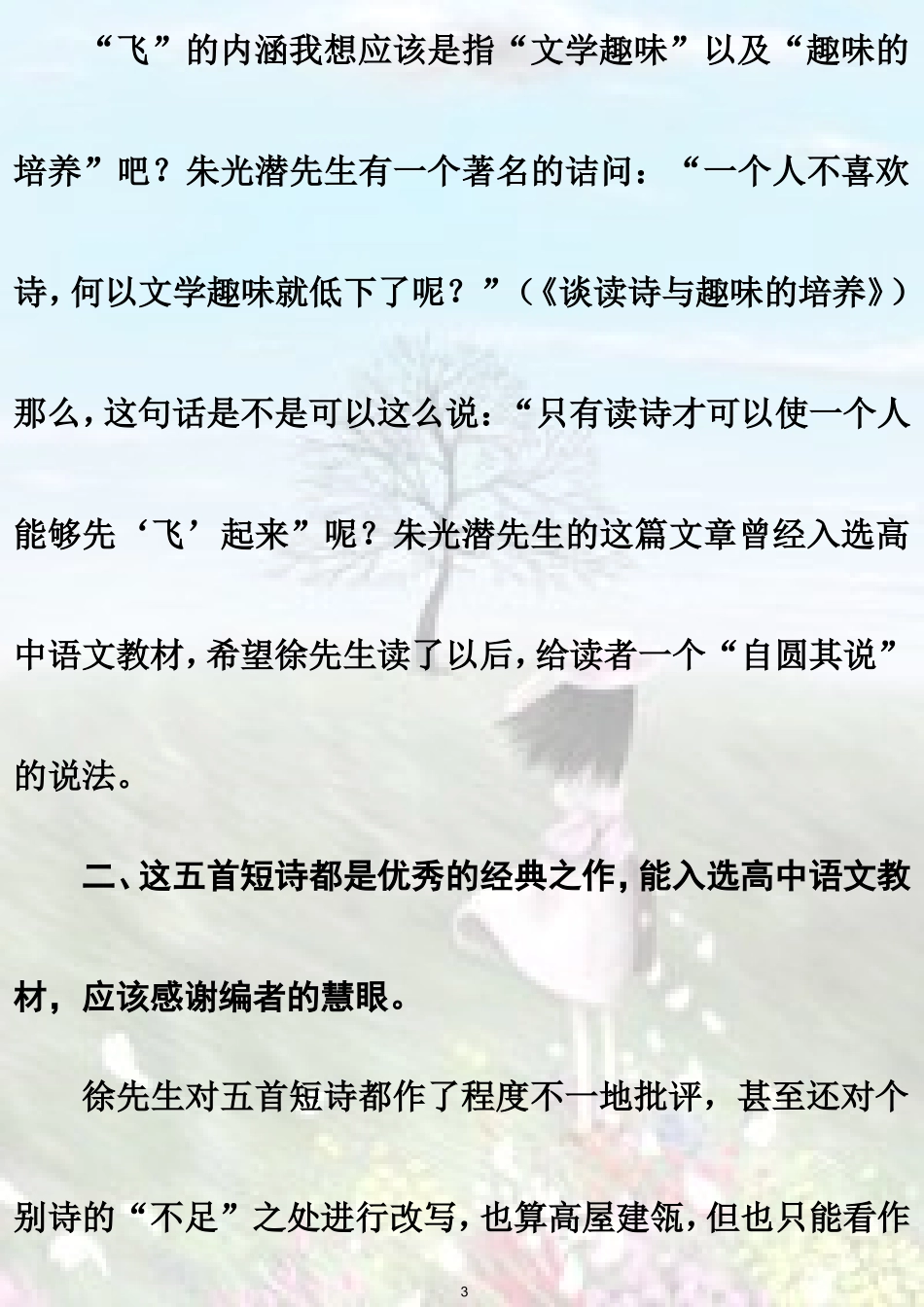飞不起来也可读诗——《中外短诗五首》的读法、教法兼与徐敬亚、耿占春先生商榷李小宁首先申明,我是一个普通人,也教几节课,也写几句诗。教高中语文近二十年,写诗已二十多年。教学与写诗几乎是同步的。有幸读了徐敬亚先生《先飞起来再读诗》与耿占春先生《青春期写作的几种样式》(2005年第1期《语文学习》),很1受教益,开了眼界,学到了思想。但,两位大家都是站在纯文学批评的角度评论这五首诗的,未免有与现今高中语文教学实际相脱节的嫌疑。我谈一点拙见,见教于大方之家。一、对“先飞起来再读诗”的怀疑。徐先生在该文中说“诗,是飞翔着的东西”,这一点我十分赞同;但对他接着所说的“读诗,要自己先飞起来”的观点,我就不知所云了。作者没有论述,接下来就是具体诗的批评了。读完全文,仍未归纳出其要点。请问“读诗”为什么自己要先“飞起来”?如何才算“飞起来”?——是当了诗人么?如何才能“飞起来”?如何才先“飞起来”?不读诗凭什么“飞”起来?——“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2“飞”的内涵我想应该是指“文学趣味”以及“趣味的培养”吧?朱光潜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诘问:“一个人不喜欢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了呢?”(《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只有读诗才可以使一个人能够先‘飞’起来”呢?朱光潜先生的这篇文章曾经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希望徐先生读了以后,给读者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二、这五首短诗都是优秀的经典之作,能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应该感谢编者的慧眼。徐先生对五首短诗都作了程度不一地批评,甚至还对个别诗的“不足”之处进行改写,也算高屋建瓴,但也只能看作3一家之言。耿先生在他文章的结尾处总结说:“现代诗有许多好的短章,这样的一些诗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并不那么让人满意。为什么我们的诗学趣味和审美趣味总是停留在不那么成熟的状态?”——问得很好,两个“趣味”均处于“不那么成熟的状态”,是因为喜欢诗、读诗的人太少,所以“飞”不起来(亦可参看朱光潜先生的文章)。《断章》就文本而言,无论是意象的选取,还是意境的生成,都是优美的,无可挑剔的。审美即知音,阅读即移情。学生通过阅读、背诵,真正能在内心深处产生些许触动,些许感悟,些许共鸣,从而受到美的熏陶,足矣。没有必要深究“学术界4几种所谓的解释”(徐文);也没有必要在乎“如果成为更广泛的趣味”是否意味着“某种普遍的不成熟”(耿文)。《风雨》也是好诗。前四句的好处,笔者同意二位大家的分析。但,对最后两句的“败笔”(徐文)与“单义性的限制”(耿文),笔者不敢苟同。更对徐先生自作聪明的改写,也“耿耿于怀”(徐文)。原诗前四句以恢弘的意象来描写外部世界的“风雨”以及人在“风雨”中的感受,给人一种压抑与无所适从的感觉,恰好为后两句“我”的出现张本。升华性地表现人的主观能动性;“风雨”中“我”有驾驭“舟”的愿望(“忧怀”)。我不知道让风雨中“年轻的舵手的忧怀/匍匐在大地的海上”(徐的改诗),“会更好些”(徐文)什么?5“匍匐”一词不但歪曲了作者的本意,而且改变了诗意升华的方向,很是蹩脚。《错误》是一首意境优美而寓意深厚的诗。耿先生几乎全盘否定了此诗,他连用“不喜欢”、“别扭”、“俗套”、“浅陋”等语词,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徐先生在说了许多废话之后终于勉强(“就……而言”)表态:“诗味最足。”议论之后,又有“遗憾”,还是针对结尾,认为最后两句应该改为“那走在江南的归人如过客匆匆隐没……”——“可能会更好吧”(徐文),是吗?我仍不敢苟同二位大家的解读与改写,因为他们还未能深入地理解文本,所以分析起来就会文不逮意。其实,这首诗用6的就是传统的“美人香草”式比兴手法,再加上“过客”等原型意象的运用,使得表达更有深意。“江南”(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即“怜”)是一个情结,一个象征;“容颜如莲花”的女子也是一个情结,一个象征;其他名词何尝不是这样。古典情怀里的少年“过客”(李白有“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名句,鲁迅有《过客》名剧),打马走过“江南”,不是回归,而是出发。我也承认这是一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