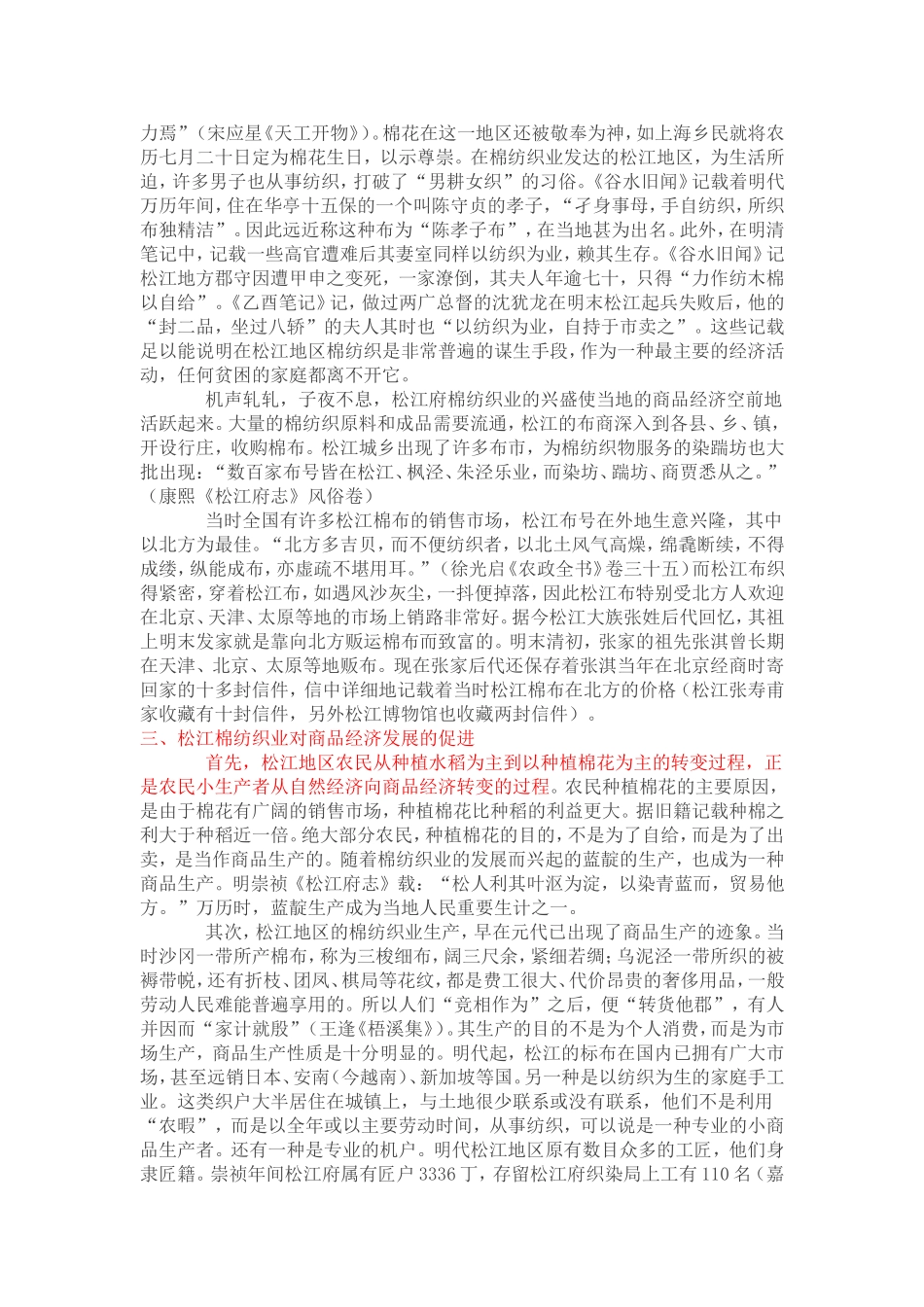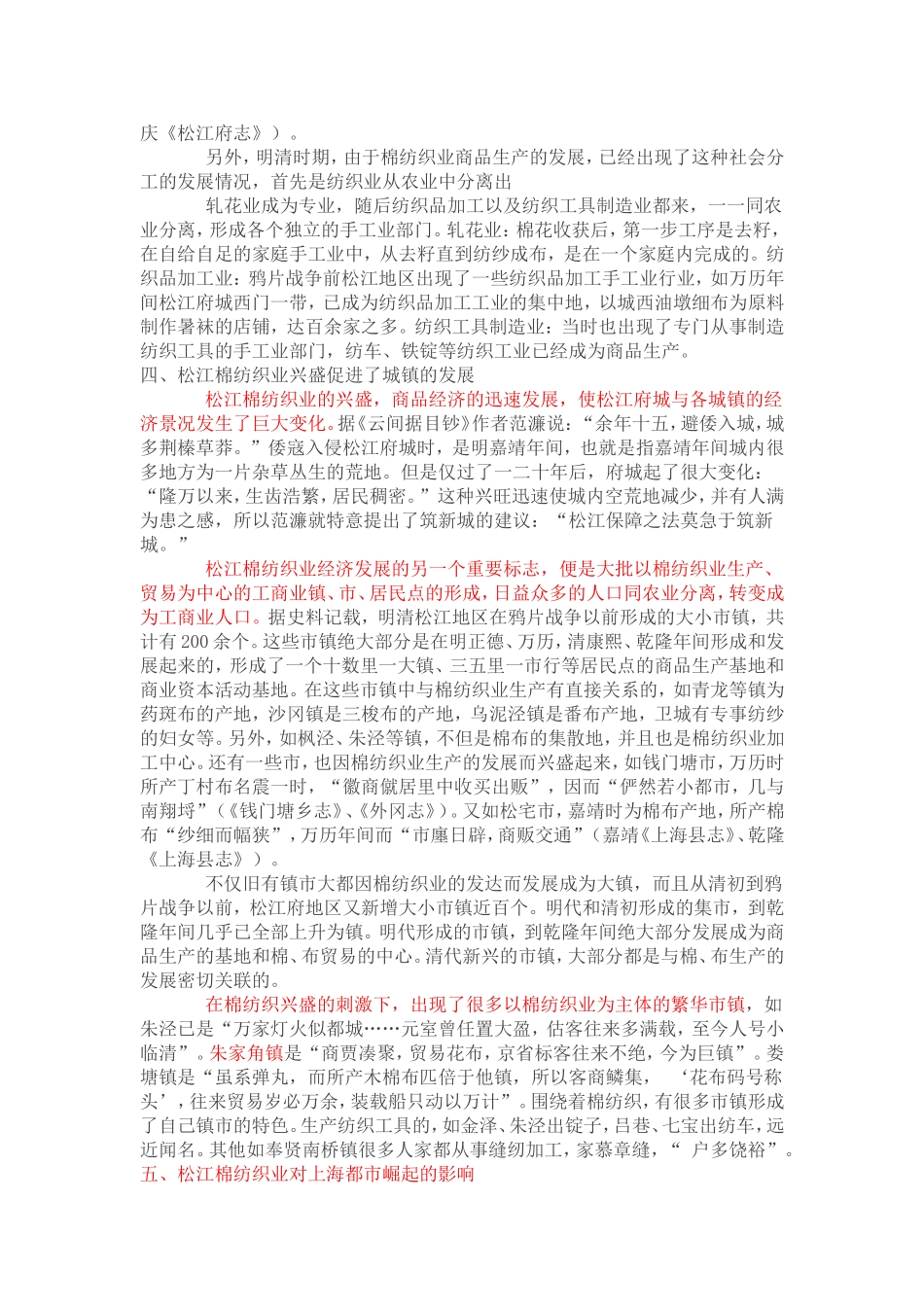古代松江棉纺织业的五大重要影响(“啷啷啷,啷啷啷,骑马到松江,街上买块布,小囡做条裤。”这首儿歌曾在上海广泛流传,由此足以说明历史上出名的松江布其影响之深远。在松江棉纺织业发展历史中,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一名农村妇女黄道婆竟然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棉花革命”,从而使松江府经济繁荣而崛起于东海之滨。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6年),乌泥泾出生的黄道婆,把从海南岛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带回家乡松江,向人们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并力行四大革新创造之举,即改革纺织工具轧花车、弹棉椎弓、纺车和织机,纺织技术的革新,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和繁荣。在明清时期松江“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当时人称松江城内外“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松江布以质地优良、花饰灿美而闻名海内外。松江地区因而发展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康熙《松江府志》记载松江棉布时称:“吾乡所出皆切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由此,松江为中华史册所谱写了最光辉的一页。在松江棉纺织业兴盛的数百年中,松江人民登上了最能显示自己聪明才智的经济舞台,松江经济社会发生了奇迹般的巨变,植棉成了松江重要的产业,纺织业成了松江的经济支柱,贸易使松江的商人财运亨通。其时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对松江乃至全国的经济生活社会风俗等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本文就此课题略作如下考析。一、以布折粮成为松江田赋的主体黄道婆所传授的先进技术,为松江棉纺织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当地人民“竞相作为”,纷纷开始从事棉纺织生产,靠纺织为生的家庭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封建王朝对田赋也不断加重。为了向人民榨取大量棉布,早在元初,元世祖就创立了“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元史》卷十六《世祖本记》)。这样的征派虽然只推行了两年,但后来到成宗时还是把棉布纳入了常赋。明初朱元璋进一步推广植棉。他在登基时曾诏令天下:“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康熙《松江府志》风俗)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开始,朱元璋还推行“桑枣田”、“棉田”免税的办法,开创了棉田免税的先例。但棉田虽然免税,种植其他一般庄稼土地的田赋却在成倍地增加。就松江府来说,田赋特别重。据康熙《松江府志》卷六中所载《顾清杂记》说:“松江在宋本华亭一县,田赋之数,见绍熙年。自景定公田法行,加赋至二十八万入元乃四十万,大德中覆实及籍没二朱张管后为七十万,国朝洪武二十四年至百四十万。皆正粮也。”前后一百余年的时间,松江的赋税额竟增加了近5倍。田赋繁苛,在松江地区的直接后果是百姓没有这么多粮食上缴,于是只得将农闲所织之布折数交售。明代统治者有意识地在松江地区扩大征收棉布,给松江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却也刺激了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封建王朝以棉田免税之法来鼓励植棉,其结果一方面达到了榨取大量棉布的目的,另一方面,同时也促进了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二、松江棉纺织业社会影响深广在松江人民的辛勤努力下,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从明代中叶开始走向兴盛。据徐光启《农政全书》载,松江府在明万历年间“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植棉数目之大,说明植棉已成为松江地区的主要农业生产活动。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形态下,妇女是棉纺织业的主要从事者,“乡村纺织,尤尚精致,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宋应星《天工开物》)。棉花在这一地区还被敬奉为神,如上海乡民就将农历七月二十日定为棉花生日,以示尊崇。在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地区,为生活所迫,许多男子也从事纺织,打破了“男耕女织”的习俗。《谷水旧闻》记载着明代万历年间,住在华亭十五保的一个叫陈守贞的孝子,“孑身事母,手自纺织,所织布独精洁”。因此远近称这种布为“陈孝子布”,在当地甚为出名。此外,在明清笔记中,记载一些高官遭难后其妻室同样以纺织为业,赖其生存。《谷水旧闻》记松江地方郡守因遭甲申之变死,一家潦倒,其夫人年逾七十,只...